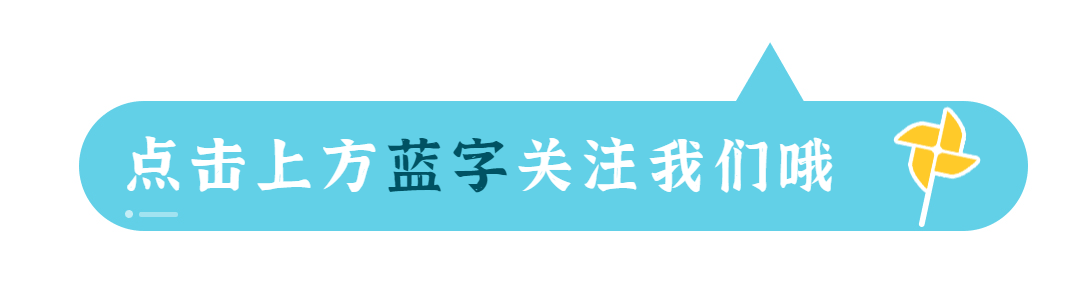
周朝是中國曆史上文化制度建設較為完整的一個時期,以禮儀、宗法為标志的社會規範在此時初見端倪,而婚姻制度的逐漸完善也為後世的發展奠定了一些原則。
西周春秋的貴族,上自周天子、諸侯,下到一般貴族,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婚姻,《詩·大雅·思齊》說周文王之妻“大姒徽音,則百斯男。”《詩·毛傳》認 為“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若按一女生十男孩計算,周文王至少有妻妾十餘人。這種婚姻的史實,近現代發現的西周春秋墓葬中也有所透露,陝西寶雞茹家 莊的西周中期墓葬中,發掘出一座夫妻妾三人合葬墓,晉侯墓地發現一組一夫二妻的并穴合葬墓。西周春秋貴族多妻的來源較複雜,歸納起來主要有:
(1)通過婚 姻禮儀正式迎娶,也就是《禮記·内則》所說的“聘則為妻”。從周天子到一般的貴族,他們的正妃或嫡妻大多是經婚姻禮儀娶來的。
(2)正式迎娶時的娣陪嫁。娣陪嫁亦即一女出嫁,她的女和妹妹陪嫁。同時還要由兩個與女方同姓的諸侯國各送一女随嫁,稱為“正媵”,正媵也要由娣、随嫁,這就是所謂“諸侯壹娶九 女”。媵嫁制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也有反映,《詩經》中“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指的是那些女子哭泣,是因為害怕随嫁。
(3)私奔為婚,亦即《禮記·内 則》所說的“奔則為妾”。
(4)轉房,即父終,子妻其庶母;兄終,弟妻其嫂;叔終,侄妻其嬸。在多妻的制度下,天子可以“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嫔、八十一 禦妻”,諸侯有夫人、世婦、妻、妾9人,除天子諸侯外,地位稍低的卿、大夫是一妻二妾,士是一妻一妾,隻有平民才是一夫一妻制。
由于 妻妾來源多雜且數量多,很容易引起貴族家庭内部沖突。為了調節這些沖突,克服一夫多妻婚姻的弊端,西周春秋時期,逐漸形成了一些有關貴族妻妾名份、地位的 禮法規定。首先,嫡妻的地位高于妾,有權幹涉妾的各種事務。其次,妾不得成為嫡妻,其子也不享受嫡長子的權力。再次,與妾名份不同。在婚姻關系方面,妾本 人具有獨立的婚姻權力,而女至娣則依附于嫡妻,本身沒有獨立的婚姻權力。嫡妻死後,娣可以合法地“繼室”,沒有嫡妻之名,卻有嫡妻之實,妾卻沒有這種權 力。
西周貴族一夫多妻婚姻不隻是一種簡單的婚姻形式,還是一種帶有政治色彩的社會活動,宗法制是西周春秋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宗法制的實質是把天然的血緣關系和婚姻關系政治化,作為政治統治的紐帶和手段。
在整個宗法關系鍊條中,家族是最基本的機關,家族的地位的高低和盛衰,很大程度取決于家族人口的多寡。西周春秋貴族實行一夫多妻婚姻的首要目的就是保證 宗法關系綿綿不斷,提高家族的地位。同時周天子通過與異姓諸侯的聯姻,與他們建立甥舅關系,稱異姓諸侯的國君為伯舅、叔舅,把衆多的異姓諸侯納入以周天子 為宗主的宗法體系;諸侯國君通過與異姓諸侯的聯姻,互相建立姻親關系,擴大他們的宗法聯系,有姻親關系的諸侯國常常是以而成為友好的國家;天子、諸侯以下 的貴族通過與異姓貴族的通婚,增強自己在宗法體系中的實力,以緻于在政治鬥争中是以而結成聯盟。在這個以婚姻為手段,擴大宗法聯系的過程中,選擇一夫多妻 婚姻是非常有利的。
夏商周時期,在聘娶婚流行之前,婚姻的成立存在着幾種形式:掠奪婚、買賣婚、交換婚姻。掠奪婚,指的是未得到女方 本人的及其親屬的同意,而憑借武力搶奪女子為妻一種婚姻成立方式。搶婚在《易經》有記載:“贲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乘馬班如,匪寇婚媾”,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意思是聽到踏踏的馬蹄聲,女子哭泣不已,原來不是強盜,而是搶婚的人馬。買賣婚是将女子當作貨物,換她作為妻妾的一種婚姻形式。交換婚是雙方父母各以女兒交換為兒媳,或者男子各以姐妹交換為妻子。
周代是禮儀建立的時代,從政治到文化制訂了一系列完整的典章制度 和禮樂規定,是為“周禮”,周禮認為夫妻之道是人倫的開端,因而給婚姻制訂了嚴格的制度,這就是聘娶婚的确立,聘娶婚延續于整個中國的傳統時代,是王朝禮 法承認的唯一的婚姻成立形式。聘娶婚,簡單地說,是男子以聘的程式娶妻,女子按聘的方式出嫁,聘娶婚最重要的特征是通常說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娶 婚的發展是因為當時父母根據自己的看法處理兒女的婚事是天經地義的,不過父母雖然是子女婚姻的決定人,但是需要中介人的工作,于是就有了媒妁之言,媒,就 是謀的意思,妁是斟酌的意思,媒妁就是斟酌男女雙方的情況給雙方家長出主意。聘娶婚成立的程式相當複雜,《周禮》對此有詳細的說明,大緻概況是納采、問 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等環節,這就是通常所謂的“六禮”。婚姻必須遵守這些禮節,才算是合法、嚴肅、正式的結合。
納采是婚禮的 第一項,即議婚階段,男家相中某女家為議混對象,就找媒人去說親,并請媒人“執雁”為禮,說明來意,征求女方家長的意見。為什麼要執雁為禮呢?因為雁是候 鳥,南遷北往必有定時,南來北往順乎陰陽,而男為陽,女為陰,以雁為禮,象征着男女雙方的陰陽和順,六禮中,除了“納征”外,其他禮節都要用雁為見面的禮 品,到了後世,由于雁的減少,就逐漸以鵝、鴨、雞來代替。
問名。女方納雁後,覺得男方合适,就寫出女子的生辰八字,交給媒人帶回男家。
納吉。問名之後,男家就将雙方的生辰八字交給蔔卦術士用龜甲蔔卦,蔔算後,如果沒有相沖相克之處,就再派媒人到女家認可,納吉到後世就變成了交換庚貼定婚的程式。
納征。就是後世所說的“下聘禮”,是“先納聘财,而後婚成”的意思。納征禮是男女成婚的關鍵,沒有經過納征的男女雙方,有“非受币不交不親”、“無币不相見”之說。
請期。也稱為告期禮,男家擇定迎娶吉日,先由術士蔔卦算定,再經雙方家長同意。後世的“催妝”就是由請期演變而來的,女方一旦接到男方的吉日通知後,就要準備嫁妝,并在成親之前,送嫁妝到男家“鋪房”,布置停妥,等待親迎。
親迎。是六禮中的最後一禮,男子在成婚之日須親自到女家以禮相迎,迎娶之後,新郎新娘拜天地、高堂、祖宗,婚姻正式成立。
“姓”最早是母系氏族社會認同血緣的一種标志,在父權制建立後包括周代的一段時間内,姓是家族系統的标志,有了姓,人們就知道自己是哪個家族的後代,如 姓梁,是因為伯益治水有功,被封在梁這個地方,他的後裔就是以而姓梁。當時,有以所在地名、國名為姓的,如曹、魯、宋、衛等,有以官職為姓的,如司徒、司 馬等,有以職業為姓的,如蔔、陶等等,由于同姓的具有一定的血緣關系,姓有着“别婚姻、别種族的社會功能。在西周的婚姻活動中,實行比較嚴格的”同姓不婚 “制度,這是周與商婚姻上的一個較大的差别,商雖然強調了近宗不婚,隻有五世的限制,而周是”雖百世而婚姻不得通“春秋時,魯昭公從吳國娶回夫人,由于魯 國是周公的封地,姬姓,吳國也是姬姓,當時人就指責魯昭公”君而知禮,孰不知禮,甚至這位夫人死後,魯國也沒有按照正常訃告諸侯,不能執行夫人一級的葬 禮。
對于同姓不婚,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生理上的,近親結婚,不利于優生,“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同姓不婚,懼不殖也”。另一個 是政治上的,同姓不婚使貴族與異姓聯盟,穩固權勢,擴大學宗的力量,同時保持了本宗内部輩份的差别,維護着嫡庶、長幼、親疏等尊卑關系,使得不至于發生混 亂,動搖倫理規範。
宗法家長制确立之後,婦女的地位開始明顯下降。禮制規定國家政權、家庭産業都由父子相繼,時代相承,既然血緣按父系計算,隻傳其子,不傳其女,是以每個家庭非常重視生養兒子,而對女兒則表現出無關痛癢的态度,《詩經·小雅·斯幹》有載:
“乃生男子,載寝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乃生女子,載寝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
重男輕女,男尊女卑,表現得極為分明,後人稱生男孩為“弄璋之喜”,生女孩為“弄瓦之喜”,其典故就來源于此。
而夫妻關系是女子從屬于男子,天子的妻稱後,表示在天子之後,諸侯的妻子稱為夫人,表示是扶助其君,大夫的妻子稱為孺人,表示服從丈夫,士的妻稱為婦 人,表示主持家務(婦的繁體字是婦其義是女子拿着掃帚灑掃)。夫妻關系對女方而言首先是順從關系,嚴格限制婦女參加社會政治生活。男女的活動範圍開始明 确:“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宮固門,阍奪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家庭之内,夫妻雙方對财産的支配也是以男子為主,妻子 不能私聚家财,婚後的家庭财産,包括妻子陪嫁的财産在内,均由丈夫支配,如《禮記·内則》所說的:“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田、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由于周朝還隻是初步建立婚姻制度的時代,雖然兩性間的接觸已經開始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在原始社會的遺風影響下,男女自由接觸相愛還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像後世那樣視為洪水猛獸,在這樣較為寬松的大背景下,男女青年在婚嫁之前自由接觸是比較普遍的。
據記載,自仲春二月到三月三日上巳節,以及夏初的采桑季節,是男女青年聚會相歡,對歌言情的良辰佳日。《詩經·國風》中有不少展現這種自由愛情情景的詩 歌,如《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适我願兮”;《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衛風·木瓜》:“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為好也”。
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中,夫死不嫁、“從一而終”的所謂“貞節”并沒有形成,《論語》一書沒有一處是讨論這一問題的,孔子最為推崇《周禮》,而他的兒子伯魚死了,伯魚的妻子改嫁到衛國,孔子也沒有表示反對,說明孔子所認定的禮儀中,貞指的是夫妻之間的“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