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赤宇(湖南湘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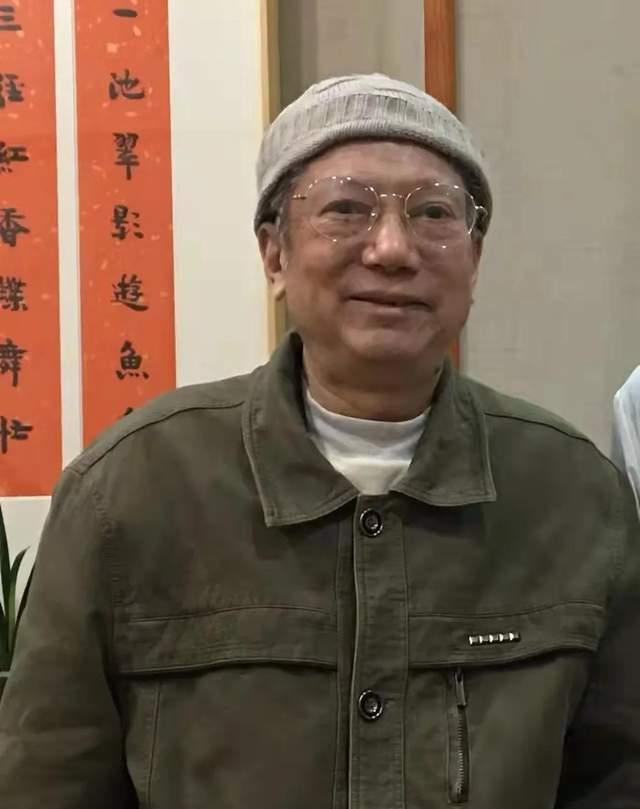
(敖普安先生)
關注敖普安先生的藝術已有經年,但與他沒有直接接觸,往往隻聞其名,未聞其聲。近期,有緣專程拜訪普安先生于其書齋“攻玉室”,一進門,牆上挂着充滿金石氣的書法作品撲面而來,感染力直指人心。與先生對話,如沐春風。
詩是統領一切藝術的源泉,充分表現出漢學之美的多種形式,或借鑒昔賢,或馳騁才力,或發抒性靈,來擴大詩美學的反射面,提高詩的穿透力和擴張力,并為其它門類藝術提供豐富的想象力和漢字把控力。普安先生幼時始入門學習詩聯對句,漸漸愛好成性。在經曆了動蕩清貧的青年時代後,普安先生,思維精敏,潛遊詩藝,工作之餘,心無旁鹜,至今已逾四十餘載,洋洋上千首詩稿,字字珠玑,然集腋成裘,于2012年彙成《攻玉室詩詞選》出版行世。
普安先生的詩,湘潭詩壇耆老、其師田翠竹公評曰:“清新俊逸,無市井氣。”抒寫了他各個時期對生活對萬物的獨到感受,即使是他人詠歎過多次的題材,他也常常翻出新意。
其七絕,如寫于1959年的《登湘潭文峰塔題壁》:“巍巍古塔立湘洲,無數風帆競上遊。但向雲天書一字,化龍飛去不回頭。”構想新奇,既點明時代背景,又抒發了個人志趣,為未經人道語。又《夢遊綠天庵》:“綠天庵外雪初消,詩思春江二月潮。醉裡不知身是客,漫題新句上芭蕉。”作者夢中置身唐代狂僧書法家懷素故地,酒後竟忘記客人身份,将自作新詩題到園中懷素為練字而種植的芭蕉上了。另有《登北固山多景樓》:“高崖百尺枕江流,攬勝何妨獨上樓。日夜松風吹不斷,滄波洗盡古今愁。”等等,皆觸景生情,因情造境之作。
五絕如《明孝陵》:“孝陵空古今,五百年風雨。山鳥踏荒苔,雲煙自來去。”《山中偶得》:“嶽雲迷客屐,山雨響松溪。偶及泉邊坐,飛花落滿衣。”小詩中寓深意。
五律如《遊鼎湖山》:“飛瀑驚山鳥,清潭洗客心。石奇疑鬼扮,樹古作龍吟。徑險詩緣苦,幽亭酒意忱。北來二三子,相與共披襟。”《初遊開福寺題壁》:“開福千年寺,叢林出市寰。修心容補衲,頂禮愛逃禅。花放香盈樹,雲飛佛在龛。菩提蔭下坐,大地是蒲團。”讀來禅意盎然。
七律如《赤心》:“碧樹珊瑚手自栽,塗鴉畫虎等童孩。逍遙古法千家外,越過雷池一歩來。青眼但将秋水洗,赤心常寄筆花開。喜看世紀交新運,好趁長風舉酒杯!”《九秋回文》:“關松鎖日卧霜晴,石壁飛泉暗笛鳴。寒菊新秋三徑泠,曲溪古渡一舟橫。還鴉噪樹驚風晚,斷雁穿雲戀月明。閑歲蔔居村酒熟,山前醉客笑詩成。”更顯現出作者的詩詞功底與情境,殊為難得。
普安先生所作古風不多,如《杭州紀行寄西泠諸友》《印象武夷山水歌》,洋洋數十言,或一韻到底,或長短轉換,氣态軒昂,句式奇谲,篇長不勝引錄。
其它佳句如“繁華遊子夢,燈火故園情。”“夕陽紅一抹,帆影過千樓。”“平态生詩膽壯,一任海濤驚。”“山中塊壘神仙果,天上雲霞日月衣”“窺燈午夜失眠鼠,鬧曉春池初醒蛙”“騎牛歸去忘時晚,明月梅花共一龛。”“春蠶莫歎絲方盡,破繭還将化蝶飛。”結合袁枚的性靈,龔自珍的豪邁,又與元、明人集中詩詞類似。詩集中象這樣的佳句不絕于目,從普安先生創作的詩脈絡,可窺先生藝術全貌。(注1)
1997年,普安先生與“一代詩魔”洛夫合作,曆時三年,創作一套《詩魔之歌印集》。普安先生借用篆刻藝術形式表現洛夫先生的現代詩境,用古老的篆刻文字,表達漢字、詩境中的生命情态。形象思維,美學信念,兩者之間的聯姻,探索出一條篆刻與現代詩藝的融合和蛻變的新路。
篆刻藝術數百年來,特别是乾、嘉時期的複古大潮,将篆刻藝術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多元化表現形式,以書入印,印外求印等方式不僅豐富完善了傳統篆刻藝術的内涵,萬變不離其宗,用古體詩句入印,成為傳統的篆刻藝術古今不變的主流,赓續數百年不衰。而篆刻與西方形式的現代詩句碰撞,普安先生和洛夫先生于是有了創作《詩魔之歌印集》的想法,大膽地進行第一次成系統、成規模的嘗試。
篆刻作為抽象的文字元号來表現宇宙無窮奧秘,普安先生倡導汲取這股現代思潮,反悖之逆,直追三代,将現代意識與遠古荒漠的樸拙之風完美結合,深沉而亮麗、厚重而空靈,注入了充滿漢魏六朝那古典東方意境的詩情,使其千古一聚。就《詩魔之歌印集》的形式所表達的意境來說,普安先生僅僅刻了一半,另一半留給了一代詩魔——洛夫。孤獨與隔絕,中華文化相碰撞的現代詩,将那些原本有生命的無生命的,都賦予了新的生命。
《詩魔之歌印集》的成功,靈感來自普安先生對詩的喜好和投入,是普安先生找到用篆刻的表達方式來探尋詩的外延擴伸的足迹。在詩詞強大的基因催化下,普安先生的篆刻作品中自然了卓爾不群的格調,有了詩詞高吭激昂的氣息。
如白文印“春醒後我将以融雪的速度奔回”,作品采用了商周青銅器的布白和章法,參差錯落,字裡行間,用刀鑿上幾點不經意的殘缺,類似青銅銘文表面的斑駁,又恰好表達了洛夫先生詩中想要的畫境。(注2,下同。)
朱文印“井的暧昧身世,繡花鞋說了一半,青苔說了另一半”,一個大的“井”字,把繡花鞋和青苔想說的都收藏在裡面。映證了“應有前朝風月事,蒼苔猶印繡鞋痕。”(先生詩句)夢幻般的詩情畫意。
白文印“沉思的人比影子還冷”,用粗曠的白文線條刻畫出高冷的塊面,如詩人獨自坐在黑夜的窗邊沉思。
“一石一世界”(盛和民先生詩句),印集中還有許多優秀作品“雪祭”“月光房子”“火焰之歌”“葬我于雪”等等,普安先生均能用詩的語言,利用漢字“錯視覺”對篆刻意象帶來的新景觀,結果是令人心驚,詩的意境在形式上的蛻變,呼喚藝術門類跨界的突破與超越,《詩魔之歌印集》部分佳作準确地表達出新奇瑰麗的境界,自然而然地讓人所膺服。印面撲朔迷離,如真如幻。既有紮實的漢印功夫,又有行雲流水般的現代意識流,既沒有快餐式印風那種膚淺,也沒有文字在變形誇張中的故作姿态。筆觸熱情熾烈,充滿了鏽銅鑄鐵般的蒼老遒勁。印面極富動感,并有濃郁的裝飾性和繪畫感,強烈的視覺效果,像音樂對人的心靈沖擊與震撼,并試圖以文字元号來訴說現代人對東方古老文化的那份陌生感和隔離感。
篆刻走出一條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道路,拉近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距離,就是一次膽敢越過雷池的開端。《詩魔之歌印譜集》表現出來的語言,無論從靜态到動态,或者動靜相生相克,都能讓觀者讀懂詩,讀懂篆刻背後的人生,觸摸到宇宙萬物那些沒有時間和地域的界線。《詩魔之歌印譜集》是普安先生書法篆刻藝術裡程碑式的轉折點。
普安先生篆刻藝術遊刃于趙、吳、黃、齊四家而來,又别于四大家之外,他善于發現和挖掘明清流派印中的亮點,歸于已有。他的用刀,十分講究技法統一性和協調性。朱文鐵線篆和寬厚雄健的白文印,一般采用西泠八家的短切法充其骨格,以齊白石沖刀法保持流暢,或沖切兩結合。小的白文印,他一般采用沖刀法完成。他的印風保留了黃牧父靈犀的筆觸,舒展幽默,體态誇張;汲取了吳昌碩渾厚拙樸,寓方為圓寫意風趣;融入了趙之謙蒼秀雄渾,計黑當白的妙理;參透了齊白石大開大阖,亂石鋪階的運勢。使轉如筆,或潤含春雨,或燥裂秋風。既有畫理,又有詩境。并将自身坎坷不羁的人生感悟寫在紙上,刻在石中。故洛夫稱:“他是一位用刀在石頭上寫詩的印人,也是一位用石頭思考的詩人。”
普安先生的篆刻藝術,詩境成為他創作的主題調。從六十年代開始,普安先生就渉獵篆刻。七十年代末,他創作的毛澤東詞《憶秦娥·婁山關》組印在杜甫草堂展出,爾後又刻《銀河頌》印集陳列在杭州西泠印社吳昌碩紀念室。八十年代中期,他創作的《陋室銘》組印,以及九十年代着手對《漢印分韻合編》《缪篆分韻》等書的篆體字,進行系統化的審美重構。曆時數載,将趙之謙“以書入印”理論,化成自已獨特的“以印入書”之法,達到了以印篆的書風回歸到書法本源上來。
是以,普安先生“一筆之中見情性”,那些充滿個性的書法風格,就有了基調。早年,普安先生是以顔真卿的《勤禮碑》《大字麻姑仙壇記》兩碑入手,爾後上溯漢魏,特别是北魏摩崖、石窟中那些篆楷合一的造像字型,體态雍容,縱橫取勢,舒展自如,類《瘗鶴銘》之曠達清恪。然,中宮收緊,筆墨粗細變化強烈,顯然參入了自己的“書尊百衲禅心淡”的旨趣。作品如自撰詩立軸《雨湖小坐》、自撰聯“壽同松鶴/懷抱古今”、趙嘏詩聯“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等。
常以篆隸筆法作行楷書是普安先生一大特點。他的篆書作品就是一方大的朱文印,張馳有度,參差錯落,善用濃墨枯筆,滿紙充溢着金石之氣和書卷之氣。如篆書冊《詩品》、篆書聯“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等。達到篆書與篆刻高度的統一,是以,欣賞普安先生的篆書作品必須先從他的印譜入手,讀懂了普安先生的印,就讀懂了他的書法。
特邀入選湖南書法晉京展覽對聯
随着普安先生步入“杖朝之年,”“順乎自然,無為而治”(周谷城先生語),他對藝術的追求心态更趨從容淡泊。參見近期普安先生的書法作品,章法愈老彌堅,筆墨使轉不可方物。境界直達禅理佛道。有時偶爾畫上寥寥幾筆寫意,得吳昌碩、齊白石之精神,骨力雄厚,亦不落俗套。書畫同源。普安先生告訴我,他青年時從周磊村老師學畫山水,六、七十年代為稻粱謀常作寫意蘭竹石之類。八十年代以來克服種種困難,專心詩詞書法篆刻,筆簡意赅,于文字藝術抽象美之想象空間駸淫既深,亦極盡快樂之享受。“萬象在旁”,大道至簡,此時,對于具象的繪畫技法,反而覺得冗繁累贅了。
臨别,敖普安先生還告訴我,藝無止境,他還在做新的課題,以實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天人合一的理想。此行令我獲益匪淺,也深深感到,在當代,一位詩人能兼書畫篆刻,且取得較高藝術成就,其作品豈容輕視。藝術與人生,其中還有許多資訊需要後來者好好研究與诠釋。
注:(1)本文所引詩詞及相關評論,見敖普安著《攻玉室詩詞選》,2012年8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
(2)本文所引書法篆刻作品及相關評論,見2005年12月湖南美術出版社所出版《真水無香-敖普安書法篆刻作品集》及蕭建民《留住一徑斜陽——讀敖普安先生篆刻新作》一文。
(作者董赤宇 湖南省雜文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知名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