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曾是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西北王”。但在我的眼里,胡宗南却是一个不怎么会打仗的人。
1947年5月12日,胡宗南听到了我一篇专门评论他的评论,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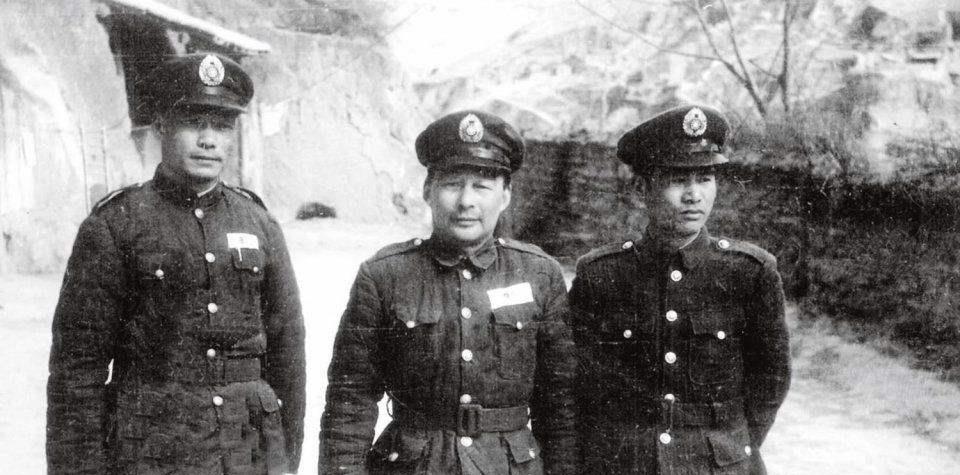
据说,胡宗南因此不再主动去看我的广播报纸,这时候,距胡宗南部首次进入我为其留下空城延安的3月19日,已近两个月时间了。在这两个月时间里,胡宗南虽说是“占领”了延安,却被整得焦头烂额,而且,分明还要焦头烂额下去。这个被我称为饭桶的将军,得为自己的吹牛付出代价。
说实话,作为“西北王”的胡宗南相对于民国其他将领,对延安还是比较了解的,又因为受命剿灭我,他还时常对延安做一些主动的了解,甚至,曾想来延安参观,但因被蒋所阻而未能成行。
毛主席说延安有“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ii]当时,胡宗南从广播里听到这话后,嘴上有些不服气,称:“只有老毛能吹这种牛!”现在,他来了,来到了延安,轮到他“吹牛”的时候了,但他却把这牛吹成了笑话。
胡宗南在占领空城延安前,就起草了一个《告陕北民众书》,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声称要彻底实行三民主义,要比我还革命。3月19日,他如愿以偿,虽说明知是一座空城,但他还是给蒋介石发去了这样的电报:“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蒋介石很快加电给他,电文如下:
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iii]
胡宗南在延安的吹牛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雪耻”了,把事情干大了,就得摆摆姿态、做做样子。首先,他成立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给当地老百姓发粮。老百姓们领取了白发的粮,他就派人去问:“国军好还是共军好?”对方不好直接回答,就说:“都好!”
派去的人逼问:“到底国军好还是共军好?”对方不说话了。问话的人没客气,直接给了对方一耳光:“白吃着我们的粮,让你说这么句话都说不出来!”对方说:“共军在这里那么久,从来没抽过我耳光……你们刚来就动手……你国军好还是共军好?”
这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胡宗南似乎并不在意,他还要准备接待中外记者。他指示下面的办事人员,既然“俘虏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就至少得有这样两个项目:一共军俘虏营;二缴获陈列室。但一没人二无缴获怎么办?只能靠自己的人和武器填充。
胡宗南抓到了500当地百姓,又将自己的1500士兵填充其中,开始化妆、训练,要将他们一起变成我军俘虏。对于缴获武器,以三八式和汉阳造为主,把部队能找来的都找来,能抽调的都抽调出来。但这么一做问题便出来了——因为武器“无数”,那么多当兵的没了枪咋办?想来想去,胡宗南想到了一个办法——贴条——给那些武器上贴上条子,写上缴获时间与地点,“调”了谁的武器,谁就得记住这个时间、地点,这样就不会乱,白天抽调来陈列室,晚上再发回去。
接下来就是对“俘虏”的训练和起草陈列室的参观解说,陈列室的武器是死的,不会说话,解说词相对来说简单,就一个词的连续应用——编、编编、编编编。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反正就是胡编、乱编、瞎编,不会出大的漏洞。但“俘虏”的事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活人,得会说话,要接受记者采访,而且,要跟真的一样,多少有一些难度的。
胡宗南为了把这事儿做得像模像样,对其进行了检查,预先设计好的被采访对象是一位被俘旅长。胡宗南问话“旅长”:“你们那边怎么样?”“旅长”立正报告胡长官:“总统的……很好!”胡宗南说:“这不是共军,一张口就是我们的人,不行不行!”随后指示手下的人接着训练。
手下的人把“旅长”叫到了一口窑洞里,设计了很多的对白给“旅长”,直到“旅长”能应答自如,还不放心地说:“要是遇到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你回答不上来,就闭嘴不谈,装没听清,装傻。”又把“旅长”带到了胡宗南面前,胡宗南问了几句,基本凑合,让“旅长”回“俘虏营”,却对训练“旅长”的人表示了不满:“你们想想,共军的旅长在提到总统时,还能叫他总统吗?得叫蒋介石,要骂,明白吗?”训练的人心领神会,终于把“旅长”给训练成功了。
再接下来,胡宗南又得面临一个问题,“俘虏”只有2000人,可“俘虏营”要十多个,这2000人怎么能填满十多个“俘虏营”呢?他指示手下人让“俘虏”们轮流坐庄,记者们参观采访这个“俘虏营”结束,动用汽车将“俘虏”们快速送至下一“俘虏营”,再次面对记者。这样,每一个“俘虏营”中也就都有了“俘虏”,而且源源不断,没有准备好几万人的必要。手下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同时给胡宗南出了一个好主意——“俘虏”不能光有活的,而且还得有死的——得有大量的假坟,以证明胡部拿下延安的惨烈。
胡宗南爽快答应,延安的国军因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坟运动”,为了把假坟做得逼真一些,他们还砍了不少树,做成木板,以“墓碑”的形式记述了国军是在何时何地消灭那些“共军”,白白的木板,黑黑的字,清楚得就像历史,让没有经历过的人也可历历在目。
4月初,记者们来了,共55人,分属39家媒体,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前来报道胡宗南部攻占延安的“陕北大捷”。但胡宗南部对“俘虏营”的操作却出了问题,露馅了,被他们训练出来的“旅长”在接受第一次采访后,被运送到了下一个采访点,正准备再次接受采访时,却被记者们认了出来:“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采访过的那位吗?”“旅长”立即想到了训练之人教会他的“闭嘴不谈”,把自己憋得满面通红,憋成了一个直不楞噔的、多少有些发胖的木头柱子。
怎么办?胡宗南想到了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他给了那些记者们“封口费”,把“陕北大捷”的事真正给“吹”了出去,自己也开始在这些“胜利的消息”里享受生活。这时,他对我给他的败绩采取了不上报的办法,如我给其痛击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他都没有上报。他抽时间结婚,还接受西北地区国民党各系统来延安的慰问,为此,有人甚至提议把延安改为宗南县,“以表彰胡长官克复延安的伟勋”,他不但默许,而且还等待着这被送到南京的提议传来被批复的好消息。
8月7日,胡宗南等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乘坐着美龄号专机飞临延安,随即,被重兵接送到延安城内最好的、戒备森严的边区外交宾馆。胡宗南不但在此前从西安运来了蒋介石的生活用具,澡盆、餐具、马桶,还找到了一些会唱歌的人,搞了一个“入城仪式”,让他们高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狠拍蒋介石马屁。那些人大多是当地的老百姓和学生,唱着唱着就把这歌给唱了回去,唱成原来的样子——他们甚至不知道蒋中正是谁,他们的心里只有毛主席。
对于这一点,今天很多文章都有显示,但具体说法不一样,一种是说蒋介石坐在车上没听见;一是说蒋介石听了心情大好。但不管是听见还是没听见,不管是唱回去了还是没唱回去,人们都能看到胡宗南吹牛和拍马屁的功夫是十分了得的。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延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来延安,他大概没想到他受到的盛大的欢迎方式,其实是胡宗南刻意营造出的一种不诚实的虚假的热烈。
当夜,蒋介石给胡宗南及其得力下属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他来到枣园,看见了毛主席住过的那口窑洞,“只见它与当地农民住的窑洞没有两样,门窗是没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的”。这里有许多喜欢情感处理的文学作品:
尽管蒋介石对毛泽东等人的情报十几年来一直没中断过。此时此刻,面对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怎么也无法想象老对手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如何有效地指挥着千军万马,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如此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蒋介石惊讶毛泽东的意志,感叹他的毅力。跟从他一起观看的侍卫们,也是一个个感叹不已。 [iv]
实际上,这些描述对蒋介石而言就一句话: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国军还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打胜仗?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让蒋介石的心情变得很糟,当天他就离开了延安。我们想说的是,当年的蒋介石一定和胡宗南一样,知道延安的十个没有,但他们分明没有把这些“没有”当回事,所以,在后来也便只能迎接千万里的大溃败,而老百姓们要唱的永远不会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
[i]《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
[ii]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
[iii]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iv] 《蒋介石的延安之行》,延安政府网,2013年11月14日。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快来关注西部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