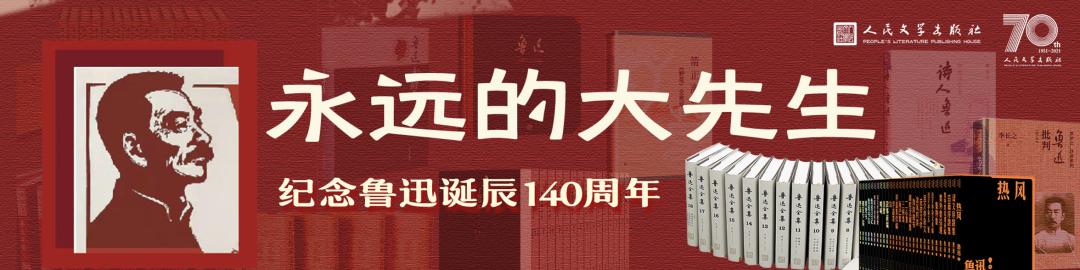
人文學會的Sage先生和Lu Xun先生
|郭偉
《新文學史》主編、主編
我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和魯迅全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馮雪峰校長與魯迅先生早年的密切關系。
馮雪峰,我們社會的第一任主席,不僅是文學史上的人物,也是黨和軍隊史上的人物。年輕時,他是一個溫柔的"湖上詩人",但在1927年決心入黨的那場血腥事件中,他參加了長征,在上饒集中營度過了國民黨監獄;蕭紅在家中遇到了魯迅,一個神秘的人物,帶來了紅軍的消息。馮雪峰率黨到滬,秘密上司文藝運動,促進文藝界團結,赢得魯迅的信任,增進魯迅對黨和紅軍的認識。早在江西蘇區,他就和毛主席燭夜談盧迅。可以說,他是黨和魯迅之間的橋梁。
1931年,為了抗議國民黨反動派殺"左聯盟"五位烈士,魯迅和馮雪峰等共産黨人一起編纂了《前哨》(紀念戰死者),據薛峰回憶,大部分是在深夜,薛峰到魯迅家,告訴他什麼文章,以及缺少什麼樣的文章和需要多少字, 魯迅道:"我湊了一下。"或者從桌子上拿出已經寫好的文章,說有多少字,然後那裡有多少字,他會再寫一點。就這樣,在白色恐怖的黑夜裡,兩個固執不屈的人聯手,向反動暴政揮舞着槍口。之後,兩人還興奮地帶着家人到照相館拍照,以紀念這次不尋常的合作。這經血火的考驗,可謂是生與死的轉折。
1931年4月20日,魯迅一家和馮雪峰的家人在上海被拍到
魯迅晚年寫的幾篇重要文章,由馮雪峰起草。魯迅的葬禮也是由上司上海地下黨的馮雪峰組織的。後來在2003年馮雪峰夫婦的墓葬在他的家鄉義烏落成,魯迅的兒子周海英向朱(金字旁容)基總理要題上薛峰墓碑,他本人為馮雪峰夫人墓碑碑,海英說:馮雪峰和我家有着深厚的根基。
1931年,馮雪峰将離開上海前往蘇聯地區,魯迅的标題
說到這裡,人文學會第二任會長王仁叔叔(Ba)也與魯迅有關。1936年6月,他在李報上發表了《祝高爾基和魯迅健康》一文,病态的魯迅看到,曾稱贊馮雪峰:"讀王叔叔的文章......他說,高爾基的憎惡是巨大的。魯迅的批評和諷刺,并不是正義的大怒——魯迅宣讀了王仁叔叔對自己的了解。王仁的叔叔尊敬1939年創立魯迅風的魯迅,在文中寫道:"魯迅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今天,我們真的還沒有找到第二個人。那時,魯迅已經三歲了。魯迅的追悼會,王仁叔叔出席,簽字,抗日戰争爆發後,大批文化人離開上海到後方,他留在"島"繼續鬥争。他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出版委員會主任之一,與鄭振軒、徐廣平共同起草了全集編輯計劃,承擔了大量的編輯工作,徐光平在全集編輯後記中有這樣一句話:"緻鄭振軒, 王仁舒二先生
徐廣平、巴人、王克甯、周海英(從左至右),攝于1949年北京飯店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建設工作全面開展。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掌舵人,代表新文化方向,十分重視政府出版他的作品。當時,馮雪峰受命在上海主持魯迅圖書編輯機構的工作,起草《魯迅工作編輯及注釋工作指南和計劃》,并很快調動了楊宇雲、孫宇、林晨、王世軒等知名魯迅研究專家,專門從事收集、整理、 魯迅作品注釋。
這些專家,和魯迅也有這樣的聯系。比如郵局的"信件檢查員"孫我們,自學了世界語和英語,翻譯了勒曼托夫的六首詩,寄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很快回信,并在他的編輯《奔潤》中發表了其中的四首,極大地鼓舞了内向的青年,使他翻譯得更勤奮,他翻譯了達菲的長詩《勇敢的約翰》, 魯迅以為"譯本很好",為張羅出版,卻一再在書商中釘釘子,魯迅抱怨:"書是為盈利而設計的,不好,這能使中國沒有好書"(1931年5月4日到孫),曆時一年半,找書店并不容易, 也為銅版插圖出于經濟原因不能印刷色彩,不得不印刷單色而後悔,而出版進度則令人焦慮:"中國的工作,真的很慢,如果印刷Zola(Zola)收藏,恐怕需要一百年。"(1931年10月5日到孫)看魯迅的信,魯迅為這個翻譯傷心欲絕,他看了看校樣,預付制版費,為譯員考慮翻譯費和印花稅等等——這麼小的事情,像魯迅這樣偉大應該花精力去做嗎?年輕的太陽一定想了無數次。魯迅做得如此有效。他一直認為翻譯是"偷火",主張"要麼拿不拿",就像他對魏素遠和此後對曹敬華所做的那樣。他這樣做是為了中國的進步,為了後來中國人能"幸福,合理的生活"。
(星期日) (1902年5月18日 — 1983年10月3日)
婁世毅,人文學會副主編、副會長,是1930年代被魯迅所熟知的年輕左翼人士。1933年秋,他在南京被特工綁架,準備遠東反戰大會,并被判處無期徒刑。魯迅在給朋友發消息後得知:"對的哥哥生病了""哥哥還活着",動員社會名人蔡元培等人搶救...婁世毅通過表哥聯系魯迅,打開了一長串的書單,準備在監獄裡學習,魯迅努力趕快滿足他的要求,讓他覺得自己成了"有錢人"。魯迅向他保證:如果沒有,就翻譯。他确實通過秘密管道翻譯了日本高爾基的《在地球上》、《文學的修養》、志賀的《篝火》等譯本,交給魯迅和朋友們幫忙出版。魯迅稱贊他的翻譯很好,沒有翻譯腔。在他的晚年,婁世頤相當年輕時對魯迅先生工作而内疚,永遠不要忘記魯迅給他的恩典。雖然在出版社負責外國文學,沒有直接從事魯迅作品的出版,但他是魯迅精神的對待作品。
婁石屹 (1905年1月3日—2001年4月20日)
古典文學主管副總編,在20世紀30年代與魯迅密切接觸——魯迅先邀請小軍、蕭紅來上海吃飯,自己信任的毛敦、胡峰等人介紹給他們,齊在場。他是一個陌生的人,他不修剪,不局限于小段,但大事不混淆。他先後就讀于黃埔軍校、蘇聯南洋下部,也曾在日本留學,當過軍人、編輯、記者,他加入了左翼文學運動,作文寫得漂亮,被譽為魯迅之後寫得最好的人。20世紀30年代,他編輯了《巫師》,魯迅的散文集《蕾絲文學》多篇報道,最初被放入《巫師》出版。後來魯迅跑了《海燕》,齊和胡楓是他的左臂右臂,魯迅晚年的幾篇作文也在上面發表。魯迅死了,龔是棺材的支援者之一。雖然後來雪峰會長安排他負責古典文學的出版,但他始終貫徹魯迅精神的傳承。晚年,他以寫舊式詩聞名于國内外,"一山田野有幾根殘縧,五路米需要千倍腰","文章信口女黃奕,心思圓錐心直白"......這些奇異的詩作,收入《散落益生詩》出版,被譽為千古古歌,頗具魯迅詩意和精髓的文字。
(1903年1月28日-1986年3月26日)
人文社團的聖賢和魯迅先生有着如此密切的關系,似乎注定要失敗,《魯迅全集》的出版是人文社團的使命,而魯迅的聖賢精神傳承,也必須鑄就人文社會的風氣和氣質。
魯迅的精神力量、人格魅力、靈感、振奮人心的中國人,熱切地親近他,汲取智慧和勇氣,傳播他的思想——編輯出版他的作品,為《魯迅集》的編輯出版和有效,是幾代編輯為榮耀做準備的。
孫宇是第一個調查魯迅所有作品的人。逐字逐句地對照作者的手稿或初稿時的報紙進行核對,確定魯迅的作品準确呈現。
楊玉雲死後癡迷地收集魯迅的散文,舊式詩歌雖然自謙,不重視自己的詩歌,但是因為有像楊雨雲癡迷于尋找魯迅的文字,就會有魯迅的"設定拾起其餘的補充",讓《魯迅集》更加完整。
"全套"的品質主要取決于三點:一是文章是否完整,二是文字是否準确,三是是否有評論和評論。
2005年版魯迅《全集》(18冊)
為了讓廣大讀者閱讀魯迅的原著,了解其思想内涵,非常有必要對魯迅的寫作背景、古今人物、曆史事件與社會、書籍、報紙甚至典故、名物、方言、引文等進行評論,盡量加以注釋和反駁, 但是注釋工作非常困難。林辰、王世軒是早期進入魯迅領域的研究專家,多年來積累了豐富的知識——林晨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了《魯迅的故事測試》,王世軒是中國第一位《魯迅傳記》的作者,他們無疑是注釋魯迅作品的合适人選。
1951年春,上級任命馮雪峰為社長,創辦人民文學出版社,将上海的《魯迅書編》遷至北京,成為我們社會的基石。
在那之後,你可以想象,這樣一些感受過魯迅精神之火的人,聚在一起,會發揚出怎樣的熱情和誠意,努力出版魯迅作品的最佳版本!
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之際,尼山結束了對中國的通路。右起:馮雪峰、奈山完畢、徐廣平、婁石一、王世軒、楊偉雲、孫,時文學出版社外語編輯部的日文翻譯編輯,暫時擔任翻譯,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名字。
此後,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帶注釋的10卷魯迅文集,16卷的魯迅文集,最權威和最具影響力,18卷魯迅收藏,于2005年進行了修訂。一代又一代的編輯付之火,編輯修訂,《魯迅合集》不斷完善,更完整、更準确的學校調查,更準确的評論,成為我們社會的瑰寶。
此外,針對不同的讀者,滿足各種閱讀魯迅作品單行、選集的需求,學生閱讀書籍、插圖、信件集、翻譯集、古叢書、關于魯迅的回憶、傳記、魯迅研究專著、魯迅詞典、魯迅相冊等書籍,幾十年來不斷出版,形成了魯迅主題的叢書群, 傳播魯迅之火之靈。
寫在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