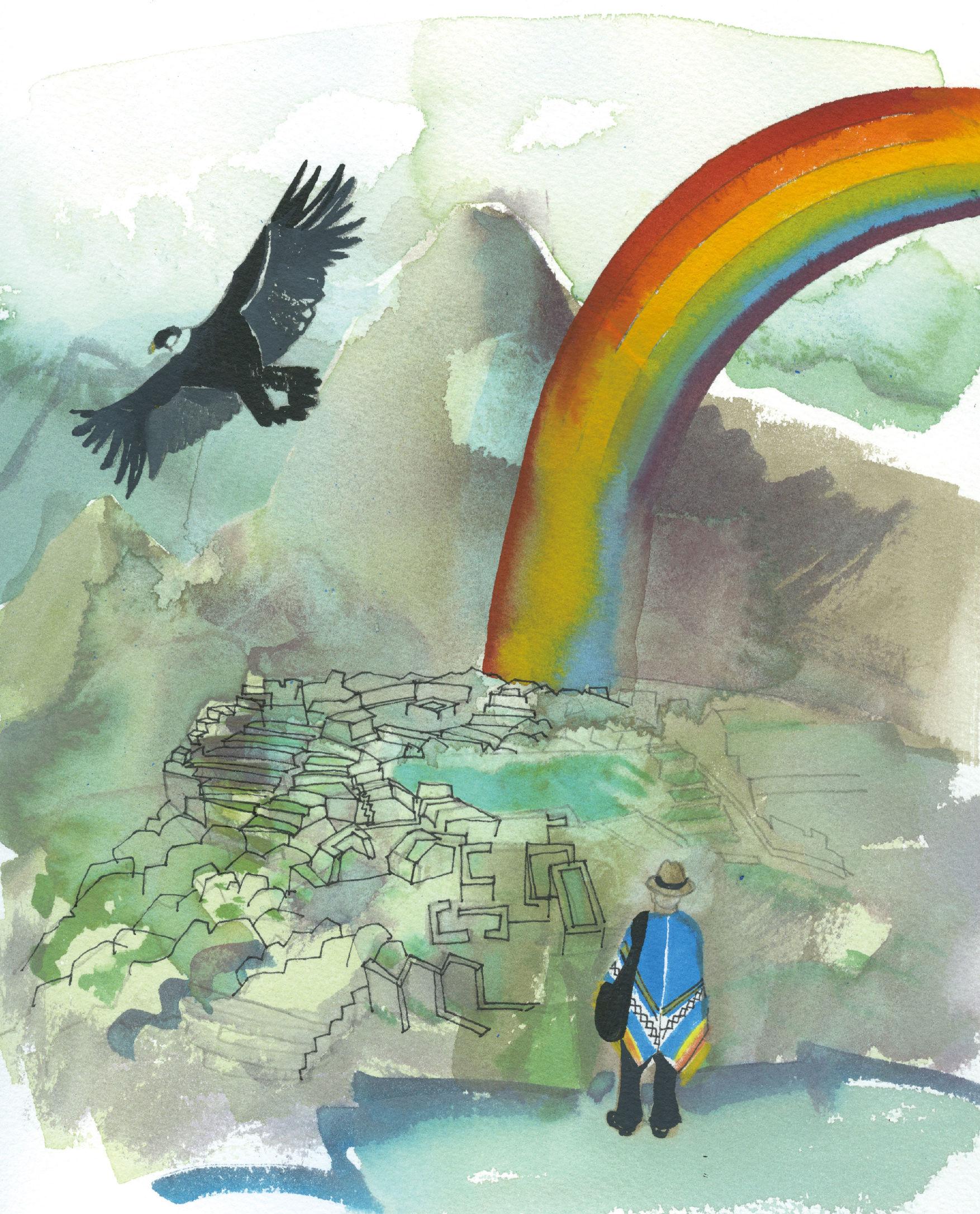
在法國南部旅行,每一頓都是佳肴,但吃了三天,就想念中國菜,其實也不一定是咕噜肉或魚蝦蟹,主要的還是要吃白飯。
意大利好友來港,我帶他到最好的食肆,嘗遍廣東、潮州、上海菜,幾餐下來,他問:「有沒有面包?」
「中餐廳哪來的面包?」我大罵。
他委曲地:「其實有牛油也行。」
剛好是家新加坡餐廳,有牛油炒蟹,就從廚房拿了一些,此君把牛油放在白飯上,來杯很燙的滾水沖下去,待牛油溶了,撈着來吃,這是意大利人做飯的方法,也隻有讓他胡來了!
百種米,養百種人,這句話說得一點也沒錯,況且世上的米,不下百種。
我們最常吃的是絲苗,來自泰國或澳洲,看樣子,瘦瘦長長,的确有吃了不長肉的感覺,怕肥的人最放心。日本米不同,它肥肥胖胖,黏性又重,是以日本人吃飯不是從碗中扒,而是用筷子夾進口,女性又愛又恨,愛的是它很香很好吃,恨的是吃肥人。
香港的飲食,受日本料理的影響已是極深,就連米,也要吃日本的,我們的旅行團一到日本鄉下的超級市場,首先沖到賣米的部門,回頭問我:「那麼多種,哪一樣最好?」
價錢不是他們的考慮之中,反正會比在銅鑼灣崇光百貨買便宜,我總是回答:「新潟縣的越光,而且要魚沼地區生産的,有信用。」
但是魚沼米還不是最好,最好的買不到,那是在神戶吃三田牛時,友人蕨野自己種的米,他很懂得浪費,把稻種得很疏,風一吹,蛀米蟲就飄落入水田中,如果貪心,種得很密的話,那麼蛀蟲會一棵傳一棵,種出的米,表面要磨得深,才會好看。這一來,米就不香了,他的米隻要略磨,是以特别好吃。
向他要了一點,帶回家,怎麼炊都炊不香,後來才發現家政助理新買了一個電鍋,國産的,炊不好日本米來。
不過這一切都是太過奢侈,從前在日本過着苦行僧式的生活時,連日本米也不舍得吃,一群窮學生買的是所謂的「外米 gaimai」,那是由緬甸輸入的米,有些斷掉了隻剩半粒,那麼粗糙的米,日本人隻用來當成飼料,我們都成為畜生,但當年是半工讀的,也沒什麼好抱怨。
念完書後到台灣工作,吃的也是這種粗糙的米,他們叫為「在來米」,不知出自何典,那有什麼蓬萊米可吃?
蓬萊米是日據時代改良的品種,在台灣經濟起飛,成為四小龍時,才流行起來。口感像日本米,如果你是台灣人當然覺得比日本米好吃,我試過的蓬萊米之中,最好吃的是來自一個叫霧社的地區,那裡的松林部落土著種的米,真是極品,但怎麼和日本米比較呢?可以說是不同,各有各的好吃。
始終,我對泰國香米情有獨鐘,愛的是那種幽幽的蘭花香氣,是别的米所無。這種米在越南也可以找到,一般米一年隻有一次收成,越南種的有四次之多,但一經戰亂,反過來要從泰國輸入,人間悲劇也。
歐洲之中,英國人不懂得欣賞米飯,隻加了牛奶和糖當甜品,法國人也隻當配菜,吃得最多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前者的大鍋海鮮飯 paella聞名于世;後者的 risotto混了大量的芝士,由生米煮成熟,但也隻是半生,說這才有口感 al dente,其中加了野菌的最好吃。
意大利人也吃米,是從《粒粒皆辛苦 bitter rice》一片中得知,但那時候的觀衆,隻對女主角施維娜•瑪嘉奴 silvana mangano的大胸部感到興趣,我曾前往該産米區玩過,發現當地人有種飯,是把米塞進鯉魚肚子裡做出來,和順德人的鯉魚蒸飯異曲同工,非常美味。意大利人還有一道鮮為人知的蜜瓜米飯,也很特别。
亞洲人都吃米,印度人吃得最多,他們的羊肉焗飯做得最好,用的是野米,非常長,有絲苗的兩倍,炒得半生熟,混入香料泡過的羊肉塊,放進一個銀盅,上面鋪面皮放進烤爐焗,香味才不會散。到正宗的印度餐廳,非試這道菜不可,若嫌羊膻,也有雞的,但已沒那麼好吃了。
馬來人的椰漿飯也很獨特,是第一流的早餐。另有一種把飯包紮在椰葉中,壓縮出來的飯,吃沙爹的時候會同時上桌,也是傳統的飲食文化。新加坡人的海南雞飯,用雞油炊熟,雖香,但也得靠又稠又濃的海南醬油才行。
至于中國,簡單的一碗雞蛋炒飯,又是天下美味。
不過吃飯,總得花時間去炊,不夠用面粉團貼上烤爐壁即刻能做出餅來友善。
但大家是否發現,人一吃飯,就變得矮小呢?中國人的子女一去到國外,喝牛奶吃面包,人就高大起來。日本人從前也矮小,改成吃面包習慣後才長高。印度尼西亞女傭都很小,如果她們吃面包,一定會長大得多。
吃飯的人,應該是有閑階級的人,比西方人來得優雅。高與矮,已不是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