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流傳有兩部被稱為《朱子家訓》的作品,一為宋代大儒朱熹所撰,二為明末清初理學家朱用純所撰。朱熹撰著原名《家訓》,載于朱氏宗譜,因朱熹的尊稱而得名《朱子家訓》或《朱文公家訓》。朱用純撰著原名《治家格言》,在流傳中被稱為《朱子家訓》,且誤傳為朱熹所撰。雖然二者的創作時間、文本内容、體例風格各不相同,但因作者同姓且均為家訓作品,以緻世人混淆。有些學者認為順應世俗習慣,二者都可稱作《朱子家訓》。這種說法是存在争議的。
《治家格言》誤名始末
朱用純(1627—1698),明末清初昆山人,為朱熹後裔,其所撰《治家格言》500餘字,以“黎明即起,灑掃庭除”開頭。朱用純的生活經曆和心态是他創作《治家格言》的動因。朱父集璜因拒降清軍而投河自盡,朱用純取西晉王裒“廬墓攀柏”之孝以自号“柏廬”。他為繼父志,終身未入仕途,以教授學生、著書為業;及至中年撰寫《治家格言》貼于廳堂以自勉并規訓家人,故未署名。朱用純生前著述中也未收錄此作品,可見無意擴散。《治家格言》由于世人的贊揚、推崇或誤解,被易名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家訓》《紫陽朱子家訓》(紫陽為朱熹别号)等,以緻随後百餘年間誤傳為朱熹所作。學界對誤名之因有如下幾種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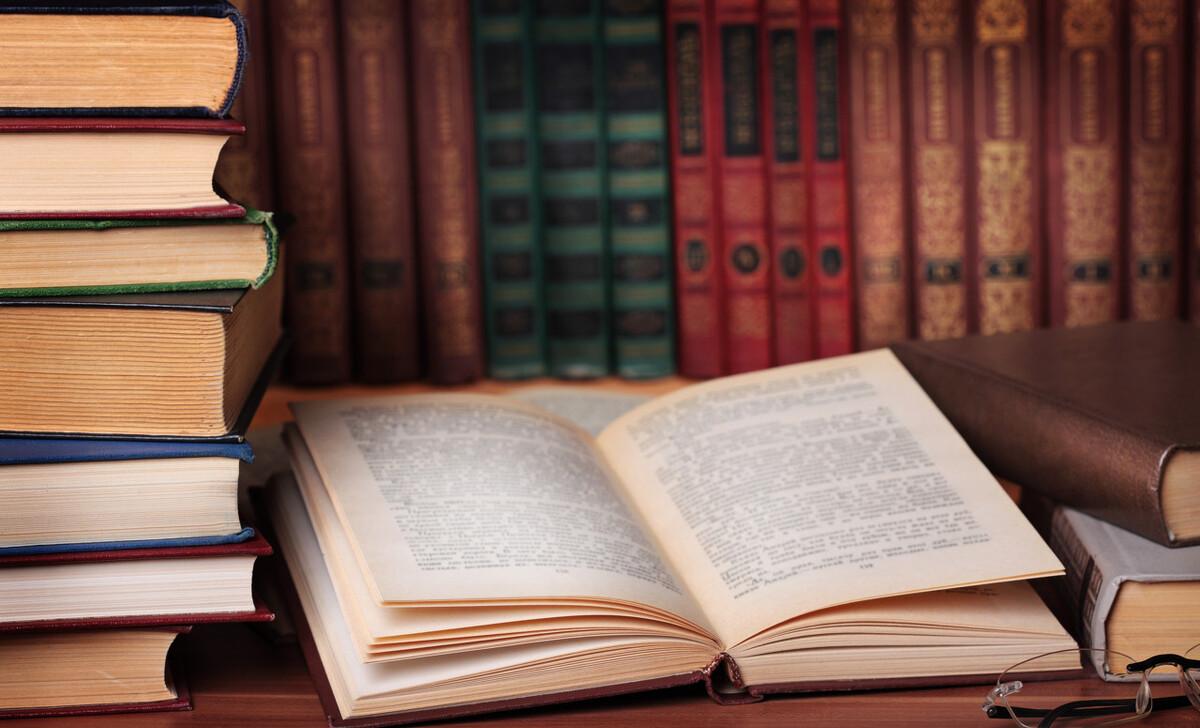
其一,朱氏之姓說。《治家格言》雖不以“家訓”為名,但實際上是一部格言體家訓。朱用純因自謙而命名“格言”,似有引聖賢之言以自勉的意味。朱用純的宗叔朱大滿為《治家格言》題對聯:“鹿洞談經傳千秋師表,柏廬繼志垂一脈家規。”并制成匾額挂在牆上。這是出于對朱氏精英的褒揚,将朱用純與曾在白鹿洞書院傳道授業的聖賢朱熹并提。“朱子”的聖賢之名可增益《治家格言》的魅力,在傳抄的過程中有人将錯就錯,稱其為《朱子家訓》。清代嚴可均為朱用純作傳時指出:“其最傳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懸之壁,稱‘朱子家訓’,蓋尊之若考亭焉。”(考亭亦朱熹别号)可見,有人出于贊揚,欲奉朱用純為“今日之紫陽”,進而稱其撰著為“朱子家訓”。
其二,弟子撰書說。朱用純有一弟子名顧易,他為闡釋《治家格言》編寫了一部《朱子家訓演證》。因古代社會“子”亦适用于尊稱老師或有道德、有學問的人,作為學生有可能将朱姓老師稱為“朱子”。朱用純是一位頗有學識的儒者,長期教授鄉裡,得人敬重。顧易出于對恩師的尊敬及其學問的推崇,便稱《治家格言》為《朱子家訓》,此處“朱子”之稱有尊師的意味。後人失之考察,誤以為“朱子”就是指稱朱熹,由此導緻以訛傳訛。
其三,他人誤解說。《治家格言》未署名是引起誤名的一個重要原因。朱大滿所題對聯引發了後人的聯想、猜測和誤解。朱熹曾在白鹿洞講學,也曾寫過“家訓”,世人便誤以為《治家格言》乃“新安朱熹所作”,連同清代著名學者陳宏謀在輯錄《五種遺規》時亦稱《朱子治家格言》為朱熹所撰。清代和民國年間将《治家格言》作為勸善書大量印行,贈閱普通群眾,其中多以“朱子”為題名。有闡釋性作品如朱鳳鳴《朱子家訓衍義》、上海宏大善書局石印本《朱子家訓白話句解》等;有插圖本如上海昌文書局《繪圖朱子治家格言》等;更有清代金國均《朱子家訓試帖》以詩句解讀原文。此外,許多名人的書法作品傳播甚廣,如林則徐手書《朱夫子治家格言》等。這些無疑都加深了人們對《治家格言》作者和命名的誤解。
《朱子家訓》的得名與傳播
朱熹(1130—1200)是繼孔孟之後的一代鴻儒,其思想不僅被後世奉為官學,更遠播海内外。早在朱用純出生前400多年,朱熹已撰《家訓》,僅300餘字,以“君之所貴者,仁也”開篇。不同于先前傳統家訓的鴻篇巨制,朱熹将廣大精微的義理融進日常生活的道德實踐中,開創了精煉、質樸又兼具哲理的傳統家訓體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訓》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首先,從作者稱謂看,“朱子”乃世所公認對朱熹的尊稱。朱熹視童蒙教育為道德教育的起步與基礎。面對宋朝社會秩序的動蕩,朱熹希望通過童蒙教育和家庭倫理建設以重建社會道德體系。其弟子黃幹有言:“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家國。聞時政之阙失,則凄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朱熹晚年為訓示家族子弟而作《家訓》,常載于朱氏宗譜而被族人奉作修身、齊家、處世的“聖經”,後因朱熹的尊稱,而得名《朱子家訓》。
其次,從學術思想看,《家訓》從屬于朱子思想體系。童蒙教育是朱子思想體系的重要構成。從束景南先生所說的“人本主義的四書學體系”來考量,可見朱熹将教“理”與教“事”相統一,認為“國小是事”,即教導依照規矩行事,而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故而,朱熹不僅對講明德之道的《四書章句集注》着力甚深,還創作了以灑掃、應對、進退等日用涵養之道為主要内容的《國小》。據此,朱熹亦認為家庭教育中“理”與“事”皆不可偏廢,《家訓》側重闡發義理,另有撰著《朱子家禮》《童蒙須知》等篇目則言明具體的行為規範,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日用與義理互相補充的童蒙教育思想體系。
最後,從文化傳播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訓》遠揚甚早。《家訓》最初僅限宗族内傳習,載于《紫陽朱氏宗譜》中,屢經重修并世代相傳。及至明清時期,亦收錄在朱氏後人朱培、朱玉分别刊印的《文公大全集補遺》和《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中。清初,朱熹撰著《朱子家訓》之名已遠播海外,遺憾的是并未在宗族之外引起社會大衆的注意。廣大世人未得見《朱子家訓》真顔,客觀上也導緻了《治家格言》的誤名。
循名責實的曆程
《朱子家訓》和《治家格言》是中國傳統齊家思想的活态傳承,蘊含着豐富的道德教育和家庭治理等方面的思想智慧。辨正名稱不僅是為了識别兩部家訓本身,更是實作其文化價值發掘的必要前提。
第一,考證作者。清代學人多方考證,澄清《治家格言》為朱用純所作。1785年,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就說:“《朱子格言》系昆山朱柏廬所作,非文公也。”其後又有翁方綱《複初齋文集》指出:“國朝《朱子家訓》于日用事為頗極切要,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廬名用純所作,世乃訛傳為朱文公家訓,竟不知柏廬矣。”以上均未改變“朱子”的題名。及至1880年,金吳瀾等考編《朱柏廬先生編年毋欺錄》,在序跋和注釋中始複稱《治家格言》。如與朱用純的另一撰著《勸言》相比較,就會發現《治家格言》可謂《勸言》的姊妹篇,從兩書在思想上的一緻性亦能證明《治家格言》為朱用純所作。後世鄉人推崇朱用純的學識和為人的氣節,建造紀念朱用純祠堂,将《治家格言》刻碑鑲嵌于祠堂壁上,撰寫題跋表明作者身份,都成為推動《治家格言》正名的重要實踐。
第二,辨識文本。《治家格言》雖在清代已被證明是朱用純所撰,但至今仍未阻斷其被誤稱為《朱子家訓》的情況,許多出版物也沿襲這種稱謂,似未從根本上明晰二者的關系。《朱子家訓》篇幅略簡且創作年代更早,立意更高也更具哲理性,從理學思想高度融合了社會基本的倫理規範。《治家格言》則叙述細緻、話語通俗,蘊含着豐富的人生道理和生活經驗,具有對仗整齊、合轍押韻的優點。二者并非毫無關聯,而是在思想義理上一脈相承,《朱子家訓》傳達的醇厚理學思想也深刻影響着《治家格言》的創作。作為理學家的朱用純必定繼承了祖先朱熹提倡的治家思想,而撰寫出深受世人喜愛的《治家格言》。
第三,守慎正名。中國傳統認為“名”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性問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是消除學術争議和疑惑的關鍵。《朱子家訓》和《治家格言》的廣泛流傳說明二者在傳統家訓史中都具有極高的地位、影響和價值。故而辨正名稱,将《朱子家訓》作為朱熹撰著專名,還複朱用純撰著《治家格言》之名,以阻斷誤解和誤用帶來的困擾。
【本文系福建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朱子禮學現代性诠釋研究”(FJ2019C027)階段性成果】
(作者機關: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蘇珍
歡迎關注中國社會科學網微信公衆号 cssn_cn,擷取更多學術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