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卷首語</h1>
曾當過偉人秘書的胡鼎新(筆名喬木),他就很清楚為何陳伯達會受到重用。
王夢奎(曾被胡老邀約做其秘書,但被婉拒了)在和胡老聊天的時候,就詢問過這個問題。
得到的答案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不怎麼熟悉馬列文獻,而我們的理論和政策,是要和馬列文獻緊密銜接的,是以就要用到陳伯達這種熟悉相關文獻的人”
“也不是說别的人就不能寫了,比如我也能寫,但我們這些人都不是科班出身,一來沒有陳伯達熟悉,二來也沒他了解得深刻。陳伯達在蘇聯系統學習過,是正經的科班出身,再加上他又有很紮實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這種人才正是所需要的”
在偉人衆多的秘書當中,陳伯達是跟随時間最長的一個,但他的平步青雲,并不是依靠時間累積起來的。因為靠着兩把刷子,陳伯達才脫穎而出,成為首席秘書,這兩把刷子就是:
第一把刷子:他有着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學識;
第二把刷子:他是正經的科班出身,熟悉馬列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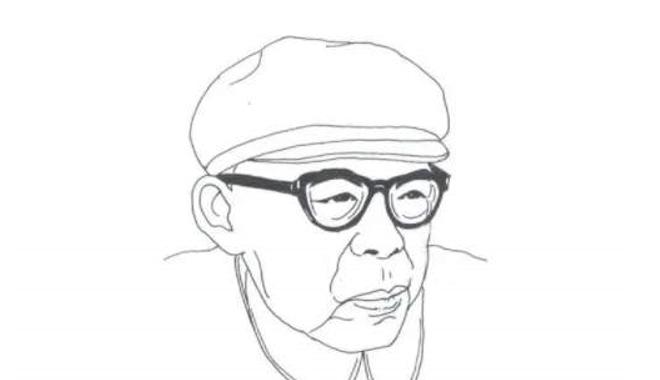
陳伯達素描像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1">早年經曆</h1>
陳伯達出生于福建惠安嶺頭村,家裡也算是個書香門第之家了,雖然是個已經破落的秀才家庭。
陳伯達17歲就畢業在老家的國小工作,當了一名國小老師,過了一年後跑到廈門,還是當國小老師。
這時候的陳伯達還是個幼稚的文藝青年,得益于出生于秀才之家的緣故,他從小就打下了很堅實的古文化基礎。
二十歲的陳伯達,在《現代評論》這本雜志上,發表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篇小說:《寒天》;這篇小說我有幸拜讀過,文筆确實不錯,隻是内容嘛,寫的是青春期男子和男子之間,那一份比較朦胧的好感。
有意思的是,從此以後陳伯達就再也沒寫過小說了。
這也說明陳伯達其實并不想做一個單純的文人,自古文人學而優則仕嘛,不過他也不想當一個純粹的政客;那麼,他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其實就是政治家和文學家的結合:一個“文名滿天下”的政論家。
你若是要他像一個政客那樣,四處演講說話,那是要不得的,就他說着一口閩南語,别人聽不懂,别人着急,他也着急。
1927年年底,陳伯達被選派到蘇聯進行學習,他進入到莫斯科中山大學, 被配置設定到了一年級二班。
在前往莫斯科的火車旅途上,陳伯達結識了一個女子,為期十來天的旅程,讓兩人之間的愛情也開始發芽,并在異國他鄉開花。
這一次在蘇聯的鍍金經曆,也為陳伯達日後的飛黃騰達埋下了伏筆。
晚年陳伯達和兒子合影照(右一)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3">人生轉折</h1>
1930年底,陳伯達回到國内,這時候他26歲,年齡長了,但是名氣并沒有見長。
經過六年的打拼,1936年的春天,這時候已經32歲的陳伯達進入北方局宣傳部,擔任部長職務,才算是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名聲也很有局限性,離他“文名滿天下”的理想還很遙遠,甚至都還沒摸到邊。
1937年下旬,陳伯達從天津坐船到青島,在一路輾轉到了延安,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
陳伯達剛到延安的時候,正好遇到陝北公學創辦沒多久,正需要教員。陳伯達這一來,就好似瞌睡來了送枕頭,就被安排進去當了一名教員。
這份差事對于陳伯達來說可就是折磨了,就因為他那一口閩南方言,讓下面的學生聽起來雲裡霧裡的。無奈之下,陳伯達隻好不停的寫闆書,一堂課下來,說的還沒有寫得多,與其說是講課,倒不如說是“寫課”更貼切了。
後來沒辦法了,就專門給他配備了一名翻譯,把他口中的閩南方言翻譯成大家都能聽得懂的話,這樣的情況維持了沒多久,陳伯達就被調去了宣傳部,擔任出版科的科長。
這時候的陳伯達,仍就沒有得到重用,是以他的心境不是很美妙。
直到一次在理論座談會上,陳伯達的辯論引來了偉人的關注,這才讓陳伯達迎來了人生的重大轉折。
在座談會結束後,偉人特意把陳伯達留了下來,簡單地詢問了他一些情況,越發的有了興趣。
等到了傍晚時分,陳伯達被告知去機關合作社的食堂,偉人在等着他吃晚飯呢。這讓陳伯達十分的意外,也十分的激動,他急急忙忙地趕了過去,發現還有一個美國記者也在場。
原來偉人當時在機關食堂宴請美國記者,順道也把陳伯達也叫過來一起吃飯。
飯後,偉人留下了陳伯達,在得知陳以前在學校講過先秦諸子的課,這一下兩人找到了共同話題,越聊越投機。
最後,偉人提議讓陳伯達也開一個課,就專門講中國古代哲學。
晚年陳伯達
這一次會面,是陳伯達人生的轉機,“陳伯達”這個名字也印在了偉人的腦子裡。
沒過幾天,陳伯達的講座課就開啟了,偉人幾乎每一次都會去聽,一看他老人家都去了,其他人也紛紛慕名而來,這一下陳伯達的名聲逐漸傳開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0">後記</h1>
陳伯達真正做到“以文名滿天下”還是在1943年的時候,當時他寫的一篇《評〈中國之命運〉》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國内外的輿論關注,“陳伯達”這三個字才真的是聲名鵲起。
1988年9月20日,陳伯達因心肌梗塞去世。
在他的遺體告别儀式上,沒有訃告,以其原名“陳建相”舉行。
同年9月30日,媒體上釋出了他的死訊: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于去年10月刑滿釋放。”
全文加上标點符号,總計53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