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是曆史的一部分,我們在談論曆史的時候,往往無法忽略戰争。從古羅馬時代到兩次世界大戰,從春秋戰國時期的大混戰到被載入史冊的現代戰役,戰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競争、生存的手段。人們在反對戰争的時候,往往無法保持理性态度,就像阿瑟.黑利在《身居高位》中寫的那樣:戰争遲早是要發生的,因為戰争從來就是無法避免的。
人類曆史上很多重大的戰争不僅關乎着生死,也會造成人口、疆域、生活模式、社會結構、政治人文環境的變化,這些變化又決定着一個時代或者一個社會的發展變化。是以,戰争才會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轉折點。
也正是因為如此,和戰争相關的作品燦若星辰。尤其是在小說、戲劇、電影、音樂、雕塑、繪畫等藝術領域,戰争不僅是很多作家、藝術家靈感的來源,也是恒常如新的話題。
今年年初,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拉開帷幕,南韓導演奉俊昊憑借《寄生蟲》獲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以及最佳國際影片四項大獎,可以說是本次奧斯卡獎最大的赢家,也是南韓電影史上的高光時刻。
欣賞了大半獲獎名單上的電影,最喜歡的是薩姆.門德斯的《1917》。這部電影一改我對戰争電影的看法,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沉浸式觀影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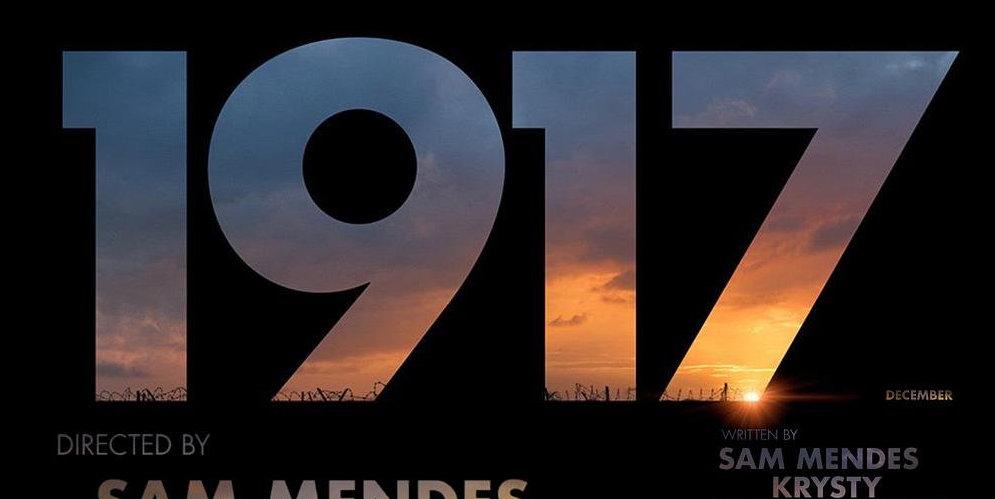
2000年薩姆.門德斯憑借《美國麗人》獲得了第7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的獎項,2009年的《革命之路》讓女主角特.溫絲萊特獲得第66屆金球獎劇情片最佳女主角。薩姆.門德斯的作品不多,但卻是好萊塢最會講故事的導演之一。
《為子搬遷》、《鍋蓋頭》、《毀滅之路》等作品都是叫好又叫座的電影。透過這些電影,我們可以窺探到導演薩姆.門德斯對電影叙事節奏的掌控以及内容的選擇。
而這部《1917》和薩姆.門德斯之前所有的電影都不同,誇張點說,這部電影和之前所有的戰争電影都不同。《1917》是一部關于一戰的電影,也是一部關于前線傳訊員的電影。薩姆.門德斯的祖父就是一戰中的傳訊員,這部電影的構想就來源于祖父在他兒時講述的那些故事。
和一些強調技術的戰争電影不同,這部電影中使用了大量的長鏡頭,觀衆透過這些長鏡頭可以很直覺地看見粗糙簡陋的戰壕、随處可見的彈坑、撕裂的鐵絲網、暗藏危機的平原高地、茂密的樹林、俯沖而下的飛機、燃燒着的建築物和被炸彈摧毀的廢墟。影片還原了傳訊員的遭遇,他的緊張、害怕、絕望、信仰以及堅持。
這種極盡“真實”的描述,強化了觀衆的感官體驗,也實作了戰争電影最核心的三個目的:呈現、重塑、記憶。
“真實”是戰争電影的生命,那麼,戰争中的“真實”是什麼樣的呢?
書評人劉憶斯寫過這樣的評述:真實的曆史不是影視劇和網絡遊戲,是從“九一八事變”至日本投降期間,中國付出了3500萬人以上的死傷;是戰時中國有上億軍民經常處于半饑餓狀态;是“淞滬會戰”時駕機撞擊日軍旗艦“出雲号”的沈崇海,這位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犧牲時年僅25歲;是抗戰期間為了不至動搖軍心,連平劇《四郎探母》都要禁演......
這就是戰争的“真實”,不是那些抽象的詞彙,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如果《1917》是這樣一部“真實”的電影,那麼,支撐起“真實”的絕不是所謂的技術手段,而是在長鏡頭中流淌的時間。
時間,讓兩個傳訊員将生死看淡結伴而行。時間,讓兩個傳訊員背負上使命和責任。時間,賦予普通士兵神聖讓死亡永垂不朽。同樣,也是時間,讓人成為人。
他們在德軍遺棄的隧道中遇見了意外,炸彈爆炸,他們死裡逃生,于是,有了這樣一段對話:
“真實”就是這樣,有怯懦、有歡喜、有緊張、有咒罵。《1917》之是以好看就在這裡,薩姆.門德斯并沒有遵照習慣,設計一個英雄人物,而是設計了一個普通的傳訊員。他并不偉大,隻是完成了任務,避免了重大傷亡。這種無數的普通人,和他們背負的責任才是戰争電影最打動人的地方。
現在讓我們從《1917》開始了解戰争電影的三個目的:呈現、重塑、記憶。
<h1 class="pgc-h-arrow-right">呈現:</h1>
戰争片有一個最基礎的叙事命題,而這個命題恰好是戰争片和其他類型片的分水嶺——塑造英雄人物、贊揚英雄行為、思想以及精神。從娛樂的角度來看,“英雄”的确有足夠的噱頭讓觀衆走進電影院。但電影發展到今天,它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也是傳遞價值觀、公德心的媒介。
盡管英雄主義主題始終是戰争電影的叙事核心之一,但“英雄”呈現出來的内涵和目的卻随着時代的不同而不斷嬗變。電影《1917》講述的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故事,戰争從1914年開始,持續了四年,1918年結束。該戰争是歐洲曆史上最慘烈的戰争之一,約有6500萬人參戰,超過3000萬人在這次戰争中喪生。
在傳統的戰争片中,“英雄”往往是一種單純的設定,他們具有非凡的勇氣,近乎神。一方面是因為電影在拍攝時需要考慮到當時社會的意識形态,也要遵守一種約定成俗的叙事規則。而《1917》并沒有遵守這個規則,薩姆.門德斯隻是呈現。
1917年,一戰正酣,兩名十六歲的英國士兵接到指令,需要立刻趕往前線,向守衛在那裡的将軍傳達“停止進攻”的訊息。時間隻有八小時,彈藥也有限。于是兩名士兵變成了傳訊員,希望穿越靜寂的死亡之地,執行任務。
<h1 class="pgc-h-arrow-right">重塑:</h1>
談論戰争的時候,人們常說,經曆過戰争的人才有資格談論戰争。大概是因為,戰争自身有着多元的屬性和意義。我們今日的文明和過往一次又一次的戰争有着密切的聯系,換言之,戰争塑造了我們今日的文明。
然而,當戰争成為電影素材,并一次又一次給我們帶來視覺奇觀時,不管對戰争有多麼深刻或者獨到的見解,每一部戰争電影或多或少會重塑我們的認知。
談論戰争,我們首先想起的就是死亡。而在電影《1917》中,薩姆.門德斯弱化了死亡帶來的視覺沖擊,比如,其中一位傳訊員被敵軍捅傷,薩姆.門德斯用長鏡頭記錄了他從受傷到死亡的過程,那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另一位傳訊員就這樣目睹着戰友的死亡,無能為力也無可奈何。
沒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也沒有痛徹心扉的表現,生命在平緩的疼痛中慢慢消失,就像沙漏逐漸漏完最後一滴。“無論是下到地界還是登上王位,獨自旅行的人走得最快。”
大多數戰争電影都可以被稱為奇觀電影,我們可以看見紛飛的戰火、奮勇殺敵的戰士、聰敏智慧的将領。這些奪人眼球的内容給觀衆帶來了巨大的震撼,在展現奇觀的同時,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塑人們的認知和對曆史的了解。
<h1 class="pgc-h-arrow-right">記憶:</h1>
關于戰争的描述,我最喜歡的是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戰争論》中寫的一段話:戰争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戰争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政治是不流血的戰争,戰争是流血的政治。戰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戰争是手段。
我承認,戰争電影曾讓我熱血沸騰,但《戰争論》讓我厭惡每一場戰争。因為戰争意味着權力的交接,意味着新的統治的開始,意味着一段未可知的時代即将拉開序幕。在這未知中,人類命運,世界文明都處于一個懸而未決的位置上,随時都有可能崩塌。
是以,戰争電影就是為了讓我們記住那些提心吊膽的日子是怎麼過來的。
《1917》中,傳訊員到達前線之後,他需要找到指揮官,并傳達指令。他穿過沒有任何遮擋的原野,炮火聲在耳邊轟轟想起,他的戰友一個借着一個倒在他身後。所有的害怕、緊張、迷茫在此時都變成了“信仰”。
整部電影直到結束時,才真正展現出了傳訊員身上的英雄主義色彩,在此之前,他隻是一個士兵,害怕戰争,害怕死亡,否則怎會拼盡全力在廢墟中和德國士兵搏鬥,然後又拼盡全力奔跑。
是以,戰争電影就是為了讓我們記住,所謂的英雄,不過是熬了過來的普通戰士。所謂信仰,不過是履行職責。
《1917》的偉大之處正是在于導演薩姆.門德斯并沒有塑造一個完美的英雄,而是真實的展現出了一個士兵執行任務的過程。接到任務指令、按照時間出發、目睹戰友死亡、單槍匹馬和敵人搏鬥、穿越沒有遮擋的戰場、完成任務時的筋疲力竭。
沒有誇張過分的情感,沒有任何多餘的煽情成分,鬼斧神工的長鏡頭将戰場的殘酷和戰士的憂愁渲染的恰到好處,精心設計的色彩、溝通、場景以及細節讓整部電影幹淨純粹。原野上的花香遮掩了死亡的惡臭,但無法消弭戰火的氣息。鐵絲紮進手心,卻無法割裂責任和使命。
完成任務之後,傳訊員倚靠着大樹翻看家人的照片,似乎看見照片就看見了回家的希望。而他又讨厭回家,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回到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