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10月27日,曆史上1491年10月27日,明武宗朱厚照出生。說到朱厚照,曆史上的評價真是一塌糊塗。先看看明史上的評價
明自正統(土木堡)以來,國勢衰弱。毅皇(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于危亡。假使承孝宗之遺澤,制節謹度,有中主之操,則國泰而名完,豈至重後人之訾議哉。
這個評價簡直是就差指着鼻子罵了。今天寫這篇文章也不是為了給照哥兒洗地,就是想大緻探讨下明武宗親手殺一人的應州大捷。
關于應州大捷,有人說是文人黑他,有人說這是史官亂寫,就拿我比較喜歡的一個up主小約翰可汗的觀點,說是來搶劫的人沒那麼多,然後又被太監兄弟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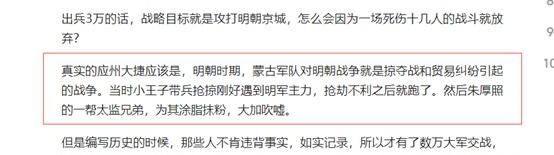
這可能是很多明史研究者的通病,即過分信任正史。但是我卻不這麼認為,為什麼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一、明武宗的對手——“小王子”達延汗
這位仁兄是個很牛X的人,七歲繼位,統一了蒙古,與右翼封建主之間進行了長達20餘年的戰争,最終統一蒙古。
在《蒙古黃金史》這本書上,記載其與明朝的交手隻有一次,當然是被明軍攻打,然後跑路的情形。
有人說這是與朱厚照的交手,我感覺不太像,我不太清楚蒙古黃金是這本書每個可汗的叙述的順序,如果按照時間順序,這段實在是太靠前了,更像是即位之初遇到的。更像是成化年間即1480年( 成化十六年) 達延汗繼位之初的 汪直、王越讨伐蒙古。
簡單介紹下:成化十五年,滿都魯汗(滿都固理可汗)去世。成化十六年,達延汗繼位,蒙古社會人心不穩。二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禦史的王越與太監汪直率兵21000 人,晝伏夜行,奔襲駐牧大同邊外威甯海子周圍的蒙古營地,擒斬600餘人。當時,在威甯海子駐營的蒙古部衆“自以不為寇,不虞官軍之至”,結果被打得措手不及。
達延汗繼位之初,内憂外擾。在解決了牽制自己的亦思馬因太師(亦思蠻太師)後,就開始對明朝大同等地展開報複性的入侵。成化十九年五月,大同上報 “北虜”小王子欲糾率部落大舉複仇”。七月十一日,(小王子)“率三萬餘騎寇邊,東西連營五十餘裡”,十三日,進入明邊。與明軍“連戰二日一夜”,明 軍 真 亡 586 人,傷 1101人;達延汗方面被明軍生擒 1 人,斬首 17 人。明朝上下造成巨大震動,“成化十九年,小王子複仇,大同官軍大遭摧衄。”
當然,這個斬首和陣亡是兩個概念,明朝以首級論軍功,文末有詳細介紹。打成這個樣子,肯定是沒辦法下去割首級的。不過自此之後,雙方交戰不斷,文獻記載蒙古成規模地入犯明邊明顯增多,明邊将也多有乘虛出邊“燒荒”、“趕馬”、“搗巢”行動。
孝宗繼位後,達延汗在弘治元年五月寫信要求上貢(其實是貿易),明朝準了之後,開始朝貢,直到弘治五年( 1492) 以後,小王子開始處理蒙古内部沖突,在此期間,既未朝貢,也很少擾邊,宣大一線邊關相對平靜。
1498 年( 弘治十一年),小王子嫌棄明朝給的少,開始轉換态度,騷擾明朝,其實這個很扯淡,憑什麼給你那麼多?你臉大?主要是内部沖突解決後開始轉向向外入侵,曆代遊牧民族都是這個德行。
弘治十三年四月,“入寇大同,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人心訩戄。” 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大同左衛 “大肆殺掠”五月中旬,“西自威遠、平虜、井坪等衛所,東自陽和、天城、順聖川,南至應、朔、山陰、馬邑、渾源、蔚州、廣昌等州縣中間環屯列寨,綿亘千裡,煙火聚落百萬餘家,旬日之間生産蕩然,人畜殆盡。”
弘治十四年八月,“虜酋小王子等七八萬騎從甯夏花馬池深入固原迄南,分路搶掠,火光營盤數十餘裡。又且埋伏阻路,勢甚猖獗。”
弘治十八年五月,“虜大舉入寇宣府,營于牛心山、黑柳林等處,長闊二十餘裡”後,蒙古與明軍“相距于虞台嶺……諸軍被圍困六七日,人馬饑乏……是役也,官軍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傷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馬六千五百餘匹,掠去男婦、畜産、器械不 可勝計。”
正德四年冬十一月,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戰死。
正德六年三月,達延汗率部入河套,進犯沿邊諸城堡,延綏縱兵侯勳、副總兵王勳等擊卻之,斬首六十四級。
正德九年秋七月,寇順聖川,遊擊将軍張勳、守備田琦、廉彪戰死。同年八月,有擁衆入甯武關,殺守備指揮陳經。九月,再犯宣府,都禦史叢蘭、總兵官白玉以計擊卻之。
正德八年 (1513 年) 三月十七日,“虜大舉入寇”,“五月四日,複以五千騎從八股泉入,三千騎從靖虜墩入,六千騎從鎮虜墩入,五百騎從沙河堡入,三萬騎從碌碡河墩入,又三千騎從滅胡墩入,一萬騎從沙溝墩入,二千騎從懷遠墩入,複以百騎從接火窯山墩入,來往石佛寺堡、滑石嶺、安邊堡至東山村諸處,四散大掠”,“蓋殺虜居民三千餘人,所掠孳畜以數萬計”。“大同三路地方,達賊蹂踐連洽旬日,數百裡煙 火蕩然,蓋數十年來未有受禍于此之慘者。”
正德十年八月,小王子犯固原。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犯薊州白羊口等處,同年冬十月,虜二萬騎分路掠偏頭關等處,我軍追襲敗之于苛岚州,斬首八十餘。
正德十二年二月,“虜七萬騎分道入寇……虜于是自青邊口出,凡攻破城寨二十處,殺虜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頭畜二萬三千五百有奇,陣亡及被傷官軍三百八十一人,所獲虜首僅九級。”
從曆次資料來看,敵人很強大,但是仍然不排除有虛報敵情的嫌疑,畢竟死了這麼多人,但是也是從死亡人數來看,敵人人數不少,且小王子軍事才能不低。另外可以看出,小約翰可汗對此時人數的評價有所低估。且其在文中說的“從土木堡之變(1449年)後,明軍戰鬥力已經明顯下降,與遊牧民族較量總是處于守勢,這是曆史事實”有兩點不對,(1)戰鬥力下降的是京兵而非邊軍,(2)成化年間無論是趁火打劫還是犁庭遼東都不能算是守勢,但是明朝窮(我之前文章提到過),以守為主。并且可以看到在應州之役前,明朝所受來自蒙古的軍事壓力是相當大的。
二、應州之戰
厚照老兄的确有點東西,當正德十二年宣大邊外再有虜情時,這位老兄便随即開始了巡邊之旅。從某些地方講,其巡邊與豹房中以江彬、許泰為代表的邊将勢力的慫恿也有一定聯系。之前說過,京營已經衰弱,是以明朝需要調邊軍鎮壓農民軍,由于邊軍在鎮壓中原流民起義中起着主導作用,邊軍将領跟朱老兄的關系也越加密切。
正德十二年八月辛未,“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縱出者。” 正德十二年九月戌朔駐跸宣府鎮,随即營建鎮國府。壬辰,上駐跸陽和城(直到應州之戰)。
因有土木堡的前車之鑒,朱老兄出關前後對進行了軍事部署, “戊辰,調右軍都督府掌府事會昌侯孫銘中府掌印管事,提督神機營如故。出關後,又“命英國公張侖奮武營坐營管操。”
當然應州之戰不隻是朱厚照一個人的功勞,秋季是蒙古打劫的好時間,是以有秋防一說,防部署的重點。從正德十二年夏五月開始,明廷就開始了秋防部署,“辛醜,命參将蕭滓統遼東兵駐宣府近地,先是總兵官劉晖往遼東選兵團操,令滓統之,以備調用,至是宣大有警,乃以所統兵赴宣府。”又命指揮金事王玺守備大同之天城城。六月, “命安遠侯柳文防守古北口,署都指揮趙承序防守白羊口,華勳防守黃花鎮,以虜在宣府近邊住牧,沿邊諸堡兵寡故也。” “癸巳,以都察院右金都禦史張襜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七月, “及查得達賊大營七月以前俱在宣府邊外住牧,八月以後俱起往西北大同境外住牧,大同鎮巡官已曾遵守本部題準防禦事宜,分布陳钰大同左衛城,周政威遠城,朱銮平虜城,張绮井坪、朔州二城,張幌懷仁城,孫鎮山陰、馬邑二城,杭雄應州城,鄭骠、麻循、高時各整部兵馬相機應援,處置周密,極為有備。”
看看朱老兄的安排,“先是有旨會計宣大二鎮糧草,務足主客兵馬四五年支用之數,戶部乃會府部大臣議處條上,一山東、河南起運臨清、德州二倉為米十三萬石,請益以太倉存留米二萬石,每石收銀八錢,以十萬石補宣府,五萬石補大同;一山西專委布政司官一員督理宣大歲征糧草,額數完足,方許回任;一兩鎮屯田歲入亦多宜令撫臣嚴督,屯田金事、管屯都指揮清查勸課,依期辦納,勿仍前玩惕;一河東解鹽課銀歲解宣府八萬兩,大同五萬兩,今增五萬于宣府;一山西軍職問發立功并文職人等所犯罪,因其輕重定為則例,俾各納銀給邊;一發太倉銀十萬兩及遣科道官再查附餘十萬分送二鎮,召商上納糧;,一收買糧草須及秋冬收成之時,可省官銀之半。得旨,河東鹽但遇鹽花生發,不拘額數,盡力撈辦分給二鎮,太倉附餘銀準動支,不必差科道官,餘如議。” ,即準備好充足的糧草。
應州之戰前又 “有旨,發戶部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準備好賞賜), “看得遼東右參将署都指揮金事蕭滓呈稱原選調宣府征進官軍來時各穿夏衣,即今八月,天氣漸寒,缺錢置買綿花,乞要給衣禦寒……今遼東官軍自遼東遠來,……何責其劾力殺賊,若遼東官軍既準給與,其延綏官軍連年調出在外,比之遼東官軍,勞苦尤甚,若不一例準給,……庶使調出在外軍人不受寒凍,緩急可用,正徳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具題,奉聖旨,……俱準照數與胖襖袴鞋,不為例,欽此” (準備好抗寒衣物,體恤士兵)
武宗北遊圖
應州之戰時,朱老兄發現之前朝廷部署的雖分布周密,但沒有重點,兵力分散,難以抵擋大規模蒙古騎兵的沖擊,是以進行了調整,“先是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将入寇,上在陽和聞之,命諸将分布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勳、副總兵官張幌、……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大概意思是①大同鎮由大同總兵官王勳、副總兵官張稅、遊擊孫鎮駐守。
②聚落堡由遼東參将蕭滓把守。
③天成衛由宣府遊擊時春駐守。
④陽和衛由副總兵陶傑、參将楊玉等駐守。
⑤平虜衛由副總兵朱銮駐守。
⑥威遠衛由遊擊周政駐守。
蒙古方面:
從“聖駕巡邊至今已經三十餘日,昨日始傳聞駕在陽和城,邊外達賊擁衆數萬,離陽和三四十裡下營,又縱賊數千,四出哨掠。”大緻能從此看出蒙古軍隊數量。
蒙古軍隊到達大同後,發現大同、陽和防守缜密,便繞過了大同、陽和,分道從大同西北入侵(“達賊約有一萬餘從彌陀山迤東往西行走。”)
戰役始末:
蒙古軍隊從大同鎮西側進攻,在孫天堡紮營,駐守在大同鎮城的王勳等人随即率兵出戰,在得知王勳部已經與蒙古軍隊交戰之後,朱厚照馬上派蕭滓、時春等支援,周政、朱鸾尾随蒙軍,伺機出戰。又召集宣府總兵朱振等與在陽和的自己彙合,準備支援。
十月十八,王勳等部與蒙古軍隊遭遇,戰于繡女村,王勳督軍力戰,蒙古軍隊朝應州方向撤退(這個是有問題的,從方向上看,應州更靠南邊,據我猜測是王勳沒打過,退回去了,蒙古軍繼續入侵)
十月十九,王勳等在五裡寨與蒙軍交戰,蒙軍分兵圍王勳(應該是騎兵沖亂了陣型)。
十月二十日,早上起霧,王勳率軍突圍,進入應州。朱鸾等趕到,合兵一處。
十月二十一日,王勳等部合軍出城尋戰,與蒙古兵在應州附近的澗子村遭遇,開打。蕭滓、時春、麻循等部來援,,被蒙軍分兵阻擋。形式危機,正巧朱厚照趕來,明軍士氣大振,蒙古稍微後撤,天色已晚,安營紮寨。(這個可能說不清,可能是真的,畢竟來援軍了)
十月二十二日,蒙古軍隊主動發起攻擊,厚照兄親自指揮,從辰時到酉時,大戰百餘回合,蒙古軍見讨不到便宜,便開始撤退。
十月二十二日,厚照兄引兵追擊,追到朔州、平虜,因為天氣、将士疲憊是以退兵。
結果:先是聖駕還自塞外,乃于奉天門下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賊器械諸物,令文武群臣縱觀,又于文華殿前頒賜賞功銀牌、彩段有差。
評價:時主兵部的王瓊評價“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甯海子,本部預奏裝置,視正德十一年尤為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适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意思是,布置很嚴密,但是沒有收獲大捷。
小結:其實吧,我覺得有這種可能,的确是打了好幾天,而且戰況很激烈,蒙古軍隊死傷不少,但是因為有第二條晉升管道(作戰勇猛)在,是以大家沒有去割首級,是以看起來斬獲并不是很大。至于有沒有抹黑,我覺得可能沒有抹黑,隻不過首級沒那麼多而已,其他地方春秋筆法一下,讓人覺得很荒唐。
想法:小王子回去基本上就死了,由于沒有史料,并不能證明此戰是否有小王子參與,因為小王子死蒙古才分裂,如果小王子真的參與了這場戰争,真的能給朱厚照填一筆功績,但是很可惜,沒有任何史料能說清楚,但是大戰是真的存在,也真的赢了。
補充:
1.明朝戰功:劉展主編的《中國古代軍制史》一書中認為:明朝基本沿用着兩種不同的标準,來制訂将士賞功的細則。第一,從決定戰局勝敗的整體出發,考察軍士的實際作用及勇敢精神。第二,則是以斬獲敵人首級的多少,來評定賞格等次。《春明夢餘錄》中也說:明朝“以首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古今治平略》記載:“凡首功四等,曰北虜,曰遼東女直,曰西番苗蠻,曰内地反賊。凡戰功二等,曰奇功,曰頭功。
2.明朝軍隊:明初,設立京營隸大元帥府後改設五軍都督府,用以訓練京軍。靖難之役後,遷都北京,北京成為中心。為訓練軍隊,明成祖定三大營之制,分為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除在京衛所外,每年調遣山東、河南等處衛所兵,到京師操練,被稱為班軍。京軍在這一時期是明朝的主力部隊。正統十四年英宗親征,明軍在土木堡遭受慘敗,五十萬大軍覆沒,京軍遭到很大損失。代宗即位後,采用兵部尚書于謙以及石亨等人的建議,精選京營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團操,号稱“團營”。原先的京軍(三大營)被稱為“老營”。英宗複辟初期廢除團營制度,于天順八年再次建立團營。明憲宗成化年間再廢團營制度,但于成化三年,采納兵部尚書馬昂等人的意見,再次實施團營制度,增為十二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團營之兵名為“頭撥”,選得一等軍士十四萬,稱為“選鋒”。到武宗時期,十二團營人數僅有六萬多,京軍人數至多十四萬。京軍本是明政府平定内部叛亂、農民起義和抵抗蒙古入侵的主要軍事力量。但是,在土木堡一戰中,京軍遭受巨大損失,而且,大量士兵又被權貴隐占,從事各種工程建設,訓練不勤,武備不修,戰鬥力已經十分衰弱。
3.曆代九邊明軍數量(引用自論文“明代九邊軍鎮體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