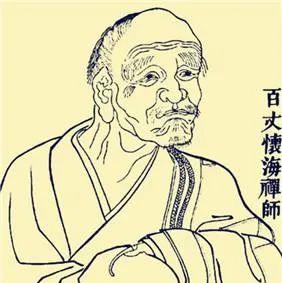
文:李滿
百丈懷海(720年—814年)是中國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俗姓王,名木尊,福建長樂人。懷海早年在廣東潮安依慧照和尚出家,後至南嶽衡山依法朝律師受具足戒,再後來至安徽廬江浮槎寺研讀經藏十餘載;終于“三學該練”,積累了深厚的經、律、論佛學知識。
唐代宗大曆初年(766年),懷海聞馬祖道一在南康(今江西贛縣)龔公山開壇講法,便前去歸依,成為馬祖的侍者,後一直追随馬祖,終得祖師真傳。懷海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三人深得馬祖道一器重,世稱馬祖門下三大士。
唐代宗大曆年間(766年—779年),鄉紳甘貞在洪州新吳(今江西奉新)大雄山(又名百丈山)建庵,聞聽小雄山普化院的懷海學養深厚,禅法精湛,于是将懷海迎入所建庵中,并将庵改名為百丈寺。自此,懷海便在此自立禅院,率衆修持,影響漸長,終成氣候,并終老于此,世稱百丈懷海禅師。
懷海于唐憲宗元和九年(814年)離世。唐穆宗敕谥其“大智禅師”,北宋徽宗追谥其“覺照禅師”,元順宗加谥其“弘宗妙行禅師”。
懷海門下最著名的兩位弟子是沩山靈祐和黃檗希運。沩山靈祐與其弟子仰山慧寂開創了禅宗五宗之一的沩仰宗,黃檗希運的入門弟子臨濟義玄開創了禅宗五宗之一的臨濟宗,臨濟宗後來又衍生出黃龍派和楊岐派兩個支系。正是由于懷海大師的傳播,洪州禅系才枝繁葉茂,信徒廣布天下,影響遍及古今,成為禅宗第一大宗派的。
史稱“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在馬祖道一之前,禅宗沒有自己獨立的修持場所,禅僧常常是四海雲遊或寄住于律宗寺院。馬祖道一首創專供禅僧集中修行的禅院(也稱叢林),使禅宗作為一個宗派有了自己獨立的據點。懷海承繼馬祖的衣缽,亦自建禅院廣聚僧衆,并首創禅林清規,使禅宗作為一個宗派有了自己獨立的修行規範和行為準則。他們師徒二人為禅宗最終成為獨立的佛教宗派居功至偉。
《百丈清規》中,普請制是其重要内容。所謂普請制,即住寺僧衆全體參加勞作的制度。禅宗不同于中國佛教其他宗派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就是自耕自種,自給自足。這對于禅宗的生存與發展都至關重要。
其他佛教宗派大多依靠信衆出資供養。而禅僧原屬遊僧,遊方時憑借化緣乞食維生。這種生存方式有極大的依賴性,給僧人的人格獨立和精神自主蒙上了深重的陰影。
禅僧集中在禅院修行之後,生存成了極大的問題。自耕自種,自給自足是以成為不二之選。然而,這種選擇也隐含着巨大的沖突沖突。農事耕種必然占用許多讀經參禅修行的時間,甚至有可能使禅僧淪為普通的農民,進而喪失純正的信仰和信念。而放棄農事耕種,生存又難以為繼。智慧的百丈懷海大師于是創造了農禅一體的修行方式,真正達到了農事參禅兩不誤的境界。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懷海大師流傳于世的名言。它既是懷海率先垂範,嚴于律己的品格展現,其中也蘊含深刻的禅學真理。與一般佛教宗派遠離人間煙火而脫離生活實際不同,禅學主張:禅理不離人間生活,生活蘊含禅學真理;遂使禅宗哲學終于發展成為獨樹一幟的生活禅學。
“參禅不異于農事,農事不異于參禅”是農禅思想的核心理論。這種理論是有深厚禅學根據的。禅學認為,佛性遍在于大千世界自然萬物,世界萬象人間萬事都是佛性的顯現。是以,真正有禅宗法眼的人,“觸目是道,立處皆真”,無論在何處,無論做什麼,他都可以從中發現禅機,領悟禅意。正所謂“擔水打柴,無非妙道”“行亦禅,坐亦禅,語默動靜體安然”。是以,耕田種地也罷,割稻采茶也罷,都是發現禅機的事宜,都是悟得禅道的契機。
這種農禅一體的修行方式不僅解決了生存需要,而且完全擺脫了乞食維生的依賴性;既為禅僧的人格獨立和精神自主确立了現實基礎,又為禅宗深入人間生活而最終成為“詩意的栖居”之生活禅注入了決定性的因素。
禅僧的勞作本質上不同于俗人的勞作,俗人的勞作隻是謀生的手段,收獲果實是其唯一的目的;是以勞作過程本身便淪為苦役,俗人避之而唯恐不及;而禅僧的勞作是物我一體而“能所俱泯”的生命活動,即對象與自我打成一片,過程與結果一體不二,手段與目的圓融統一的生命活動。是以,勞作成為妙悟道谛的形式,成為信仰修行的過程,成為提升和實作自我的過程,實質上成為了展示生命和享受生活的過程。
據《仰山慧寂禅師語錄》載,沩山靈祐問仰山慧寂道:“馬祖門下出八十四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山答曰:“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 沩山雲:“如是,如是!”
沩山靈祐是懷海門下高足,是馬祖道一的再傳弟子,自然深知馬祖道一禅法。馬祖道一獨創的禅法被譽為“大機大用”。這裡所謂“機”,指機遇。這裡所謂“用”,指應用。所謂“機用”,用俗話說就是相機行事,随機應變,應機而動,達成目标的意思。馬祖道一獨創的禅悟教學法就有這樣的特征。
上述靈祐和慧寂的對話淵源于馬祖道一與百丈懷海的之間的禅法的傳授活動。據《五燈會元》記載: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床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将何為人師?”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于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百丈侍立于馬祖身邊參學時,馬祖恰好看着禅床角上挂着的拂塵。懷海便道:“即此而用,離此而用。”意思是:禅既展現在用此拂塵的行為上,又不局限在用此拂塵的行為上。照理,這樣的回答是合乎佛學禅理的。禅學認為佛性“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無所不在”指一切事物都是佛之化身,都是佛性所現之相;當然,佛性也展現在此拂塵的作用上;是以,通過拂塵的作用,是可以讓學僧感悟佛性,領悟禅理的。“所在皆無”指佛性是絕對實體,而非相對有限的現實存在物,是以,掃除将佛性等同于實事實物的觀念,超越執著于現實利害的俗人作為,才能感悟佛性,領悟禅理。馬祖接着問:“你将來何以教導學僧?”懷海應之以豎起拂塵的動作,意思是我就這樣子啟悟學僧。馬道回應道:“即此而用,離此而用。”懷海以為馬祖認可了自己的見解,便将佛塵挂回原處,卻猝不及防遭到馬祖疾聲怒喝,其聲音之大、來勢之猛,導緻懷海耳聾三日。
馬祖因何怒喝,懷海有何過錯?懷海錯就錯在執著于他人固定的教學模式(别人豎拂塵,他也豎拂塵),且沉溺于禅法的邏輯程式(不即又不離),而自心并無切實的禅悟體驗。真參實修到家的禅者,忘情忘我又唯我獨尊,縱橫無羁而左右逢源,既不拘泥于禅法學理,也不固執于邏輯程式。得道禅僧,“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縱橫捭阖,無不自由,随緣自在,到處理成。馬祖震威怒喝,其實是以直截峻烈的方式,截斷懷海固定的邏輯思路,掃除其内心對既成道理的癡迷執著,打破其鹦鹉學舌式的說法程式,使其迷途知返,返璞歸真,返空歸無,真正複歸于涅槃妙心而達到“我心即佛,佛即我心”的境界。
馬祖傳道的整個過程可以說是随緣說法,應機自動,了無刻意造作,臻于禅學化境。懷海遭此一喝,終于大徹大悟。懷海所謂“耳聾三日”其實是自己由此而徹悟禅道的意思表示。自此,懷海傳承了馬祖道一随緣說法,應機啟悟,當頭棒喝的禅法。
懷海啟悟學僧的方式方法在禅宗典籍中多有記載:
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師便打。學僧自以為懂了懷海話中道理,懷海劈頭便打。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個。”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麼?”曰:“見。”師揚拂子便打。學僧對答如流,似乎頭頭是道,懷海又是劈頭便打。
這兩次手法皆與馬祖道一如出一轍:當頭棒喝,截斷其習慣性邏輯思路,掃除其對固定套路程式的癡迷執著,使其迷途知返,返璞歸真,返空歸無。
《五燈會元》還記載:“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适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适來肚饑,聞鼓聲,歸吃飯。’師大笑。”衆僧正鋤地時,寺中鼓聲傳來,一僧大笑而歸。衆僧納悶不解,懷海卻當下認可,認為此僧是入了觀音悟道的法門。禅僧有見色而悟道者,所謂目擊道存;亦有聞聲而悟道者,所謂觀音入理。懷海借此随緣說法,應機傳道,亦與馬祖道一的禅法一脈相承。是以說,懷海禅法是真正得了馬祖道一的真傳,恰如靈祐慧寂師徒所言,他得了大機大用。
《五燈會元》
大機大用之“大”,意為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能。所謂“大機”,意為佛性遍在,無處不現禅機。得大機者,觸目是道,處處皆識禅機。所謂“大用”,意為應用萬方,妙用無窮。得大用者,左右逢源,縱橫捭阖,無所不能,妙用無窮。百丈懷海正是這種得了大機大用的偉大禅師。
随緣說法加當頭棒喝的禅法是懷海從馬祖那裡繼承的家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禅思想和修行實踐則是懷海的首創。後者影響尤其深遠,最終成為洪州禅延續千年傳承不絕的家風。如今江西雲山真如禅寺、江西靖安寶峰禅寺的僧衆仍在奉行農禅實踐。
(作者系南昌師範學院教授、江西美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