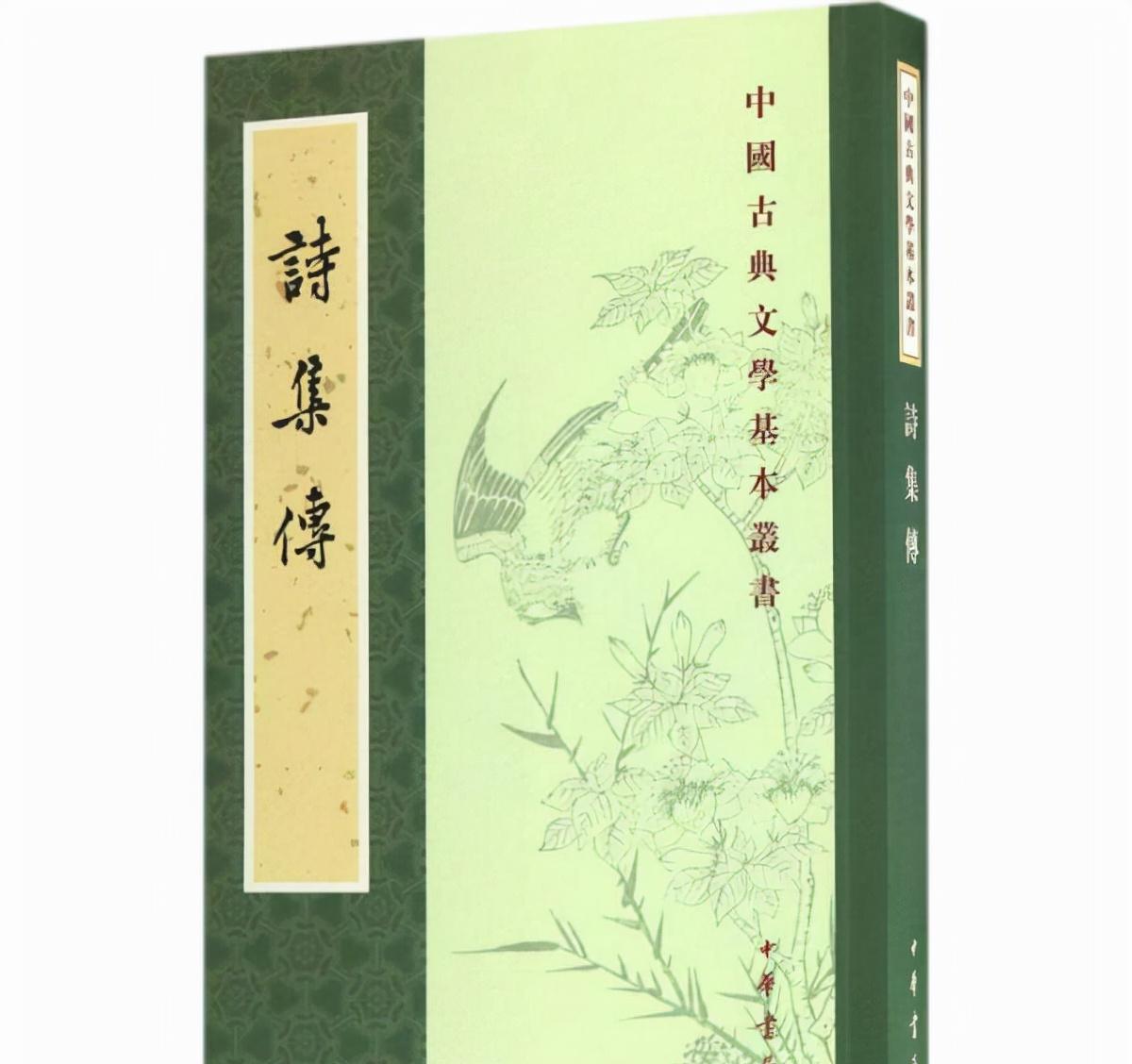
個人閱讀朱熹《詩集傳》版本
朱熹《詩集傳》由《詩集傳序》、《詩傳綱領》、《詩序辨說》、《詩卷》和《附錄》五部分組成。《詩集傳序》為朱熹自撰之序言,以設問的形式成篇,回答了《詩》産生的原因、《詩》的作用、風雅頌詩體不同的原因、如何學《詩》四個問題;《詩傳綱領》是朱熹對前人解詩内容的抄錄和釋讀,以為綱領,包括《詩大序》、《書·舜典》、《周禮·大師》、《禮記·王制》、《論語》、《孟子·萬章》等著作,此外還包括二程、張載、謝良佐幾人的一些觀點;《詩序辨說》為朱熹對《詩序》内容的批駁,先列原文,随後加以辨說,多反駁之語;《詩卷》為《詩集傳》之正文,《詩經》原文與朱子注解為一體;《附錄》為編者收集的曆代學者、藏書家關于《詩集傳》的一些著錄、序跋文字。
另,前三篇著作,宋本《詩集傳》中未收錄,本書編者為友善讀者,以原本為底本并校以他本加以收錄。
朱熹在《詩集辨說》開篇對《詩序》發展以及寫作緣由作了簡要概述。關于《詩序》的作者,他以為“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衛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關于寫作緣由,他說:“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雲雲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别附經後。”他否定了前人臆測解詩,主張從文本出發去了解詩歌,是他對《詩序》反駁的立腳點,然而對于《詩序》他并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繼承。他說:“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複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雲。”
《詩序辨說》正文先列《詩序》原文,然後附以朱子之辨說,其中有從詩意和史實出發對《詩序》判說持反對意見予以辯駁的,也有部分同意《詩序》觀點的;亦有對《詩序》看法的認同。
以《王風》為例,《黍離》、《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蓷》四篇中《詩序》評價朱子表示認同,《兔爰》一篇,《詩序》評曰:“闵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表示了部分同意,并進行了辨說,他說:“‘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關于《君子于役》、《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五篇,朱子以為《詩序》為誤。如《君子于役》,《詩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朱子反駁:“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又如《采葛》,《詩序》曰;“懼讒也。”朱子反駁:“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傳”是傳述之意,指注疏家們闡釋經義的文字,所謂“集傳”即“集注”的意思,彙集各家傳注,加以鑒别,擇善而從,并間下己意。朱熹雜取毛、鄭,也兼采齊、魯、韓三家,還吸取了不少當代學者的解說。對于沒有把握的問題,以“未詳”标之,而不強解,展現了朱子踏實嚴謹的學術态度。
《詩集傳》共二十卷,正文包括國名介紹(國家地理、曆史狀況)、《詩經》原文、注音、賦比興手法标注、字的解釋、句的釋讀、篇章解讀、一國之風總評等,在字句篇的解讀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學者的觀點,如呂祖謙、蘇轍、張載等。它基本廢除了《毛詩序》的題解,隻從《詩經》文本入手,探求詩篇本意。
朱熹否定了長久以來的“美刺”傳統,提出《詩》涵詠道德,修身齊家的理學思想。正如他在《詩集傳序》中關于學《詩》門徑的論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诂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朱熹繼承了前人“風雅正變”之說,以《二南》為“正風”,其餘十三《國風》為“變風”,将《二南》看作文王之化,大力稱頌文王德化之勝。他在《詩集傳序》中說到:“吾聞之,凡《詩》所謂《風》者,多出于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在正文中更是把這種觀點貫徹到了篇章解讀之中,如《桃夭》首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朱子解釋為“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漢廣》首句“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解讀“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複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複詠歎之也。”在《周南》之總評中更是說到:“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後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于後妃,然其實則皆是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緻而自緻者,故複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是以至此,後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後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誤矣。”将《詩序》中所稱頌的後妃之德歸結為文王之化的成果,在《召南》總評中,更是将文王之化擴充到更多的人、更廣的地方:“《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業。《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朱熹對《詩經》篇目主題的解讀與《詩序》多有不同,即使是本人在《詩序辨說》中的觀點和《詩經》正文中的觀點也是存在龃龉的。如《鄭風·豐》在《詩序辨說》中說:“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而在正文解讀中又說:“婦人所期之男子以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之是以存在這樣的差異,《四庫全書總目·詩集傳》解釋說:“注《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是為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序》,蓋猶初稿……《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删改未盡者也。”清代周中孚在《鄭堂讀書記》卷八中也說:“蓋其初稿亦用《小序》,後與東萊相争,遂改從鄭樵《詩辨妄》之說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攻《小序》,而《集傳》一一追改。”
當然,與現代人對《詩經》的解讀相比,朱熹的解讀也有不少他的局限性,這主要展現在《國風》中,特别是對愛情詩的看法。他将其斥為“淫奔之詩”“淫女之詞”“刺淫亂”等等,如《邶風》中的《匏有苦葉》、《靜女》;《鄘風》中的《桑中》、《蝃蝀》;《王風》中的《采葛》、《大車》;《鄭風》中的《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萚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等,特别是《鄭風》中共二十一篇就有十二篇“淫詩”。(淫奔之詩:《靜女》、《蝃蝀》、《采葛》、《大車》、《将仲子》、《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淫女之詞:《山有扶蘇》、《萚兮》、《狡童》、《褰裳》、《風雨》;刺淫亂:《匏有苦葉》;淫而見棄:《衛風·氓》、《鄭風·遵大路》)
而類似題材出現在《陳風》中,情況就又發生了不一樣,《陳風》十篇中有五篇愛情詩,他稱之為“男女會遇之詞”“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主要展現在對《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五篇中。對于這種情況,朱子引用東萊呂氏言:“‘變風’終于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是以為正者,舉其正者是以勸之也。‘變風’之是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将男女之情至于禮義之内,進而肯定了愛情詩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對《鄭風》多有指斥,究其原因,也許還在孔子。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複邦家者。”(《論語·陽貨》)
朱熹在最後總評中更是對《鄭風》狠狠指責:“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複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故自由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在他看來,鄭衛之聲同為“淫聲”,鄭聲更淫于衛,其原因在于《鄭風》中愛情詩篇幅多于《衛風》,在内容上《鄭風》淫靡過甚,《衛風》尚有勸誡諷刺之内容。
朱熹受到吳棫葉韻說的影響,用這個方法來為《詩經》注音,把一個字臨時改變讀音,以求押韻。用今之讀音去讀,有些存在較大差異。私以為除音韻學自身發展階段原因外,還有可能是朱熹方言讀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