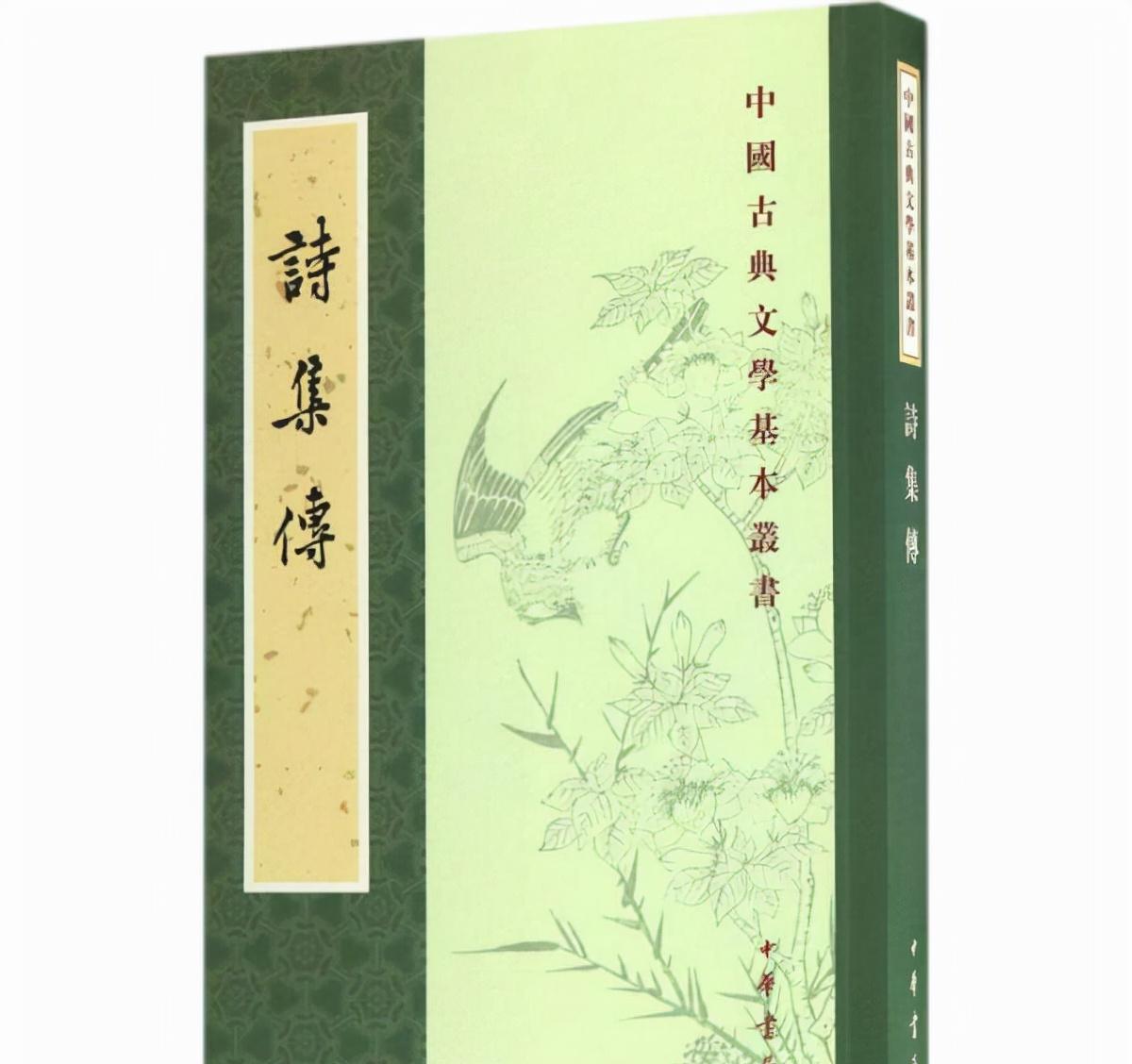
个人阅读朱熹《诗集传》版本
朱熹《诗集传》由《诗集传序》、《诗传纲领》、《诗序辨说》、《诗卷》和《附录》五部分组成。《诗集传序》为朱熹自撰之序言,以设问的形式成篇,回答了《诗》产生的原因、《诗》的作用、风雅颂诗体不同的原因、如何学《诗》四个问题;《诗传纲领》是朱熹对前人解诗内容的抄录和释读,以为纲领,包括《诗大序》、《书·舜典》、《周礼·大师》、《礼记·王制》、《论语》、《孟子·万章》等著作,此外还包括二程、张载、谢良佐几人的一些观点;《诗序辨说》为朱熹对《诗序》内容的批驳,先列原文,随后加以辨说,多反驳之语;《诗卷》为《诗集传》之正文,《诗经》原文与朱子注解为一体;《附录》为编者收集的历代学者、藏书家关于《诗集传》的一些著录、序跋文字。
另,前三篇著作,宋本《诗集传》中未收录,本书编者为方便读者,以原本为底本并校以他本加以收录。
朱熹在《诗集辨说》开篇对《诗序》发展以及写作缘由作了简要概述。关于《诗序》的作者,他以为“毛公始分以寘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卫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关于写作缘由,他说:“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他否定了前人臆测解诗,主张从文本出发去理解诗歌,是他对《诗序》反驳的立脚点,然而对于《诗序》他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他说:“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
《诗序辨说》正文先列《诗序》原文,然后附以朱子之辨说,其中有从诗意和史实出发对《诗序》判说持反对意见予以辩驳的,也有部分同意《诗序》观点的;亦有对《诗序》看法的认同。
以《王风》为例,《黍离》、《君子阳阳》、《扬之水》、《中谷有蓷》四篇中《诗序》评价朱子表示认同,《兔爰》一篇,《诗序》评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朱子表示了部分同意,并进行了辨说,他说:“‘君子不乐其生’一句得之,余皆衍说。其指桓王,盖据《春秋传》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见此诗之为是而作也。”
关于《君子于役》、《葛藟》、《采葛》、《大车》、《丘中有麻》五篇,朱子以为《诗序》为误。如《君子于役》,《诗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朱子反驳:“此国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辞。序说误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又如《采葛》,《诗序》曰;“惧谗也。”朱子反驳:“此淫奔之诗,其篇与《大车》相属,其事与采唐、采葑、采麦相似,其词与《郑·子衿》正同,《序》说误矣。”
“传”是传述之意,指注疏家们阐释经义的文字,所谓“集传”即“集注”的意思,汇集各家传注,加以鉴别,择善而从,并间下己意。朱熹杂取毛、郑,也兼采齐、鲁、韩三家,还吸取了不少当代学者的解说。对于没有把握的问题,以“未详”标之,而不强解,体现了朱子踏实严谨的学术态度。
《诗集传》共二十卷,正文包括国名介绍(国家地理、历史状况)、《诗经》原文、注音、赋比兴手法标注、字的解释、句的释读、篇章解读、一国之风总评等,在字句篇的解读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学者的观点,如吕祖谦、苏辙、张载等。它基本废除了《毛诗序》的题解,只从《诗经》文本入手,探求诗篇本意。
朱熹否定了长久以来的“美刺”传统,提出《诗》涵咏道德,修身齐家的理学思想。正如他在《诗集传序》中关于学《诗》门径的论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 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朱熹继承了前人“风雅正变”之说,以《二南》为“正风”,其余十三《国风》为“变风”,将《二南》看作文王之化,大力称颂文王德化之胜。他在《诗集传序》中说到:“吾闻之,凡《诗》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在正文中更是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了篇章解读之中,如《桃夭》首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朱子解释为“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汉广》首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解读“文王之化,自近而远,先及于江汉之间,而有以变其淫乱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见之,而知其端庄静一,非复前日之可求矣。因以乔木起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也。”在《周南》之总评中更是说到:“按此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词虽主于后妃,然其实则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齐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则家齐而国治之效。《汉广》、《汝坟》,则以南国之诗附焉,而见天下已有可平之渐矣。若《麟之趾》,则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故复以是终焉,而序者以为‘《关雎》之应’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为无所助矣。然妻道无成,则亦岂得而专之哉?今言《诗》者,或乃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将《诗序》中所称颂的后妃之德归结为文王之化的成果,在《召南》总评中,更是将文王之化扩展到更多的人、更广的地方:“《鹊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见当时国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修身以正其家业。《甘棠》以下,又见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国君能修之家以及其国也。其词虽无及于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朱熹对《诗经》篇目主题的解读与《诗序》多有不同,即使是本人在《诗序辨说》中的观点和《诗经》正文中的观点也是存在龃龉的。如《郑风·丰》在《诗序辨说》中说:“此淫奔之诗,序说误矣。”而在正文解读中又说:“妇人所期之男子以俟乎巷,而妇人以有异志不从,既则悔之,而作是诗也。”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四库全书总目·诗集传》解释说:“注《诗》亦两易稿,凡吕祖谦《读诗记》所称‘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说全宗《小序》,后乃改从郑樵之说,是为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无一语斥《序》,盖犹初稿……《周颂·丰年》篇《小序》,《辨说》极言其误,而《集传》乃仍用《小序》说,前后不符,亦旧稿之删改未尽者也。”清代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卷八中也说:“盖其初稿亦用《小序》,后与东莱相争,遂改从郑樵《诗辨妄》之说而废小序。故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一一追改。”
当然,与现代人对《诗经》的解读相比,朱熹的解读也有不少他的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国风》中,特别是对爱情诗的看法。他将其斥为“淫奔之诗”“淫女之词”“刺淫乱”等等,如《邶风》中的《匏有苦叶》、《静女》;《鄘风》中的《桑中》、《蝃蝀》;《王风》中的《采葛》、《大车》;《郑风》中的《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溱洧》等,特别是《郑风》中共二十一篇就有十二篇“淫诗”。(淫奔之诗:《静女》、《蝃蝀》、《采葛》、《大车》、《将仲子》、《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溱洧》;淫女之词:《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风雨》;刺淫乱:《匏有苦叶》;淫而见弃:《卫风·氓》、《郑风·遵大路》)
而类似题材出现在《陈风》中,情况就又发生了不一样,《陈风》十篇中有五篇爱情诗,他称之为“男女会遇之词”“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主要体现在对《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泽陂》五篇中。对于这种情况,朱子引用东莱吕氏言:“‘变风’终于陈灵。其间男女夫妇之诗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所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时之治乱,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录之烦悉,篇之重复,亦何疑哉!”
将男女之情至于礼义之内,从而肯定了爱情诗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对《郑风》多有指斥,究其原因,也许还在孔子。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论语·阳货》)
朱熹在最后总评中更是对《郑风》狠狠指责:“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故自由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在他看来,郑卫之声同为“淫声”,郑声更淫于卫,其原因在于《郑风》中爱情诗篇幅多于《卫风》,在内容上《郑风》淫靡过甚,《卫风》尚有劝诫讽刺之内容。
朱熹受到吴棫叶韵说的影响,用这个方法来为《诗经》注音,把一个字临时改变读音,以求押韵。用今之读音去读,有些存在较大差异。私以为除音韵学自身发展阶段原因外,还有可能是朱熹方言读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