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慕津鋒
2021年5月5日,是我國當代著名作家杜鵬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杜鵬程(1921年——1991年),原名杜紅喜,陝西韓城人。1939年,18歲的杜鵬程以劇本《反擊》進入文壇。在他52年的漫長創作生涯中,杜鵬程先後創作出長篇小說《保衛延安》、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裡》,短篇小說作品《年青的朋友》、《速寫集》、《杜鵬程小說選》等。杜鵬程的小說多為重大題材,他擅長從嚴峻的鬥争與考驗中,描寫人物精神面貌。其中,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第一部大規模正面描寫解放戰争的優秀作品,它的出現具有裡程碑意義,它在當代文學史上被譽為“英雄史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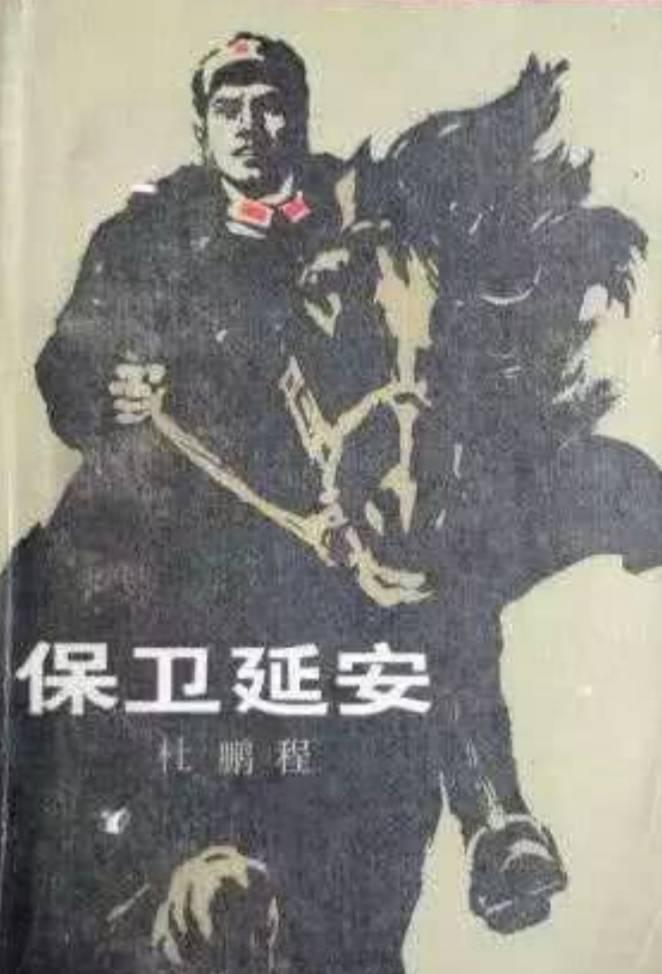
《保衛延安》是杜鵬程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該小說全面描繪了1947年3月到7月黨中央撤離延安後,西北野戰軍在西北戰場開展青化砭伏擊戰、羊馬河、蟠龍鎮攻堅戰、長城線上突圍戰、沙家店殲滅戰和九裡山阻擊戰等幾場重大戰役,小說熱情讴歌了解放軍指戰員的雄偉氣魄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生動展現了在延安保衛戰中,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為戰略反攻這一曆史發展過程的全貌,進而深刻反映了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軍事形勢。
杜鵬程
1949年底,杜鵬程開始動手創作《保衛延安》。最初,杜鵬程是想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他設想從1947年3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主動撤離延安寫起,直到1949年末一野一兵團進軍帕米爾高原為止,記述西北解放戰争的整個過程。談及創作初衷,杜鵬程在《保衛延安》手稿中曾專門寫下這樣一段“開頭的話”。
手稿
講人民解放軍艱苦奮鬥、英勇善戰這種故事的人,實在不少了。我為什麼還要講這一篇故事呢?說起來話長:
一九四七年三月,部隊從晉中出動,過黃河保衛毛主席的時候,我到二縱隊X旅X團第一連當文化教員。後來又調到營部當工作員。部隊從陝北打倒(到)西安,從西安打倒(到)甘肅、青海,過祁連山,以後萬裡進軍,通過塔裡木盆地的戈壁沙漠,一直進到帕米爾高原……)在帕米爾高原上保衛國防,在塔裡木盆地上參加生産。戰士們常常說:“把咱們打仗的事情編起來吧!這是滿有味道的。”戰士們這樣說有兩個意思:第一,我們部隊有些新同志他們聽了部隊過去艱苦奮鬥的故事,會受到一番教育。第二,老戰士希望把這個故事編起來,一方面回憶過去艱苦奮鬥的戰争,可以增加今天保衛相國和建設祖國的信心;一方面把我們部隊那些活着的和犧牲了的英雄們的名字和事透記下來。大家推我來編。
杜鵬程的創作确實是有着得天獨厚的條件。1947年3月,杜鵬程以新華社野戰分社記者身份加入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獨立第四旅第十團二營六連,西北野戰軍著名的戰鬥英雄王老虎就在六連。在部隊,杜鵬程與戰士們同吃同住,給他們講政治課、教他們識字,此外還替他們寫決心書、寫家信。漸漸地,杜鵬程與六連的幹部戰士結下了深厚友誼,并逐漸熟悉他們的身世、性格、生活習慣以及戰鬥表現。與此同時,杜鵬程還經常接觸到西北野戰軍各級指揮員。二縱司令員王震得知杜鵬程是記者,還曾特意找他談話,鼓勵他要經受住戰火的考驗,并努力寫出反映廣大指戰員英勇戰鬥的好作品來。不久,“延安保衛戰”爆發。國民黨胡宗南精銳部隊20多萬人,在數十架飛機的配合下,分别從洛川、宜川出動,聲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而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指揮下,以裝備遠遠不及對手的3萬餘人,與胡宗南在陝北周旋、拼殺,展開了一場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的殊死搏鬥。戰争進行地十分殘酷,幾個月後,杜鵬程所在的西北野戰軍二縱即減員過半,他所在的六連由原來的90多人銳減為十多人,長期與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見面就送給他一條新毛巾的營長黃培樞,都在榆林三岔彎的戰鬥中壯烈犧牲;戰士許柏齡臨上戰場前,留給杜鵬程兩封信,一封寫給黨支部、另一封寫給他孤寡母親,許柏齡最終卻沒有回來;曾經給杜鵬程很多幫助和鼓勵的團參謀長李侃,為了使山溝裡的數千名戰友脫離險境,和一些戰士英勇無畏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激勵着杜鵬程,使他忘我地戰鬥。杜鵬程抓緊一切可用時間在自己的日記中記下一個又一個難忘的戰鬥場面。有時,他将裝日記的包袱放在膝蓋上寫,有時是在宿營以後趴在老鄉的鍋台上寫,即使在硝煙彌漫、子彈橫飛的陣地上,他也照寫不誤。數年之間,杜鵬程寫下近二百萬字的日記和素材。1949年7月,杜鵬程被任命為新華社第一野戰軍分社主編。同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杜鵬程随一野一兵團司令部乘飛機由甘肅飛抵迪化。随後,杜鵬程跟随部隊參加了在新疆的多次戰鬥,他們穿沙漠、過草原、跨戈壁、越高山、趟河流,直到1949年末進軍至帕米爾高原。曆時2年多的艱苦卓絕的西北解放鬥争以及無數英雄人物所表現的自我犧牲精神,都給杜鵬程巨大的沖擊,使他萌生了要将西北戰場這一偉大的人民解放戰争訴諸筆端、昭示後人的強烈沖動。
經過充分準備,1949年底,杜鵬程正式動筆創作這部報告文學。當時他所能依靠的創作資料有:一本油印毛主席《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新華社各個時期關于戰争形勢所發表的述評及社論,自己在解放戰争中所寫的新聞、通訊、散文特寫、報告文學和劇本等,還有他在戰争中所寫的近二百萬字日記,以及部隊中油印小報、曆次戰役和戰鬥總結。一捆捆材料堆在他那狹小的寫作間地上,要想進屋裡去,杜鵬程必須跳着“翻山越嶺”。那一時期,杜鵬程白天要騎馬出去采訪、發消息、寫通訊,反映我軍打仗和生産建設情況。隻有晚上夜深人靜時,忙完一天所有工作後,他才能坐下來寫這部作品。2個月,杜鵬程“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時序交錯,……”不知熬過多少通宵達旦,杜鵬程按時間順序把他在戰争中所見、所聞、所感真實地記錄下來。
1950年2月,近二百萬字的報告文學初稿完成,全是真人真事。初稿完成後不久,杜鵬程就開始對這部報告文學進行第一次修改。1951年2月,杜鵬程在新疆喀什完成第一次修改。3月下旬,他接到家鄉寄來的母親病危電報,心急如焚的杜鵬程拿着電報趕忙去找自己的兵團司令王震。王震當即特批讓杜鵬程搭乘當時西北唯一的一架軍用飛機趕回陝西。杜鵬程在西安下了飛機,在嚴寒和風雪中步行數日,終于回到家鄉。當時,他随身隻攜帶了一大捆自己剛剛創作完成的報告文學《保衛延安》手稿和一把手槍。 當午夜趕到家中時,母親已沒有了呼吸。杜鵬程坐在自己随身攜帶的那捆稿子上,伸出雙臂,抱起了永遠不能再回答他的母親,放聲痛哭。為母親辦完喪事後,杜鵬程搬到韓城縣人民政府,他打算在這裡書稿進行第二次修改。該稿名為報告文學,實則是對杜鵬程自己“戰地日記”初步整理的資料長編,文字質樸無華,極具真實感。杜鵬程“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地工作,把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在修改時,杜鵬程的眼前常浮現母親的面容,還有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從母親身上,杜鵬程看到了中國人民悲慘的過去;從戰士們身上,杜鵬程又看到了被壓迫、欺淩了百年的中國人民奮起抗争的那種排山倒海的力量。
1951年5月,杜鵬程完成對這部報告文學的第二次修改。但修改後,對于自己眼前這部長篇報告文學,杜鵬程認為“雖說也有閃光發亮的片段,但它遠不能滿足我内心的願望。從整體來看,它又顯得冗長、雜亂而枯燥。”于是杜鵬程“苦苦思索,終于下定了決心:要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搞,一定要寫出一部對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藝術作品。”
正是這次回鄉,讓杜鵬程決定将自己最初100多萬稿子重新進行删減、修訂,體裁也由報告文學轉為長篇小說。1951年春夏之交,杜鵬程背着稿子重新回到自己在新疆的工作崗位。此後,杜鵬程在繁忙的工作之餘,開始對這部作品進行不斷修改。1951年7月、9月、11月,1952年2月,杜鵬程在迪化先後對《保衛延安》進行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修改完成于迪化。1952年5月,《保衛延安》第八次修改完成于北京。1953年春,杜鵬程借調到北京軍委總政治部。正是在這一時期,杜鵬程對手稿進行了最集中的一次修改,除此之外,他還将一部列印稿送給中國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著名文藝理論家馮雪峰審閱,請予指正。馮雪峰是杜鵬程恩師柯仲平的好友,柯在此前曾特地寫過一封推薦信給馮雪峰,請他對于杜鵬程創作的《保衛延安》多提意見。馮雪峰收到稿子後,在百忙中認真閱讀了小說,後來他又幾次約杜鵬程到家裡,當面談了他的一些具體看法和意見。根據馮雪峰的意見,杜鵬程對手稿又進行了認真修改,最後該小說順利通過終審。經過近五年的創作,杜鵬程“把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為六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又把六十多萬字變成十七萬字,又把十七萬字變成四十萬字,再把四十萬字變為三十多萬字……漫長歲月裡,九易其稿,反複增添删削何止數百次。”不久,小說《保衛延安》被解放軍總政治部列入“解放軍文藝叢書”。1954年6月,《保衛延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杜鵬程對于《保衛延安》手稿視若生命,曆經幾十載,他都将其珍藏在身邊。在他去世後,為給這些手稿找尋最好的歸處,妻子張文彬20世紀九十年代親自來到位于西三環萬壽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向當時負責人舒乙提出捐贈意向。很快,文學館便派了兩位同志前往西安杜鵬程家中取回《保衛延安》等手稿。這兩位同志不久便背回了兩大捆書稿。其中《保衛延安》手稿最多,有《保衛延安》的寫作大綱、人物表,有《保衛延安》報告文學版第一稿、第二稿。(其中,第一稿共3514頁,100多萬字。第二稿則有1451頁。)小說版書稿共四部(第三稿有270頁,第四稿306頁,第五稿有428頁,第七稿有228頁)。
在每一稿,杜鵬程都做了較大修改,密密麻麻數的修改處數不勝數。正是這些修改,讓我們看到杜鵬程為這部文學作品到底付出了多少艱辛。
今年是杜鵬程先生誕辰100周年。謹以此文,向這位創作了不朽的紅色經典小說《保衛延安》的作家緻以我們文學館人最高的敬意。
<b>【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歡迎向我們報料,一經采納有費用酬謝。報料微信關注:ihxdsb,報料QQ:33864057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