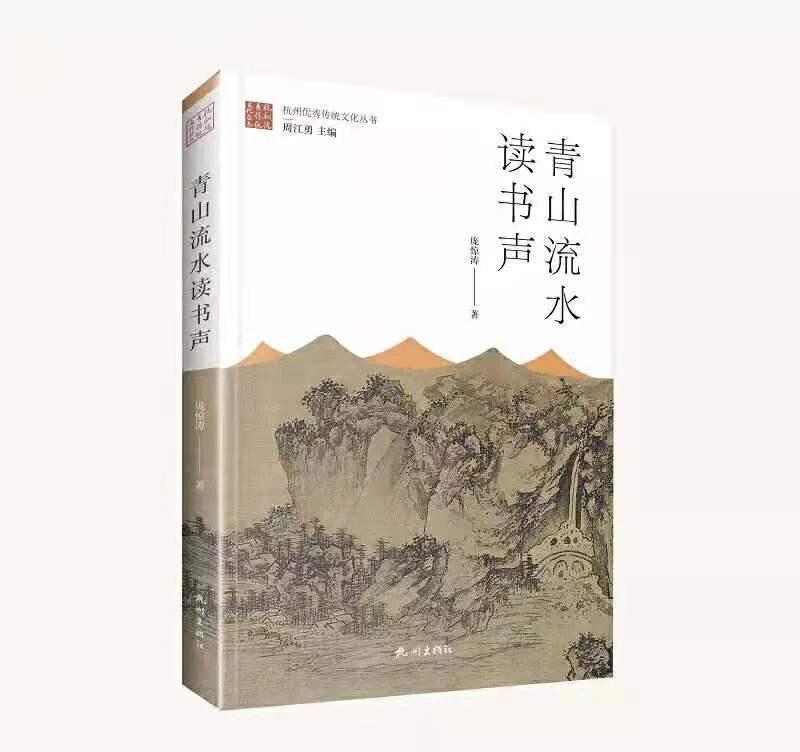
文/龐驚濤
6.留在杭州記憶裡的天真書院
門人周積萬萬沒想到,他竟能有這樣非凡的“機緣”為老師送終。
他隻道是一次平常的谒見,能得老師開示一二,即是莫大的福分。
在途細推谒見應答細節時,他已将老師此番平亂的前後事功作過細細的回放。以學問宗師而立至偉戰功,學生的景仰和歌頌怎麼都不為過。
他甚至悟出老師抗命回師正是行的“人倫之常”的無言之教。“廟堂之上”的大學士桂萼大約是不會懂得他的,是以下了進軍安南(今越南)的指令。而老師要的,隻是告病回家這個人倫之常。
周積沒想到老師的病已到膏肓,是以面對老師的離去,開始是一陣慌然失措和手忙腳亂。稍一穩定方寸,方才馳書同門,報告這一悲傷的消息。
無論如何,老師匡扶聖學的人生任務到此就算完成了,作為門人,該一起商量怎麼接過心學的大旗。王大用、劉邦采、汪鋐等,或早已有準備,或迎祭于道。靈柩過南昌、弋陽,直至二月,歸于吳越故裡。是年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一切停當,周積才和同門深談繼承老師心學大旗的事業。
黃绾說:“老師早有遺言,‘無他所念,平生學問方見得分數,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如何成?竊以為還是在開書院、講心學。”
薛侃講起往歲随老師遊曆杭州時的一段聞見,以此窺得老師之遺願:
那是正德二年(1507)年夏天的事。早在二月,生性秉直不畏權奸的守仁就因為援救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而開罪宦官劉瑾,挨了四十闆子後,貶谪貴州龍場驿。路經杭州,曾計劃攜一衆弟子作名山勝水之遊。天真山,即在學生們的計劃之列。
戴罪在身,加之劉瑾追殺甚急,守仁不得不改變行程。雖然最終得以安全脫身,但未上天真山,到底成為了一件憾事。
對天真山之奇景妙觀,守仁是有想象的。這美好的想象,源于一衆弟子的交口盛贊,他甚至在意識裡規劃過天真山聚徒講學的場景。
“如是,我們當為老師完成這一心願。”講完這段經曆,薛侃道。
山在湖海之交而多奇岩古洞,錢德洪向老師推薦這裡時,是有相當充足的籌劃的,他明白此處風月佳構,正契老師素望。為擺脫劉瑾的追殺,老師不得不臨時放棄遊覽天真山的計劃,但到了西安,老師寄來兩首詩,卻能見其肺腑,其中兩句,錢德洪念念不忘:“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文明原有象,蔔築豈無緣。”老師堅信,一定會有他年築室天真山的緣分。如今,即便老師肉體消亡,但靈魂不滅,就讓這青山綠水,成為老師不滅靈魂的歸隐地吧。
“莊子有言:真者,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老師中歲以後,頗注意對道家思想的融攝,闡釋良知學說,每有道家術語。山名天真,正是老師融鑄儒道兩家之本義,此其一;先生臨終所言‘此心光明’,要在了解何為‘光明’,竊以為,‘光明’即‘天真’之别解。此其二。有此兩端,此書院實已有老師生前賜之:天真精舍是也!”薛侃人如其言,此番侃侃而談,讓一衆同門信服不已,當即議定書院即取名天真精舍,以祭祀老師、傳承聖學為大業。
這番計議很快得到了一衆同門的認同,大家為完成老師遺願而倍感安慰的同時,也為同門之間有了長久的聚會之所而欣喜。諸同門大多本在公門,一呼百應,推進迅速;即便有少數不在當朝為官,但也是名家望族,影響地方。由此,籌措建造天真書院的經費便得到了保障。弟子們各自領責分工,很快,一個可同時招收一百多學生的天真書院就建起來了。
薛侃當仁不讓,就建造天真書院的過程及書院規制作文記之,并勒石而銘。通過這篇《勒石文》,大體可以想象天真精舍初建早期的規制:
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為載書室,右為望海亭,左為嘉會堂,左前為遊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為日新館,餘為齋舍。周以石垣,界則東止淨明、西界天龍、北暨天真、南抵龜田路。
中間的祠堂,自然是祭祀先師王守仁的地方,是整個精舍的中心所在。由此也明确了天真精舍以祭祀為主的性質。24年後,門人歐陽德選址天真精舍上院,修建“仰止祠”,專祀先師王守仁,此後,春秋兩祭,“四方同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終月。”祭祀之後,是連續一月的會講,四方同志參加祭祀和聽講,成為天真精舍數十年間弦歌不辍的盛大景象。
守仁應該是欣慰的。
而杭州城的儒生們,卻為這個生于越城而遺愛杭州的大儒充滿無盡的感激。是以,上至來浙任職的官員,下到普通的杭州儒生,對天真書院的增建和講學都非常重視。據鄒守益所記《天真書院改建仰止祠記》所載:嘉靖三十六年(1557),總制胡宗憲平海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事,命同門杭二守、唐堯臣重刻先師《文錄》、《傳習錄》于書院,以嘉惠諸生。增修祠宇,加丹垩,搜泉石之勝,辟‘凝霞’、‘玄明’二洞,梯上真,穴蟾窟,徑三峽,采十真,以臨四眺;湘煙越峤,縱足萬狀,穹島怒濤,坐收樽爼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師嘗詠之,而一旦盡發于郡公,鬼神其聽之矣。
這是杭州儒生們追思守仁的高潮。
由是,天真山上,湖海之中,每每有朗朗不絕的吟誦之聲。一派天真出自然,仰止亭下悟良知。從公元1530到1579年的數十年間,天真書院持續不斷的祭祀和講學,使杭州城成為守仁聖學當之無愧的傳播高地,而天真書院的持續數十年的儒家經典講學,也對杭州文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然而,守仁自己想到了聖學在他身後分化的必然,但或許沒有想到天真書院屢興屢廢、終至于毀棄的命運。更為關鍵的是,毀棄書院政令發起者,竟然是自己的門人之後。
說起來,張居正應是守仁的再再傳弟子。因守仁看重并喜歡聶豹,便收他為弟子。聶豹在華亭時,又收了徐階為弟子。日後徐階做了首輔,獎掖和提拔尚是翰林學士的張居正,使他逐漸掌握實權,并有了抗衡朝中權貴的實力。徐階功成身退,張居正很快接了他的班,成為萬曆初年獨秉朝政的首輔。但他當了首輔後,并沒有興私學、建書院,反是毀書院、禁講學。萬曆七年(1579年),萬曆皇帝下诏毀書院。“自應天府以下,凡六十四處,盡改為公廨”。六十四個書院,就這樣成為官府辦公的地方,天真書院作為傳播陽明心學的重要法場,也在毀壞之列。
張居正假手萬曆皇帝毀天下書院,理由是反對書院師生們的空談誤國,講學牟利,而昭昭昌明的,在于他反複強調的實幹興邦。他讨厭那些清談的讀書人,對國家大事指手畫腳,他需要經世緻用的幹才,也即他強調的循吏。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這班聚徒講學的大儒,一言一行皆在朝野裡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的思想理論和政治主張,會影響他大力推行的萬曆新政。他是一個善于決斷的人,也是一個“六親不認”的人,為完成他的改革大業,不要說這種轉彎抹角的師生關系,即便是他曾經服膺的師者如今站到了他改革的對立面,他也會毫不心軟,把他搬開。
張居正對天下書院下如此狠手,讓包括天真書院在内的書院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诏書下達到杭州後不久,天真書院轟然拆毀。
百尺秃牆在,三千舊事聞。
野花黏壁粉,山鳥煽爐煴。
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
兒孫空滿眼,誰與蔫荒芹。
在明朝文人袁宏道《天真書院陽明講學處》一詩中,看到了天真書院被拆毀後的樣子:百尺秃牆尚在,但那些祭祀講學的場景是再也無法重制了。徘徊于林中,所見皆野花野草,山鳥飛來飛去,一幅山野的圖景,讓人很難想到過去這裡曾經不絕于耳的朗朗書聲,晨鐘暮鼓,即便再響,也是衰敗的哀鳴,而非激勵的号角。
守仁是豁達的。沒有萬世不壞之軀,自然也沒有萬世不敗的書院。隻是,軀體不在,書院不在,但他的浩大學問會一直在。在他的經籍裡,也在杭州人的記憶裡。(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龐驚濤,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雲棲閣主,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成都市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錢學(錢锺書)研究者,蜀山書院山長。有《啃錢齒餘錄—關于錢學的五十八篇讀書筆記》、《錢锺書與天府學人》等著作。現供職成都時代出版社。
<b>【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歡迎向我們報料,一經采納有費用酬謝。報料微信關注:ihxdsb,報料QQ:33864057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