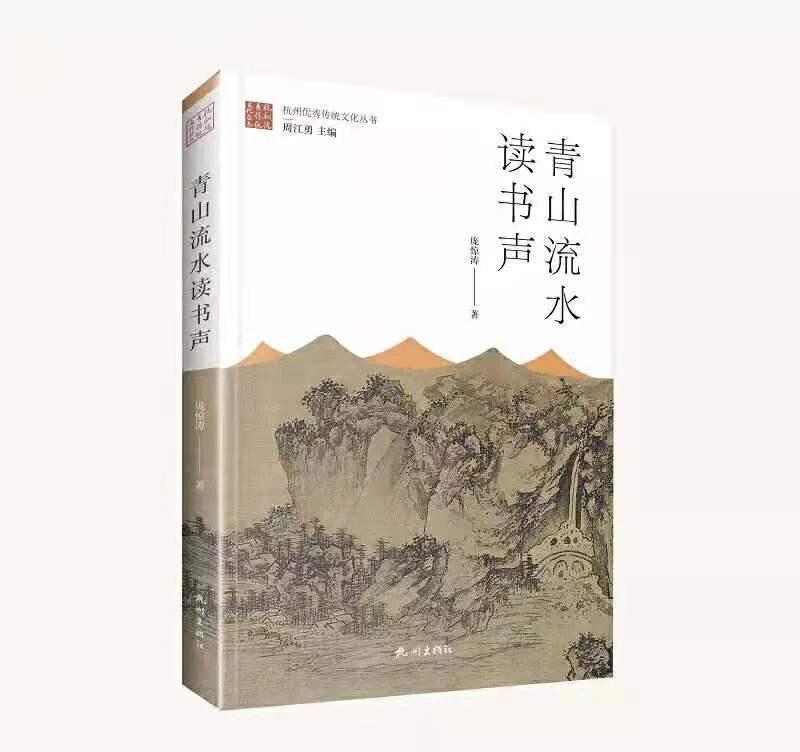
文/庞惊涛
6.留在杭州记忆里的天真书院
门人周积万万没想到,他竟能有这样非凡的“机缘”为老师送终。
他只道是一次平常的谒见,能得老师开示一二,即是莫大的福分。
在途细推谒见应答细节时,他已将老师此番平乱的前后事功作过细细的回放。以学问宗师而立至伟战功,学生的景仰和歌颂怎么都不为过。
他甚至悟出老师抗命回师正是行的“人伦之常”的无言之教。“庙堂之上”的大学士桂萼大约是不会懂得他的,所以下了进军安南(今越南)的命令。而老师要的,只是告病回家这个人伦之常。
周积没想到老师的病已到膏肓,所以面对老师的离去,开始是一阵慌然失措和手忙脚乱。稍一稳定方寸,方才驰书同门,报告这一悲伤的消息。
无论如何,老师匡扶圣学的人生任务到此就算完成了,作为门人,该一起商量怎么接过心学的大旗。王大用、刘邦采、汪鋐等,或早已有准备,或迎祭于道。灵柩过南昌、弋阳,直至二月,归于吴越故里。是年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
一切停当,周积才和同门深谈继承老师心学大旗的事业。
黄绾说:“老师早有遗言,‘无他所念,平生学问方见得分数,未能与吾党共成之,为可恨耳。’如何成?窃以为还是在开书院、讲心学。”
薛侃讲起往岁随老师游历杭州时的一段闻见,以此窥得老师之遗愿:
那是正德二年(1507)年夏天的事。早在二月,生性秉直不畏权奸的守仁就因为援救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而开罪宦官刘瑾,挨了四十板子后,贬谪贵州龙场驿。路经杭州,曾计划携一众弟子作名山胜水之游。天真山,即在学生们的计划之列。
戴罪在身,加之刘瑾追杀甚急,守仁不得不改变行程。虽然最终得以安全脱身,但未上天真山,到底成为了一件憾事。
对天真山之奇景妙观,守仁是有想象的。这美好的想象,源于一众弟子的交口盛赞,他甚至在意识里规划过天真山聚徒讲学的场景。
“如是,我们当为老师完成这一心愿。”讲完这段经历,薛侃道。
山在湖海之交而多奇岩古洞,钱德洪向老师推荐这里时,是有相当充足的筹划的,他明白此处风月佳构,正契老师素望。为摆脱刘瑾的追杀,老师不得不临时放弃游览天真山的计划,但到了西安,老师寄来两首诗,却能见其肺腑,其中两句,钱德洪念念不忘:“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门期。”“文明原有象,卜筑岂无缘。”老师坚信,一定会有他年筑室天真山的缘分。如今,即便老师肉体消亡,但灵魂不灭,就让这青山绿水,成为老师不灭灵魂的归隐地吧。
“庄子有言:真者,故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老师中岁以后,颇注意对道家思想的融摄,阐释良知学说,每有道家术语。山名天真,正是老师融铸儒道两家之本义,此其一;先生临终所言‘此心光明’,要在理解何为‘光明’,窃以为,‘光明’即‘天真’之别解。此其二。有此两端,此书院实已有老师生前赐之:天真精舍是也!”薛侃人如其言,此番侃侃而谈,让一众同门信服不已,当即议定书院即取名天真精舍,以祭祀老师、传承圣学为大业。
这番计议很快得到了一众同门的认同,大家为完成老师遗愿而倍感安慰的同时,也为同门之间有了长久的聚会之所而欣喜。诸同门大多本在公门,一呼百应,推进迅速;即便有少数不在当朝为官,但也是名家望族,影响地方。由此,筹措建造天真书院的经费便得到了保障。弟子们各自领责分工,很快,一个可同时招收一百多学生的天真书院就建起来了。
薛侃当仁不让,就建造天真书院的过程及书院规制作文记之,并勒石而铭。通过这篇《勒石文》,大体可以想象天真精舍初建早期的规制:
中为祠堂,后为文明阁,为载书室,右为望海亭,左为嘉会堂,左前为游艺所、传经楼,右为明德堂,为日新馆,余为斋舍。周以石垣,界则东止净明、西界天龙、北暨天真、南抵龟田路。
中间的祠堂,自然是祭祀先师王守仁的地方,是整个精舍的中心所在。由此也明确了天真精舍以祭祀为主的性质。24年后,门人欧阳德选址天真精舍上院,修建“仰止祠”,专祀先师王守仁,此后,春秋两祭,“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祭祀之后,是连续一月的会讲,四方同志参加祭祀和听讲,成为天真精舍数十年间弦歌不辍的盛大景象。
守仁应该是欣慰的。
而杭州城的儒生们,却为这个生于越城而遗爱杭州的大儒充满无尽的感激。所以,上至来浙任职的官员,下到普通的杭州儒生,对天真书院的增建和讲学都非常重视。据邹守益所记《天真书院改建仰止祠记》所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总制胡宗宪平海夷而归,思敷文教,以戢武事,命同门杭二守、唐尧臣重刻先师《文录》、《传习录》于书院,以嘉惠诸生。增修祠宇,加丹垩,搜泉石之胜,辟‘凝霞’、‘玄明’二洞,梯上真,穴蟾窟,径三峡,采十真,以临四眺;湘烟越峤,纵足万状,穹岛怒涛,坐收樽爼之间。四方游者愕然,以为造物千年所秘也。文明有象,先师尝咏之,而一旦尽发于郡公,鬼神其听之矣。
这是杭州儒生们追思守仁的高潮。
由是,天真山上,湖海之中,每每有朗朗不绝的吟诵之声。一派天真出自然,仰止亭下悟良知。从公元1530到1579年的数十年间,天真书院持续不断的祭祀和讲学,使杭州城成为守仁圣学当之无愧的传播高地,而天真书院的持续数十年的儒家经典讲学,也对杭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守仁自己想到了圣学在他身后分化的必然,但或许没有想到天真书院屡兴屡废、终至于毁弃的命运。更为关键的是,毁弃书院政令发起者,竟然是自己的门人之后。
说起来,张居正应是守仁的再再传弟子。因守仁看重并喜欢聂豹,便收他为弟子。聂豹在华亭时,又收了徐阶为弟子。日后徐阶做了首辅,奖掖和提拔尚是翰林学士的张居正,使他逐渐掌握实权,并有了抗衡朝中权贵的实力。徐阶功成身退,张居正很快接了他的班,成为万历初年独秉朝政的首辅。但他当了首辅后,并没有兴私学、建书院,反是毁书院、禁讲学。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皇帝下诏毁书院。“自应天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为公廨”。六十四个书院,就这样成为官府办公的地方,天真书院作为传播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场,也在毁坏之列。
张居正假手万历皇帝毁天下书院,理由是反对书院师生们的空谈误国,讲学牟利,而昭昭昌明的,在于他反复强调的实干兴邦。他讨厌那些清谈的读书人,对国家大事指手画脚,他需要经世致用的干才,也即他强调的循吏。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这班聚徒讲学的大儒,一言一行皆在朝野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会影响他大力推行的万历新政。他是一个善于决断的人,也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为完成他的改革大业,不要说这种转弯抹角的师生关系,即便是他曾经服膺的师者如今站到了他改革的对立面,他也会毫不心软,把他搬开。
张居正对天下书院下如此狠手,让包括天真书院在内的书院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诏书下达到杭州后不久,天真书院轰然拆毁。
百尺秃墙在,三千旧事闻。
野花黏壁粉,山鸟煽炉煴。
江亦学之字,田犹画卦文。
儿孙空满眼,谁与蔫荒芹。
在明朝文人袁宏道《天真书院阳明讲学处》一诗中,看到了天真书院被拆毁后的样子:百尺秃墙尚在,但那些祭祀讲学的场景是再也无法重现了。徘徊于林中,所见皆野花野草,山鸟飞来飞去,一幅山野的图景,让人很难想到过去这里曾经不绝于耳的朗朗书声,晨钟暮鼓,即便再响,也是衰败的哀鸣,而非激励的号角。
守仁是豁达的。没有万世不坏之躯,自然也没有万世不败的书院。只是,躯体不在,书院不在,但他的浩大学问会一直在。在他的经籍里,也在杭州人的记忆里。(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庞惊涛,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云棲阁主,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主任。钱学(钱锺书)研究者,蜀山书院山长。有《啃钱齿余录—关于钱学的五十八篇读书笔记》、《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等著作。现供职成都时代出版社。
<b>【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