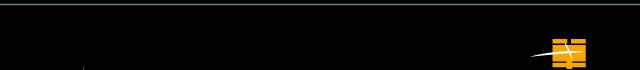
無論什麼制度,青春都會受到傷害。- 夏威夷大島
日本電影分為時代劇和現代劇,三井物産想知道歐洲是否也被時代分割。他以波蘭導演安德裡亞·瓦伊達(Andrja Vaida)為例,以解決他的疑慮。在這個過程中,《大島》呈現了一個在曆史面前忏悔的瓦伊達,一個從内到外困惑的瓦伊達。
曆史與遺憾:天使瓦伊達
夏威夷大島(周日)
周譯卷
在歐洲,任何與日本電影有很大關系的人都知道,日本電影中的時代劇和現代劇是有差別的。非常流行的Jidaigeki-gendaigeki概念,在電影雜志和報紙的批評和介紹專欄中是斜體的。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人們可以譴責我的無知,說我對将日本電影引入海外的人是多麼傲慢,他們的工作是多麼孤立和困難。但這不是我現在的主題。外國電影中有沒有這樣的時代劇和現代劇?當然,與"日本電影"相比,"外國電影"這個詞是非常專橫的。如果相當于日本電影的選址,那麼嚴格來說,應該一次一個國家來表示。然而,現在,為了友善或以某種方式,"外國電影"一詞指的是美國,亞洲和歐洲的電影。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劇和日本電影等現代劇在"外國電影"中有什麼差別嗎?恐怕它不存在 因為沒有這樣的差別,在描述日本電影時使用了"Jidaigeki-gendaigeki"這個詞,主要是介紹。
Anjaye Vaida電影中The Sewer的海報
當然,我讨論的前提是承認日本電影中有時代劇和現代劇。但是,我發現外國電影在相當于日本電影和現代戲劇之間并非沒有差別。本文将讨論Andrjaye Vaida,是以這裡有一個類似于他的例子。最近,我們終于看到了像耶爾齊·卡瓦洛維奇(Yerzi Kavalovic)的《法老》(Pharaoh)這樣的電影,這是一部像時代一樣的電影。換句話說,對我來說,幾乎所有具有古代背景的外國電影和大約一半的中世紀電影都是時代劇。小心翼翼地排除某些古代背景的電影是由于皮埃爾·保羅·帕索裡尼的一系列作品可能被算作不合時宜的戲劇;歐洲觀衆對此有何看法?當然,我知道沒有"時間戲劇"意識的架構。不過,他們有這樣的差別嗎?這方面的無知顯然是由于那些在日本引進外國電影的人的傲慢造成的,應該受到譴責;但是,難道現在不是我們了解真相的時候嗎?
我知道一個詞——古裝戲,像塞西爾·C·.B·德米爾的作品可以這樣稱呼。那麼費德裡科·費裡尼(Federico Fellini)的《愛的神話》(The Myth of Love)呢?在去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我看了這部電影,然後說:"什麼,那不是德米爾嗎?"作為回應,《綜藝》雜志的吉恩·莫斯科維奇(Gene Moscovici)滔滔不絕地說:"如果是德米爾,他會讓我們感到更快樂!"《愛情神話》真的可以稱為舊時古裝劇嗎?"或者可以稱之為時間劇嗎?歐洲觀衆對電影分類不感興趣。電影類型确實存在,例如指南中對電影的明确分類,戈達爾的作品經常被歸類為喜劇電影。但我沒有發現時代劇和現代戲劇在印刷品中至少有差別。
我為什麼要堅持這個問題?例如,最新的黑幫電影是時間劇還是現代劇?如果你去歐洲,被稱為日本電影,應該做些什麼來把它們分成不同類型的評論家?我覺得這種黑幫電影應該分為時代劇。最近,每年夏天都有戰争電影 - 或者更準确地說,戰争電影 - 出現,就像嚴格的正常怪物一樣。你如何劃分這些?在我看來,它們都是時間劇。是以,對我來說,所謂的現代戲劇是一部以戰後日本為背景的電影。這是我的想法和感覺,這種想法和感覺不正常嗎?我不這麼認為。我想有人會同意的。
讓我們回到歐洲。歐洲觀衆在觀看時會對自己國家的電影進行分類嗎?我想知道。
寫在這裡,我的話題終于來到了Angel Vaida。我們日本人對瓦伊達的作品知之甚少,我們通常可以看到四部作品:《下水道》(1956年)、《灰燼與鑽石》(1958年)、《無辜的女巫》(1960年)和《二十年的愛》(1962年)。他的作品的介紹也不夠。佐藤先生前往波蘭,向和田先生簡要介紹了"一代"(1955年),"Lotona"(1959年),"灰燼"(1964年)和"一切出售"(1968年)。我們第一次通過阿多蘭·塔利農(Adoran Talinon)的作品了解了瓦伊達的《參孫》(1961年)和《西伯利亞小姐悲劇》(1961年)。至于《天國之門》(1962年)、《千層》(1968年)、《驅逐蒼蠅》(1969年)、《戰後的土地》(1970年)等其餘的,我還是不知道内容。但即使是大約十個,我發現其中大多數都是基于過去。有五部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灰燼和西伯利亞小姐悲劇講述了一個更遙遠的過去的故事。隻有三部完全基于現代主題的作品,即《無辜的巫師》,《二十年前的愛情》和《一切待售》。在我對電影的思考中,瓦伊達是一個不合時宜的劇作家。當然,這是一個笑話。歐洲人當然對瓦伊達有不同的看法。塔利農說,瓦伊達第一次放棄了現代主題,在拍攝《西伯利亞悲痛小姐》時面對過去。這種感覺可能是正常的。實際上,我是這麼認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基于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的《洛托納》似乎屬于"面向過去的電影"的範疇。但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無法得出結論。
在這篇長篇大論中,我寫了很多似乎很有道理的文字。其實,我想說的是,為什麼和田的戰争題材電影在我眼裡是一部現代劇?當然,存在嚴格的時間問題。"世代","下水道"和"灰燼和鑽石"被稱為瓦伊達的三部曲,在1954年至1958年間拍攝和制作,可以假設戰争仍然在許多人的腦海中。毋庸置疑,這個問題在瓦吉達的心中也存在一個非常鮮明的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瓦伊達隻有十三到十九歲。後來,他這樣回答别人的問題:
佐藤先生:(...)這與你自己的戰争經曆有關嗎?
維達: ...我有某種情結。......在德國占領期間,我與地下組織有聯系,但沒有被關押在強制性庇護所。當時,我碰巧去了克拉科夫,沒有參加華沙起義。可以說,我懷念那個時代發生的一切。我填補了我工作經驗的空白。
Boreslaw Mihawik:你經曆了什麼樣的戰争?戰争期間你在哪裡?
維達: ...我幾乎沒有參加過抵抗運動。是以,我幾乎沒有戰争經驗。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在電影中彌補它。
《The Big Island》《Happy Christmas on the Battlefield》
我簡直不敢相信導演說的話。不要以為他對某人說了同樣的話,這是真的。但對兩個人說同樣的話至少可以清楚地表明,瓦伊達在心裡已經決定要回答這個問題。隻有這樣才是真的。好吧,讓我們來看看他的答案。一是他"很少的戰争經驗"或"幾乎沒有參加過"任何抵抗運動或地下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回答中的"經驗很少"或"幾乎沒有"可以替換為"完全缺席"。在我的猜測中,公平地說他可能沒有參加。但它沒有使用"完全不參與"這個短語,因為他仍然想參加。另一個是用一份工作來彌補這一點。雖然文字很美,但你能用作品來彌補行為的不足嗎?此時,面試官的詢問尚未到位。很明顯,瓦伊達本人一定認為這是無法彌補的。他自己知道,不可挽回的行為或o的不作為可能是創造的動機。
但是你能僅僅基于這種動機創作一件作品嗎?文學也許是可能的,但電影不能,至少僅憑動機是這樣。過去是無法彌補的,我們面對曆史是一種遺憾。最強烈的悔恨感是和田。面對曆史,一般人充其量隻是受害者般的遺憾。我認為,波蘭是世界上面對曆史最悔恨的國家之一。但即便如此,不,這就是為什麼普通人隻有受害者般的悔恨。在這一點上,Wada的抵抗和地下組織在曆史面前,什麼也沒做,隻是意味着他們有潛力發揮自己的優勢。然而,它一開始是一種悔恨的形式,一種連受害者式的悔恨都不能稱之為悔恨的形式。在羅德電影大學讀書時,當人們講述他們在戰争中的經曆時,我擔心薩達已經悄悄地離開了座位,也許他充其量會高興地說:"我真的沒有參加過戰争。"
在《下水道》、《灰燼與鑽石》中以主觀悔恨的形式呈現出這種面對曆史的遺憾之前,發生了什麼?WADA是否在1956年采取了主要行動,當時影響了波茲南的非斯大林化和民主化運動?
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情況,沒有書面記錄,沒有語言叙述,甚至佐藤中南都沒有去追。我這麼說并不是為了保護我心愛的佐藤。當時波蘭電影業可能有某種難以處理的氣氛 - 當我隻在波蘭呆了幾天時,我就感受到了這一點。是以,目前尚不清楚瓦伊達在這一時期做了什麼,當時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化運動像地下水流一樣活躍。但完全推測的是,與此同時,羅德電影大學和電影業無疑是民主化運動的據點。1954年出現了幾個名為"運動"的創意團體。以前由國家直接管理的電影制作開始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标志着電影運動比其他領域更加民主。當然,我們不知道和田在這個中間扮演了什麼角色,尤其是在政治領域。然而,在1954年,由導演上司的演員陣容和一些演員是新的,"在不同的原則下,他們制作了與以前截然不同的新電影"(Wajda),"一群将電影作為宣言的人"(Wajda)的上司者。在此期間,Vaida無疑發揮了主導作用。
事實上,如果瓦伊達顯然是非斯大林主義者,甚至更反斯大林主義者,他會走得有點太過分了。毋庸置疑,他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在從世代到下水道再到灰燼和鑽石的摸索過程中的反斯大林主義立場。如果有一個大膽的猜測,也許他對政治的思考已經達到了頂峰,直到灰燼和鑽石在下水道之後開始生産。而且,當他站在反斯大林主義的立場上時,波蘭的斯大林化和民主化運動正開始逆轉。就像馬爾奇克緊緊抓住被擊倒的鈴鹿時在他們身後綻放的煙花一樣,《灰燼與鑽石》之是以美麗而悲傷,是因為有一種沖動,想扭轉瓦伊達的潮流,瓦伊達已經走向了斯大林主義和民主化。
換句話說,面對1945年的空隙,Vaida在1956年將他面對的一切投入到歷史上,拍了兩部電影,《下水道》和《灰鑽與鑽石》。《世代》是一部情感作品,《洛托娜》是一部悲傷的副産品。是以,包括前兩部電影在内,它們完全是現代劇,永遠是現代劇,與一年一度的玉蘭盆地節上像怪物一樣出現的日本戰争電影截然不同。不過,我想在這裡提請注意,瓦伊達的現代劇絕對不同于一個在一個國家制作時間劇,但認為存在現代問題的導演。在作為物質的"過去"中,我們與曆史的關系随着我們現在與曆史的關系而不斷變化 - 就像瓦伊達的電影一樣。沒有這種過程的電影,以過去為基礎,隻是花架,無論作者的話語多麼強烈。這才是真正的"老前輩戲"。
說起古裝劇,我想到了這樣的事情。"Vaida故意要求Ziebleski穿流行的窄褲,"Taurenon說,引用了Prazowski在電影手冊中的一篇文章。瓦伊達一再強調自己思維的雙重面,即角色盡管坐在小酒館的椅子上,卻不喝酒精飲料,而是更喜歡喝馬基(反德)團隊水壺裡的水。然而,瓦伊達也強調了戴着1958年淺色眼鏡的英雄。"Taulinon引用了這段話,但他不明白這段經文的意思。他隻是是以接受了這句話。1945年的反革命抵抗(在語言上是多麼沖突!穿1958年的太陽鏡和緊身衣 - 這不是結果,而是方法。瓦伊達把一切都押在他身上。
在回答佐藤先生的問題時,"波蘭電影看起來好像在波蘭的高調事件之後幾乎沒有移動過,"卡瓦列羅維奇先生回答說:"有時他們幫助人們制作好電影,有時他們陷入危機。"這句話很精彩。我問了同樣的問題,也得到了同樣的答案。對于瓦伊達來說,1958年之後的波蘭時間可能不是"幫助他拍好電影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是否幸運,但從那以後我隻看過他的一部電影,"二十年的愛情"。相反,這部電影在"現在"中加入了"過去",是一部優秀的電影。我沒有看過他的其他電影,也沒有發言權。但看完他的電影後,我感受到了瓦伊達的苦澀。
如果以現在現代性為主題,瓦伊達在曆史面前可能不能像1956年那樣發揮,是有局限性的。即使以戰争為主題,這也是一件非常遙遠的事情,恐怕參孫被批評為"冷漠"是很自然的。一種基于遙遠過去的傑作拍攝傑作的新方法可能還沒有被發現。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可以從Vaida的電影中清楚地看到,他從内到外都面臨着困難。
"如果我是自己作品的制片人,并且我可以在經濟上獨立,我将能夠制作第二代和下水道。這是瓦伊達在回答伊萬娜·芭比的問題時所做的一次悲傷的對話,該問題于1963年1月4日發表在《世界報》上。是以,我們将想到社會主義制度下藝術家的命運。但是,作家不得建立"第二××"。我不相信字面上的意思。瓦伊達的電影充滿了絕望和苦澀,但他并沒有退縮。我想盡早看到在茲比格涅夫·齊布爾斯基去世後開始的電影"一切待售"。由于1968年貝加爾默國際電影節充滿了"平庸的作品",是以沒有頒發任何獎項。許多人強烈反對,馬塞爾·馬爾文(Marcel Malvern)在《1968年電影》(Film 1968)中大喊:"如果陪審團能判給平庸,那就太好了。這是因為除了《憂郁的高盧人》(由米歇爾·庫諾執導)和羅伯特·克萊默的《邊緣》、《宴會與客人》(由Jan Nemek執導)、《一個女人和另一個女人》沒有被提及之外,還有兩部最好的未出版作品:瓦伊達的《All for Sale》和日本導演大島的《絞刑》。你說的平庸是什麼意思?!"也許是有了這樣的命運,也許有點情緒化,我發現瓦伊達在《一切待售》之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拍攝了《千層》(1968年)、《驅逐蒼蠅》(1969年)、《戰後之地》(1970年)等作品。我想這一定是有原因的,非常期待。Ziebleski的死可能點燃了Vaida心中的激情。瓦伊達必須做兩件事,一件是否認,另一件是繼續包容曆史和自我過早被發現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在波蘭,藝術家比其他國家多得多,"Wajda說。"有時是榮耀,有時是沉重的責任。和田遠離大規模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鬥争,遠離資本主義國家,一再受到創傷,但不斷産生新的突破,以推進新的左翼革命運動;如果沒有1956年的去斯大林化運動,瓦伊達與之相關的民主化運動,快節奏的堅持制作電影具有重要意義:将會有"鑽石像勝利的曙光一樣閃耀",這是波蘭人民的要求之外的。甚至遠遠超過波蘭國家的要求。
作者:大和(日本)
出版社:亞竹文化/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 - 6
單讀産品,轉載請到背景查詢
無條件歡迎分享轉發給朋友
按住以識别二維碼
買音樂劇"洗衣服"的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