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唐山
"無論如何,我總是想象一群孩子在一個大麥田裡玩遊戲,成千上萬的孩子,我旁邊沒有人 - 我的意思是不老 - 我的意思是這隻是我。我會站在懸崖邊上。我所要做的就是抓住每個跑到懸崖上的孩子 - 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跑上去不看方向,我必須到那裡去抓住他們。我整天都在這樣做,我成了麥田裡的守望者。我知道這很離譜,但這是我唯一真正想做的事情,我知道這太離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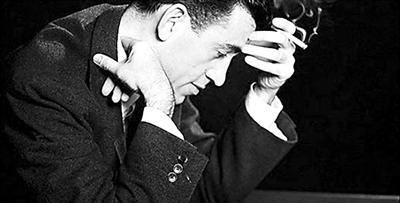
在孫忠旭的譯本中,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是如此平易近人,遠不如石顯榮的譯本那麼有力。
在中國世界,大多數塞林格的粉絲都被石賢榮的翻譯所感動。
2019年1月1日,正值塞林格誕辰一百周年之際,塞林格著作的譯本,塞林格的作品首次在中國出版,是塞林格基金會權威評論的新譯本。
它被稱為全套,但它不是全部。塞林格的"去看埃迪","把戲","瓦利奧尼亞兄弟","麥迪遜的溫和叛亂","破碎故事之心"和"颠倒森林"等短篇小說沒有收到,晚期的"哈普沃斯16,1924"也沒有收到。
全套在兩點展現了塞林格的風格:一是封面設計簡約。第二,沒有前言、後記等。它最大的價值在于它對塞林格文本的原始外觀的忠實。他們是瑣碎的、解構的、反句子的粉絲,每個故事都是平淡無奇的,隻有深入其中,塞林格才能明白他想說什麼。
事實上,閱讀塞林格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有些令人擔憂:在一個日益放松的時代,塞林格會被遺忘嗎?他的反抗和掙紮有意義嗎?
他一直是一個失敗者
塞林格的生平和小說有兩個主題:失敗的成長和對失敗的熱愛。
塞林格的成長是失敗的,他從未達到父母的期望。他有六次失敗的情感經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塞林格回到維也納試圖找到她的初戀,但猶太女孩去世了,她主演了小說"我認識的女孩"(不包括在完整的收藏中)。
塞林格愛上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女兒烏娜(Una),後者利用塞林格的服務,嫁給了笑星卓别林。在小說《悲傷的警長》(The Sad Sergeant)中,塞林格含蓄地諷刺了卓别林。
1946年,塞林格娶了一位在德國出生不到八個月的法國女子。她嫁給了克萊爾,育有一女,一起生活了13年。五年後,塞林格搬進了大學生梅納德家,一年後兩人分手了。73歲時,塞林格嫁給了一位比他小40歲的護士。
失敗的成長和失敗的愛情是交織在一起的,是以在塞林格的寫作中,教授大多是虛僞的、世俗的,大多數女孩都是膚淺和虛榮的(除了弗蘭尼)。
成長是必要的潰爛
塞林格的寫作經常被"純真頌"和"觀看孩子般的真理"等大詞所掩蓋。
按照這個例子,那麼"充滿欲望的成人世界"和"純潔的孩子的世界"是互相對立的,塞林格飾演的泰迪、考菲爾德、佐伊等人因為"初慧"而參與前者的虛幻,不得不承擔"半智能"的負擔。
概括是美妙的,但它用哲學智慧來掩蓋小說的智慧。
除了哲學智慧,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它?如果隻是高層的抱怨,有必要存在嗎?
在智慧小說中,作者不承擔給出解決方案的義務,作家的義務在于發現人的真實狀态和挖掘故事。
"發現"是塞林格小說中最有趣的部分,而不是抱怨。他的"發現"石頭是一種震撼——成長是一種必須通過的潰爛。
所謂"成長",是一個現代概念。在前現代文化中,沒有"童年"、"少年"等等,孩子被認為是被壓縮的成年人,教育是一種奢侈,隻有少數孩子才能享受。
現代社會的代價之一是人們需要長期的教育來适應它。結果,成年人通過資訊掩蓋、暴力和集體生活迫使兒童接受一種控制狀态,法國哲學家福柯稱之為"監獄社會"。
塞林格小說的價值在于,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搞笑娛樂、一群英俊美女,一聲呐喊"我真的想接受這種潰爛嗎?
他不需要一個好故事
閱讀塞林格并回到他的文本。
閱讀塞林格的作品和王碩的作品是有共同點的:一種特别凄美的、消費主義的玻璃文化,對救贖感到困惑。不同之處在于:讀王碩的人會覺得自己變成了一個開悟的人,更願意主動去攻擊,讀塞林格的人會覺得他被束縛了,更願意逃避。
王朔也寫過很多悲劇,為什麼沒有産生塞林格小說那樣的效果呢?從Glass系列中可以看到它。
格拉斯系列由六部小說組成,"捕捉香蕉魚的最佳日子","弗蘭尼","舉起光束,木匠","佐伊","西摩:傳記"和"哈普沃斯16,1924"(前五集都集中在一起),所有這些都以西摩·格拉斯為特色。
西摩·格拉斯的名字似乎是隐喻性的,在英語中,語氣接近于"看到更多的玻璃"。西摩也是一個"清晨"的人,他的憤世嫉俗對他的弟弟妹妹産生了巨大的影響。他莫名其妙地愛上了膚淺的女人穆裡爾,但拒絕參加婚禮,幾乎冒犯了所有人。
婚後,西摩和妻子去海邊度假。他的妻子在一家酒店修指甲,讀《性:天堂或地獄》,并與母親長途跋涉。西摩在橡皮筏上,在海面上和一個五六歲的女孩西比爾聊天,說海裡有一條香蕉魚會進入香蕉洞,繼續吃香蕉,他不能再從洞裡遊出來,因為他越來越胖,他死于香蕉熱。
這顯然是對唯物主義的隐喻。西比爾說,她看到香蕉魚嘴裡有六根香蕉。
西比爾告訴西摩,就連孩子們也充滿了謊言,所有通往救贖的道路都被封鎖了。回到房間裡,西摩開槍自殺了。
正是精神上的痛苦,讓塞林格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在精神上難以忍受。塞林格不需要設計一個好看的故事,他不需要在故事中隐藏結局的合法性,是以他的悲劇更具感染力。
每個人都在撒謊
小說是漸進開放的藝術,留住讀者是作家一生都在練習的功夫。塞林格小說的故事情節比較簡單,他如何留住讀者?在《弗蘭妮》中,有一場特别精彩的表演。
人們普遍認為弗蘭妮的原型是克萊爾。塞林格19歲時追求她,正在大學學習。塞林格希望克萊爾辍學,但被拒絕了。克萊爾曾經結過婚,幾個月後他們分手了,克萊爾和塞林格結婚了。
塞林格一生都在尋找年輕、不善于交際的女人,他更喜歡做一個父親而不是戀人。
《弗蘭妮》的主角弗蘭尼正在和著名學生瑞安約會。瑞安是一個典型的中産階級孩子,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說話,沒有人有尖銳的聲音,慷慨的聲明,仿佛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個極具争議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讓大學以外的世界在幾個世紀以來一直保持着翅膀。
Ryan談論了很多關于小說,詩歌和戲劇的事情,但他主要關心的是報紙能否獲得"大A"。弗蘭尼試圖扮演一個文學愛好者的角色,以配合瑞安的演講,瑞安可以吃蝸牛,青蛙腿和沙拉。
塞林格的女性大多是物質女性,《麥田裡的守望者》一直受到女性讀者的批評,《弗蘭妮》很可能是女性版的《麥田守望者》,是對女性自我覺醒之路的描述。
考菲爾德選擇逃離城市,弗蘭尼在長時間的耐心之後終于暈倒了。
塞林格喜歡寫對話。人生就是舞台,每個人都戴着語言面具,這歪曲了對話本應是邏輯,展現了内心深處的戲劇性:每個人都在撒謊,都認為自己是主角,卻是在虛拟生活中。這構成了Selin格式的豐富性,使其不受捏合情節幹擾。
啟蒙來得有點晚
早在1963年,《麥田守望者》就有了中文譯本,隻能"内部發行",直到1983年才能公開出版。幾年後,這本面向中學生的書出乎意料地在大學校園裡流行起來。
當時,中國讀者還沉浸在現代教育的神話中,作為治愈世界的良方,大學生被譽為"天上驕傲的兒子"。然而,經過聯考的艱難通過,卻發現生活本身并沒有改變。
從夢境跌落到現實,迫使人們反思存在。
《麥田裡的守望者》被稱為一代人的"啟蒙之書",太多人開始從中尋求自己的覺悟之書。但畢竟這種啟蒙為時已晚,啟蒙大悟基本上是聯考制度的受益者,當他們帶着"黃鶴樓看船"的心态去讀這部小說時,就成了一種思考。
我們看到的是塞林格是一個隐士,一個思想家,一個生活偶像,而不是一個小說家。
此後,中國小生的負擔明顯加重,今天還有多少孩子在讀塞林格?畢竟,這部小說的抵抗力太脆弱,太有限,遠不如電子遊戲那麼直接。
視訊遊戲提供了一個可玩的、可操縱的空間,人們不必忍受覺醒的痛苦。
終于明白了塞林格在說什麼,一代人已經老了,要麼是瑞安,要麼是斯賓塞先生(科爾菲爾德的老師,僞君子),要麼是穆裡爾......成為他們年輕時讨厭的角色。
上一代人誤讀了,下一代人根本沒有讀過。也許塞林格會漸行漸遠。(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