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仁貴為大唐東征西戰,其子薛丁山和孫子薛剛亦是保衛大唐河山的英雄人物;楊業一生跨馬平天下,七子亦是北宋的頂梁柱。将門之家,能在王朝間百年無虞,家風的傳承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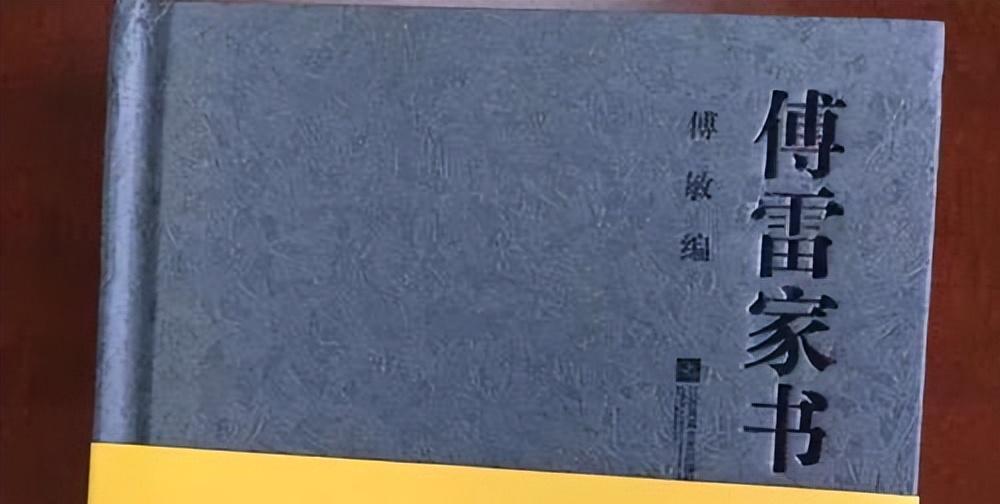
諸葛亮曾在《誡子書》中談到“<span data-bjh-target="非澹泊,非甯靜無以緻遠”,《傅雷家書》和《曾國藩》亦可作為教導後人的依據。隻不過,虎父不可能永無犬子,家風傳承不好,名貴勳家亦能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張之洞一身清譽毀于後人
晚清大廈将傾,李鴻章、張之洞等一衆老臣扶着顫顫巍巍的大清,試圖護住大清的國脈。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的名聲可不比李鴻章小,隻是相比于李鴻章,張之洞背負罵名更少。
張之洞本人并沒有诟病之處,于大清、于個人,張之洞都把“修身、治國、平天下”時刻謹記,唯獨“齊家”這一條,張之洞沒有限制好後人,不僅連累了自己還拖垮了國家。
五歲入私塾、十四歲中了秀才,因幫助父親處理公務同治二年進士及第,張之洞的仕途一路上順風順水。以張之洞入朝之後的所作所為,張之洞的父親必然是注意家風的傳承,尤其是愛國和變革這兩條,必定是每日敲打。
法國來犯,張之洞在廣州嚴防死守;他國強大,張之洞開始朝廷興辦洋務、主張變法。張之洞在世做的每一條,都是在為滿清殚精竭慮,那條條框框都是藏着一顆老臣的愛國心。滿清能在八國的虎視眈眈下苟延殘喘多年,這其中張之洞有一半的功勞。
可能是張之洞一心撲在朝廷上,忽略了子女的教導,這才導緻子女毀了自己一生累積的清譽。等到小兒子張仁蠡降生時,張之洞已經六十三歲。老來得子,門徒衆多,自己又是高官厚祿在身,張之洞覺得人生不過如此。
隻是此時張之洞有心管教子女,可老天已經不準備給他更多的時日。張之洞去世之時,張仁蠡還是一張白紙,張之洞給小兒子留的後路就是交予五子張仁樂教導。一步錯,步步錯,張之洞給小兒子留下的後路,給中國埋下了禍根。
兄長言傳身教毀了一張白紙
張之洞擁護的是大清朝,可并不排斥他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礙于滿清當年的現狀,張之洞自然在家中多有談論兩國之間的差别,而這一切被張仁樂耳濡目染。
當年,張仁樂被送往日本,張之洞本意是希望兒子能夠學習先進技術與思想,但張之洞給兒子呈現的晚清頹廢的面貌卻讓張仁樂再無報效國家的心思。
中國文化焉能不如日本,張仁樂更多地是被日本社會的繁榮所迷惑。在這般崇洋媚外的哥哥身邊,張仁樂的思想自然與張仁樂“一脈相承”。
張之洞隻是痛恨滿清的落後,可卻願意以一己之力匡扶天下。張仁樂不同,張仁樂以滿清為恥,對滿清的高談闊論也是把滿清貶到塵埃,昔日老祖宗留下的精華也被張仁樂踩一腳,而日本丢棄在路邊的垃圾在張仁樂嘴邊也是香的。
在兄長的言傳身教中,張仁蠡這張白紙自然也成了第二個張仁樂。晚清倒台之後,北洋軍閥登上曆史舞台,之前張仁樂和張仁蠡兄弟倆隻是在家中談論,可北洋軍閥與國外勢力的靠攏卻讓兩兄弟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
張仁樂在東北地區籌謀,做了李景林的走狗,可李景林又與日本人聯系緊密,是以這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更是助長了張仁樂的野心。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享受着中國的資源,張仁樂卻在日本人的庇護下大肆斂财同時傳播日本文化。張仁樂想要把東北變成日本人的王國。
哥哥迫害老百姓,張仁蠡在他的庇護下焉能有憐憫衆生的同理心?張仁樂已然沒了良知,又怎麼能夠祈禱一個自小生活在惡魔身邊的小惡魔有任何的良知呢?這兄弟倆比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兩兄弟一個逃脫一個被捕
張仁樂後期已經徹底歸屬于日本人的名下,張仁蠡自然也不甘落後。張仁蠡後來成了武漢市的市長,為官者應造福一方百姓。但張仁蠡做的不是中國人的官而是日本人的官,武漢的百姓就是張仁蠡對日本人的孝敬,隻需要日本人一聲令下,張仁蠡就能獻上讨好。
張仁蠡一心想着日本人能在短時間滅亡中國,而自己作為日本人對接中國的負責人,自然是頭等功,到時候榮華富貴是唾手可得。隻是,張仁蠡的想法成了妄想,他最不看好的國家成了勝者,他最看好的國家灰溜溜地逃走,至于為日本效力的張仁蠡,自然被丢在了國内。
日本從中國撤軍的速度很快,甚至來不及接走留在中國的國民。連自己國家的群眾都可以丢下,何況是張仁蠡一個外國人。張仁蠡是貨真價實的漢奸,他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就應該受到淩遲之刑。
張仁樂和張仁蠡兩兄弟是在建國之後論罪查處的,隻是張仁樂因為妻子從中周旋逃亡到了日本,而張仁蠡被處以死刑。
張之洞在國内享有多大的聲譽,張仁樂和張仁蠡就在國内有多大的唾罵聲。子不教父之過,張仁樂和張仁蠡在國内的為非作歹,張之洞沒能一點點的責任?張之洞為滿清鞠躬盡瘁,并不能替他的兩個兒子折罪。
日軍帶過來的兵力有限,真正能在中國土地上為非作歹的是那些主動向日本人“投誠”的中國人。國家生死存亡之秋,國人卻成了我們的對立面,實屬不該。父親有罪,的确不應該禍及子孫;但子孫有罪,卻與父輩脫不了幹系。
張仁樂和張仁蠡的所作所為,也是張之洞一生中最大的黑點,張之洞對得起滿清,卻對不起民國時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