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僅46歲。在他逝世60周年之際,我們重讀他影響範圍最廣的經典之作《社會學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會科學的想象力。我們專訪了陳映芳(社會學)、任劍濤(政治學)和劉海龍(傳播學)等三位學者。本篇為對社會學者陳映芳的專訪。
人與社會的關系是米爾斯闡釋“想象力”的基本内容之一。當個體陷于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時,借用社會學的想象力可以探尋周邊世界,發現社會的結構架構,了解此架構與我們的關系,概括出我們的狀态。陳映芳認為,了解周邊世界的能力,其本質是習得的。而對于研究者來說,挑戰則是如何形成“基于内心價值關懷的問題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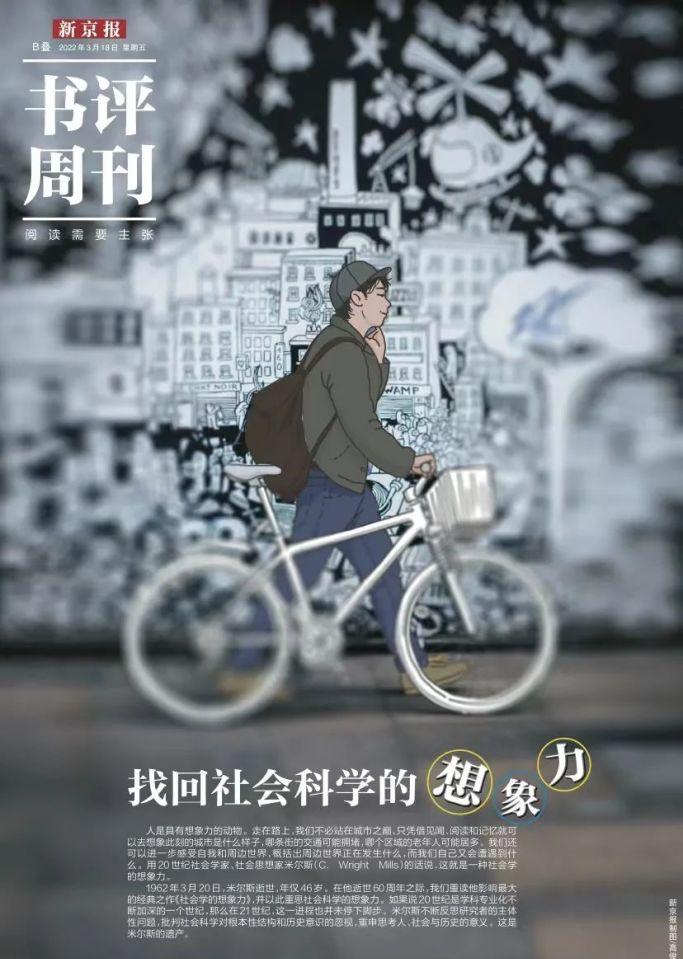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3月18日專題《找回社會科學的想象力》的B05。
更多内容詳見:
遺憾的是,我們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丨紀念賴特·米爾斯逝世60周年
政治學研究的曆史視野丨專訪任劍濤
采寫|羅東
陳映芳,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青年”與中國的社會變遷》《城市中國的邏輯》《秩序與混沌:轉型中國的“社會奇迹”》等。
米爾斯對感受性的強調
新京報:你還記得第一次讀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情形嗎?
陳映芳:具體記不清了。我是上世紀90年代初接觸社會學的。1992年剛到日本時,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招聘外國人學者”的身份。正式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前,我曾在京都大學旁聽社會學的課程。然後因為家庭原因,到大阪市立大學讀了一年“研究所學生”(相當于“大學院生”的預備生),最後正式參加大學院社會學專業的入學考試。學習社會學、乃至了解米爾斯的學術,是跟着自己内心的沖動一步步摸索的過程。
最近,我找出從日本帶回來的資料,發現我手邊的日文版《社會學的想象力》是1995年紀伊國書店出版的“新裝版”。它是1965年被介紹到日本的,譯者鈴木廣教授(日本研究米爾斯理論的專家,著有《米爾斯的理論》),初版到1984年時已經印了14次。上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自費留學生,讀書主要是到圖書館借,購買新書要思量再三。好在那時的日本舊書市場還很好,大學裡和便利店裡的影印機也已經普及。是以,除了與博士論文主題直接相關或特别感興趣的新書需要下決心買下來,其他的文獻主要靠淘舊書,或者摘要影印。
後來《社會學的想象力》有了簡體中譯本。我手邊的《社會學的想象力》是陳強和張永強翻譯、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7月發行的初版。
由于我接觸米爾斯的學術時,對美國50、60年代的社會學史,以及米爾斯的學術思想演變軌迹,特别是他自身在那樣的時代中曾經曆的精神沖突等,都缺乏相應的了解,而主要是結合當時我自己的問題尋找學術資源和方法參照,是以,對當初我的研究來說,《性格與社會制度》和《社會學的想象力》好像是一體的——前者對我當初的研究有直接的影響,是我博士論文的重要參考文獻,同時它也讓我更容易接受後者的學術價值。
《性格與社會制度》是米爾斯和他的老師格斯(Hans Heinrich Gerth)合著的,1953年出版。格斯對米爾斯産生過重要影響,他們曾一起合編過馬克斯·韋伯的著作。但自米爾斯發表《權力精英》後,他被學術界一些人視為激進的異類,也與一些朋友漸行漸遠,包括格斯。這兩天我翻出《性格與社會制度》,發現中間還夾着幾頁當初寫的讀書筆記,對要點和重點的歸納。簡單來說,除了“性格結構”及其形成機制、“社會制度”的曆史性變動等基本内容外,它的重點之一是論述了在作為個體的“人”和“制度”之間,“角色”作為中介項的意義和操作性。這本書很厚,結構龐大,我的筆記中特别一條條地歸納了米爾斯和弗洛伊德·米德的對比,并勾勒了有關社會學制度研究的學術史經緯,以及書中有關曆史次元的意義。這讓我意識到,米爾斯後來的學術盡管一直強調人的感受性的重要,以及如何從個體中發現社會整體,但并沒有走向社會心理學的微觀社會學研究,這應該跟他早期跟導師一起從事的韋伯研究,以及“性格與社會制度”的研究,有直接的關系。
米爾斯與導師格斯合著《性格與社會制度》(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99年再版封面。
“周邊世界”與每個人有關
新京報:想象力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在人的處境與社會的結構之間穿梭的能力,依米爾斯的了解,也便是“清晰地概括出周邊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他們自己又會遭遇到什麼”。自上世紀以來,絕大多數研究者都接受人的行為是社會性的、文化性的、制度性的,那麼,自然而然就會由此去了解背後的社會結構,而不會滿足停留于個體生物和心理等微觀層面。幾個主要的宏大叙事諸如“後現代主義”“消費主義”甚至成為解釋“周邊世界”的靈丹妙藥。而在中觀層面,社會調查研究也在不斷收集個體層面經驗資料,歸納分析“階層”“教育”“社群”等中層概念,關注着個人之外的“周邊世界”在發生着什麼。總之,将人的處境和“周邊世界”連接配接起來好像是人們一直都在做的。那麼,想象力還是一個問題嗎?我們需要了解的那個“周邊世界”是什麼?
陳映芳:中國社會學經曆過一段被取消的曆史,在改革開放後恢複重建,當時,無論是“南開班”(由社會學家費孝通等人組織舉辦的社會學研究所學生班)畢業的,還是早期從海外留學歸來的,他們接受的社會學專業訓練大多都基于同期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範式也受其影響,而我們的社會因其所處的不同時期,事實上最需要的是更早一些的如古典的或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學研究。你可以看到,這裡有“現代”與“後現代”的錯位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所處的社會接近米爾斯當初的情形,包括冷戰開始後的國際關系和美國國内社會秩序的邏輯,以及社會科學的功能、地位在學術研究智庫化背景下的變化等。
以上是我的一些了解,在這個基礎上再來說你提的“周邊世界”。
我們每個人都是會關心“周邊世界”的。在過去,人們可能主要關心的還是家庭和傳統共同體等内群體、地域社會,而在近代化過程中則關心民族國家命運,在計劃年代也關心機關的事。在20世紀80、90年代市場化過程中,個體進入市場,隻不過也是帶着家庭進入的。而此後,城市化和城市大開發也引發了諸多重要的變化,包括我們如何了解城市的開發機制、市民的财産安全,當然在這其中既有家園也有社群的命運。由此我們還可以關注到公共資源配置和社會公平等問題。這些都屬于“周邊世界”的範疇。我們無法說“我這個地方”或“我這個階層”好就好,命運有連帶性,遠方發生的災難也是我們的災難。甚至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的災難都可能改變我們國家的命運,進而影響到每個人。
《城市中國的邏輯》,陳映芳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5月。
人作為主體的條件
新京報:接着你剛才說的“每個人”,如何了解既是想象力對象(被研究時),也是想象力主體(去感受并了解“周邊世界”時)的人?
陳映芳:人的社會學想象力是有條件的。按照阿倫特的說法,人需要成為完整的人。在有關社會調查的制度架構中,專業的調查機構及其從業成員的存在,以及他們展開調查的動因和基本條件,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商家需求,或者則附着于大學科研項目之上。也就是說,在有關社會調查的制度中,我們的“社會”、“社會成員”,其實多隻是被設定為調查的對象、被诠釋的客體,其本身卻并不具備研究社會、了解自身的基本條件。而市民之成長、社會之成熟,需要社會成員具備相應的認識自我、诠釋自我的基本能力,唯此才能成為社會權利、社會主張的聲張者,成為推動社會自我變革的真正主體。
從社會學關于“角色”的認識角度看,我們作為人,其身份也是具體的社會人,換言之我們生活在角色叢中,擔任着家庭的、親密關系的、職業分工和公共生活等方面的不同角色,而其中一個基本的角色是共同體成員資格(市民、社群居民)。
我們都知道,角色是習得的,關心“周邊世界”,将個體的境遇想象成公共的問題,則是角色習得的一項基本内容。
當然,實作這一“自我發現”始終還是個問題,或至少是個過程。在我們今天的大學中,學生們并不缺少參加各類專業實踐的機會,比如由專業教師、政治輔導員以及團組織等等牽頭的科研項目、調查課題多得讓學生們應接不暇。然而,基于人們了解自身狀況、關心社會命運等動因的、獨立自主的調查研究,缺少足夠的鼓勵和支援。在現實中,以我這些年來的教學實踐而言,鼓勵學生們探索自己内心關心的問題、指導學生們從事真正以自己為研究主體的社會田野調查,幾乎成了另類教學實踐。在教師,從課題或市場項目中騰出精力來,已是不易;在學生,業績競争需要之外的專業訓練有何意義?而且,對不少學生而言,“基于内心價值關懷的問題意識”這樣的要求,也意味着某種陌生的路徑。
新京報:在研究多年或緻力于社會學研究的學者那裡是一個問題嗎?
陳映芳: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們的知識、思想,其本質上是從現世關懷出發的。可是,人們對社會的知識探索,卻又往往集中于對過往曆史或遙遠世界的研究。對于這種現象,一種可能的解釋或許是:有關我們身處的現實社會、我們體驗的日常生活,人其實更難獲得客觀的認知、普遍的解釋,人的知識探索難免迂回曲折。
此外,普遍知識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作為認識主體的“我們”的存在。就譬如今天的我們可以接受有關曆史的普遍知識,而東方的我們有可能形成關于西方社會的普遍認知。但是,當面對身處其中的現實社會、面對日常生活,幻象的形成既缺少必要的距離和空間,人們不同的觀念、不同的生活體驗更可能阻礙普遍知識或廣泛理論的形成。
社會學的難題就在于:它不僅主要以現實社會為認知對象,而且相信,經由邏輯整理、經驗檢驗,人可以認識社會現實,并以客觀性來克服由人們的觀念、意識形态對事實的任意诠釋。可以說,對客觀性的探索是社會學的基本價值之一,但是,它也是社會學背負的沉重擔子,是以在一般意義上,你說的也是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