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又呈吳郎》是大陸偉大的詩人杜甫寫的一首七言律詩。律詩有一條最基本的不可動搖的法則,就是隻有八句。是以,這首詩也隻有五十六個字。但是,在這五十六個字裡卻包含着豐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藝術成就。
杜甫寫這首詩的經過和目的是這樣的:公元767年,也就是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裡。草堂前面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幹涉。後來,杜甫把這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居住,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裡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堂前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知道杜甫是這草堂和棗樹的主人,就來訴苦,杜甫因而寫了這首詩去勸告吳郎,希望他能和自己一樣體貼那個寡婦。在寫這首詩以前,杜甫已經寫過一首詩給吳郎,題目是《簡吳郎司法》,是以這首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但是為了使他能比較容易地接受自己的勸告,是以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一個表示尊敬的“呈”字。這個“呈”字看來好像和對方的身份不大相稱,但卻是必要的,正是杜甫細心的地方。白居易詩《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說:“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僚栽。”這詩題裡的“呈”“簡”,表明身份。可知杜《又呈吳郎》一題,不用“簡”字,确是有微意,非泛泛。清人陳醇儒《書巢杜律注》引許合伯說:“詩家有題目看似沒要緊,而發詞卻極關系,極正大者,須就此詩細參。”也注意到這首詩的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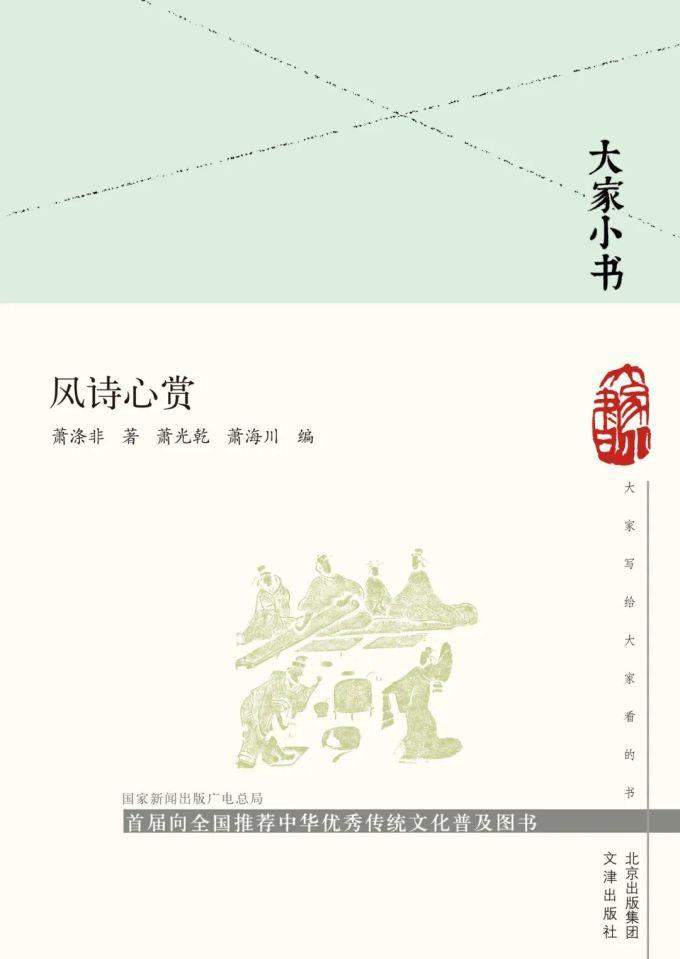
《風詩心賞》,蕭滌非,文津出版社,2020年9月。
杜甫是怎樣勸告吳郎的呢?且看原詩的第一句“堂前撲棗任西鄰”,開門見山,從自己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杜甫另有一句詩“棗熟從人打”,可見“撲”和“打”是一個意思。這裡為什麼不用“打”而用“撲”呢?這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緻。杜甫寫這首詩的時候,心情是沉重的,是以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着的入聲字“撲”。“任”就是放任,一點不加幹涉,愛打多少就打多少。這個“任”字很重要。為什麼要這樣放任呢?第二句就回答了這個問題:“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西鄰竟是這樣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沒有丈夫、沒有親戚,一句話,什麼也沒有的老寡婦。杜甫寫這句詩,仿佛是在對吳郎說:朋友!對于這樣一個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窮苦婦人,你說我們能不任她打點棗兒嗎?
詩的第三、四句:“不為困窮甯有此?隻緣恐懼轉須親!”“困窮”,緊接上第二句來;“此”,指撲棗這件事。這兩句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為窮得萬般無奈,她又哪裡會去打别人家的棗子呢?正由于她總是懷着一種恐懼的心情,怕物主辱罵,甚至把她當作盜竊犯,是以我們不但不應該幹涉,恰恰相反,而是要表示親善,表示歡迎,使她安心撲棗。在這裡,杜甫對寡婦撲棗的原因做出了正确的合乎情理的解釋,說出了窮人心坎裡的話。這和他的另一句詩“盜賊本王臣”所表現的“官逼民反”的進步思想正是一緻的。陝西有這樣兩句民歌:“唐朝詩聖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真是不假。以上四句,一氣貫串,可以算是一段,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當然不是為了表彰自己,而是為了啟發吳郎,使他認識到插籬笆這種事萬萬做不得。
詩的第五、第六兩句才落到本題上,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要聯系起來看,它們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上下一氣,互相關聯,互相依賴,互相補充的。上句的“即”字,當“就”字講。“防”是提防,心存戒備,是以說防。“防”字的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串起來講就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着你禁止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着插籬笆,卻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你自己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你不特别表示親善,也就夠了,為啥還要忙着插上籬笆呢!這兩句詩,措辭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傷害了吳郎的自尊心,會引起他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在這裡,有必要附帶談一下關于“遠客”的解釋問題。有的注解說“遠客”是指“過路的客人”,“防遠客”是防備過路的客人打棗。這樣,“防遠客”的人也就不是寡婦,而是吳郎了。我以為這是不對的。遠客就是遠方作客的人,古典詩歌中從來沒有把過路的客人叫作遠客的。杜甫自己的詩就可以做證,像《虎牙行》:“遠客中宵淚沾臆。”又《早發》:“艱危作遠客。”這“遠客”就都是指的他自己,而不是泛指什麼過路的客人的。而且照“過路的客人”這種解釋,“雖多事”的“雖”字就講不通,因為如果是為了防止過路人打棗,那就不能說是“多事”,而且這樣講,也和下句的“卻”字失去了呼應作用,意思無法貫通。
現在,我們接着講這首詩的最後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這兩句是全詩的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個對偶句,但不要看作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由小到大,由近及遠。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進一步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就是廣大人民的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所謂“征求”。這剝削的殘酷,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她窮到隻剩下幾根骨頭。這也就為寡婦的撲棗做了進一步的洗雪。杜甫仿佛在對吳郎說:朋友!如果要追究撲棗的責任的話,那也要由貪官污吏們來承擔,寡婦本人是沒有罪的。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杜甫更進一步地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也就是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夫妻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點醒吳郎、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絕不止寡婦一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也絕不隻是撲棗;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還住着我的草堂嗎?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總是鼠目寸光的,如果能叫他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這樣看來,最後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我們正是要在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态度。
《又呈吳郎》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的律詩中,這首詩更值得我們重視,但這一點可以不多說。這裡要做補充說明的是藝術表現方面的一些特點。首先是,作者采取了擺事實、講道理的手法,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颠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後還用自己的眼淚來感化對方,現身說法,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隻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這些字就是。我們說過,這是一首律詩,律詩有不少清規戒律,比如中間四句就必須作成對偶,很容易流于呆闆。現在因為運用了這些虛字,是以能化呆闆為活潑,使這首詩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此外,措辭的委婉,也值得我們注意。杜甫是草堂的主人,讓不讓寡婦打棗,原可以做得一分主,但是杜甫卻竭力避免以主人自居,隻當吳郎是這棗樹的主人,而自己則不過是替寡婦說說人情,這就更能感動對方了。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閱讀與欣賞》1961年廣播稿,後收入《杜甫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版;《蕭滌非文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蕭滌非杜甫研究全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