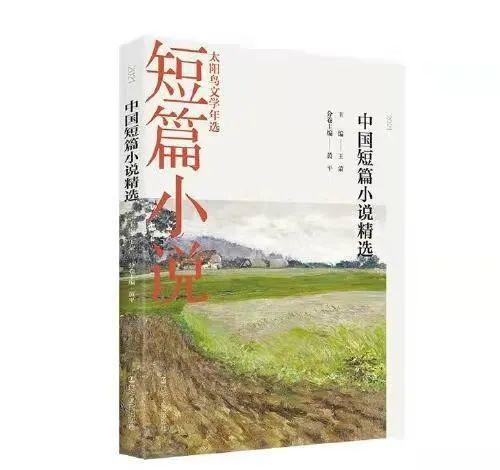
從追憶中突圍:2021年短篇小說觀察
黃平 李曉晴
本文原刊《當代作家評論》2022年第1期
一
當今的我們,在經曆疫情帶來的停頓以後,已然意識到身處一個需要不斷處理記憶與經驗的時代。小說寫作面對的疑難,不再隻是在形式與内容上構造出不同的美學模型,而是如何在一個不再變動不居的世界裡、在日新月異的感官體驗當中緊緊把握住我們的生命。如果說不斷在當下與追憶之間來回切換的意識流,是人類所獨有的精神日常,那麼超越當下,從追憶中突圍便是這一日常的自反,也是文學所必要具有的價值。寫作者一面采用不同的叙述技藝進一步建構自我感受與真實世界之間的關系,一面為防作品在各種經驗的堆積中下沉,而自覺地創造出種種“突圍”方式。
潘向黎
最直接的一種政策是借助單一視角的寫作,塑造出高度風格化的現代獨白,在各個人物對于事件、經曆的追溯中,探讨可能的客觀遮蔽或主觀逃避。比如潘向黎的《荷花姜》,講述日式料理店老闆丁吾雍目睹了兩位顧客的感情由發展至破滅。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已訓示了店主視角的單向特征:“每一次看見那個女人,丁吾雍心裡就有一個聲音響起:應該去報案。”[1]顯然,此刻的丁吾雍仍陷于對“荷花姜”殺害戀人的誤會之中,謎底還未揭開,而真相在握的作者徐徐叙述丁吾雍對這段愛情故事的追憶。情數萬化的都市生活有遺忘,自然也有記憶,明媚而熱烈的女子“荷花姜”便是丁吾雍記憶中的“不可溶晶體”。丁吾雍人如其名地緻力于維持自身與世界之間的微妙和諧。如此地矜于世故,他對自身把控現實的能力高度自信,比如投入核心技術的學習,成為餐廳的主廚,以避免變動可能帶來的困境;為得到窺察客人的友善,他竭力在沉默中讓自己隐入背景,“甚至連每次對坐吧台的客人遞上的微笑都減到半明半滅”[2]。至于旁觀造成的“不得其解”,他甯可不去求解,還暗自認定了他們是婚外戀關系,因為“他相信太陽底下,真的沒有新鮮事”[3]。丁吾雍之是以對“荷花姜”記憶深刻,正如他将其命名為“荷花姜”,是因為她擁有日常所罕見的非常滋味——“模樣嬌豔,味道奇特霸道”[4]。然而這滋味又在他的神遊中,被指認為上海都市女郎的“氣場”,由此不無沖突地揭示了這位廚師對“荷花姜”的偏愛實為一種“現代口味”。隻要人有口味選擇,一件尋常物便可被看作不尋常,正如荷花姜這一草本植物,可以是菜,也可以是花。
是以,當女子絕望地告訴丁吾雍她殺害了自己的夫妻,好比在水中引爆炸藥,無聲而震蕩,“荷花姜”的刺激程度超出了預設:“這麼好看,怎麼可能殺人?”[5]丁吾雍發現自己“過于自信”了,生活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這位女子帶來的體驗遠不止是某種口味的“性感”想象。在這一刻,“荷花姜”突破了審美的邊界:“那一瞬間,丁吾雍感到在她的身後,是一大片空虛。”[6]女子把丁吾雍視作知己顯然是表象造成的錯覺,後者終究隻是一個有品位的男人。在丁吾雍的視野裡,他既不能洞察事件的真相,也無法真正穿透“荷花姜”的内心;他在不安中确認了一直以來搖擺着的、對于平靜生活的理想,而向多年同居的女友求婚。即使“荷花姜”關于殺人的自白因黑衣男人的重新出現而被證明為一句氣話,對内心漂浮的丁吾雍來說,這仍是一場激蕩的白日夢、一次華麗的冒險,猶如一位男性的精神出軌最終草草收場。不管怎樣,他的隐藏在口味背後的不安分——對于危險魅惑的夢幻在這一事件的結尾宣告消亡。《荷花姜》透露的真實是,人們自以為熟悉的日常經驗将在某一次抵達邊界之時爆破,将錯就錯、得過且過的想象掩飾了不可靠的習慣合理性與蠢蠢欲動的好奇心,正如丁吾雍眼中一向氣勢非凡的黑衣男子,隻有在面對前妻時“萎靡裡透出輕松”才“顯得真實”。當事件由震蕩歸于平常,它在人物的内部鑄就了某種終極失落,這一點震蕩的殘餘/日常的溢出使丁吾雍從一種無法得到的口味的追思中突圍,某種程度上平複了他當初放棄到日企闖蕩一番的遺憾,真正在“吾雍”所寓意的從容和諧中達至自我圓滿。
魯敏
同樣采取限制性視角獨白叙述的,還有魯敏的《味甘微苦》。小說在夫妻兩人的視角間來回切換:徐雷認定近來心不在焉的妻子已經出軌,為避免讓兒子重複自己喪母的遭遇,他選擇忍辱負重勉強維持婚姻;另一頭,金文的13萬私房錢在一次詐騙中被全數卷走。參加苦主讨債群的集體行動時,她認識了獨自撫養腦癱女兒雙全的老展,三人發展出“相濡以沫”的情誼。金文從中體驗到家庭生活逐漸喪失的凝合感,漸漸看不得徐雷“那種忍讓的、裝糊塗的樣子”:“每次一浸入到讨債鬧事的情境裡,就覺得她跟老展、雙全、輪椅,是完全一體化的,是整個兒的捆綁,那種徹底的傳遞,倒讓她放松。反而是回到家裡,在徐雷、小雷身邊,三心二意的,人裂成幾瓣,很不舒服。”[7]金文、老展和雙全三人共同的性格、遭遇和目标激發了同一社會階層内部的“親和力”,無數細碎的挫敗組合成一種綿延可感的生活狀況:“這回,算得上是一次特别的重創嗎,也談不上。一直都是屢戰屢敗吧。……她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她的語速像泥石流一樣,帶着災難的氣勢,而泥石流中的笑,可真有點兒硌耳朵。”[8]
無論是徐雷撒網、小雷放風筝,或金文把欲望列成了一張“浮華的小資産階級清單”,他們總有方法營造一種願景,打發自己的生活。好奇的雙全樂于聽金文細陳這13萬是如何在零碎的算法和延遲滿足中逐漸積攢起來,姨娘給自己找起了墓地。生活的泥石流下并非隻是不堪重負,也有别樣的負隅頑抗。另一視角,耽于自傷的徐雷希望金文想起兩人當初在病房相知相戀的記憶,但本來也不是機緣,而是喪失引發的共情使他們結合:“她跟徐雷的最開始,不就因為兩人都剛剛割掉了闌尾嗎。她和老展,所被割掉的,可遠遠不止是那節子無用的小肉腸。人們哪,都會因為失去而共同沉陷吧。”[9]一開始,徐雷的養母姨娘和金文也“确實不親”。退休後她在市區裡閑逛,一次偶然撞見金文帶雙全在廣場讨債,才打破了過去對金文“傲滋滋”的誤解。姨娘不僅沒有追究金文藏私房錢,還“像是突然被啟蒙”,和她們熱烈地讨論起“清單”所羅列的奢侈生活。在故事的結尾,她主動向金文提出想要“入夥”:“加個老太太,效果肯定更加好”[10]。一種奇妙的情感作用力代替血緣,在婆媳之間建立起聯結,甚至比她與養子不生不熟的關系更為親近。正如小說的題目“味甘微苦”,人物們在世俗的疑難中打轉,不能脫身,但這些經曆就像飲中藥一般,略微苦澀卻有回甘。在“當下性”之迫切與“現世性”之追求的交織下,小說結尾在瑣碎的日常描寫中穩穩停住,作者最終沒有消除夫妻兩種視角之間暗含的沖突與隔膜,然而經由姨娘這一中間人的介入、她與金文和老展父女組成的情感共同體,小說完成了雙重視角内在裂縫的“縫合”[11]。
二
記憶遠不止是對過往事物的表象。以動名詞的方式,它“構造”着一切實體經驗的形态,同時也是超越性經驗的真實原點。《荷花姜》《味甘微苦》兩篇小說呈現了現實的程序如何從人物既定的記憶或認知中突圍,借視角的遮蔽來沖破認知表象的遮蔽,描述生活的特定真相。在當今時代,寫作者們要求從表象經驗中突圍,不僅是創作層面對于低層次現實主義的不滿足,對于名牌包、咖啡廳、玻璃大樓等組裝的“都市認同式書寫”的抵觸,更是要從一種淺嘗辄止的碎片化體驗中掙脫出來,在對于過去曆史和當下經驗的追索中穿透隐含的遮蔽,整合出一個完整的自我。自先鋒寫作、新曆史/新寫實主義、“新生代”及青春文學在文學史中逐個消沉以後,文學形式與現實經驗的磨合仍在磕磕絆絆地進行着。當經驗的追憶拒絕下沉為特定意識表象的堆積,它便不是全然無用,相反,它将使我們靠近一種更為原初的意識。如此,追憶作為一種動态的探尋,融入故事的結構,甚至化為結構本身而超脫其外。今年的小說選中,《恍惚概要》《喝湯的聲音》《雪山大士》《海與荒漠之間》不約而同地提及2020年以來在全球爆發的新冠疫情。疫情以前的時間激流中,科技快速發展,引申出未來主義的世界圖景,展現在人工智能、賽博格的熱烈讨論中。寫作者也試圖将既有的曆史與未來叙事接軌,比如,在郝景芳的小說《2050殺人事件》,發祥于美國作家愛倫·坡的偵探小說叙事有趣地依托于未來AI技術的理論推演。但在今天,疫情卻讓人類的時間之流減緩暫停了。這一事件既使得現實從經驗中脫落,在另一層面上又使現實從中突圍,個人的時空感受發生了改變而帶來一種新的反思:“人其實沒自己想象的那麼戀舊,對過去的記憶總會被新發生的事覆寫甚至替換,不管深層裡埋着什麼樣的石頭、礦物,人們都隻看見表面的浮塵和枯葉。那才是人對生活最主要的感覺”[12],同時,它在人與曆史時間之間形成一道阻隔,成為人們面對現實生活乃至整個文明時一種新的參照系。
在遙遠的黑龍江,食客們舉起手中的酒杯時,“五顔六色的口罩有點鳥兒掙脫樊籠的意味,向上沖去”[13]。居于後疫情的時空坐标上,《喝湯的聲音》這個有關烏蘇裡江畔少數民族百年曆史的傳奇故事,被“當下”賦予了别樣奇異的曆史意趣。在“擺渡人”對“我”講述這個傳奇的同時,傳奇裡的哈喇泊和他父輩祖輩也不斷向同時代人講述着這個愛恨交纏的故事。他們以咬碎牙齒的代價,近乎頑固地儲存着這個家族的記憶。直到曆史的航标來到眼前,人們已聽煩了這個故事,就連奶牛聽了他講的故事都将無法産奶。史詩之死是每一曆史階段的必然,同樣,哈喇泊也沒有後人傳承故事,猶如牙齒銘刻一個人的一生,哈喇泊幾代人伴随牙齒之疾的家族史注定是“滿嘴的殘垣斷壁”,是“無後”的曆史廢墟。唯一得到延續的是這個沒有牙齒的族人喝湯的聲音,它化為一種“要把大千世界都收入腹中”的生命力量,被收納到烏蘇裡江的強風、江水之中。而當下“我”的夫妻被山洪卷走,與哈喇泊族人所遭遇的喪失,在這不可擋的生命之流中疊合。唯有“擺渡人”以自然之名傳遞着人類的故事,向正經曆疫情餘震的我們确證:人們的生命、魂靈終究與山河的血脈連成一體,而生命之樹長青。
《雪山大士》呈現了個體對曆史變幻的另一種體認。在著名足球運動員D對于曆史的感覺中,柏林牆倒塌對生活的影響還不如幾年後一場小火災造成的失落來得真實深刻,後者燒光了家中一切與東德記憶相關的物什,包括曾外祖父從中國帶回的佛像。因為這種真誠,D将後來的職業視作一門藝術:相比于快節奏和高強度的現代足球,他甯可優雅從容地踢古典前腰,盡管這種踢法富有觀賞性而無益于勝負。和D享受球與腳的觸感一樣,他的理療師赫爾曼僅憑聽覺就能作診斷,對于内在感受的誠實與敏感使他們彼此欣賞。然而極緻的外在體驗伴随着對生命的同等損耗,D終究難以擺脫職業生涯帶來的情感激蕩,于比賽失利的壓力和重傷後的漫長療養中自暴自棄:“渴望逃離自己,逃離這一塌糊塗的劇本”[14]。在雪山大士像與釋迦摩尼傳說的啟示之下,D一度釋放自我意識,跟随蒼鹭飛出足球賽場的綠色背景,但這一超脫隻不過是某種虛僞的排解,“僅限于諸事不順的時候”[15]。與虛無的第二次纏鬥中,D模仿赫爾曼低下頭傾聽自己的膝蓋,在“積液的湖底”聽見緩緩升起的一聲“唵”,那是嘗遍世間情愛而深陷虛無的釋迦摩尼在自殺前聽到的救贖之聲。
更有意思的是,與第一次宗教式的精神出走相比,“唵”的聲音不源于超驗:“與其說是精神遭遇,不如說是生理體驗”[16]。它來源于D對内在生命的傾聽,來自體内“隻有自己能聽見”的真實聲音。在海德格爾的意義上,它是存在的聲音或絕對的聲音,而非某種語言。[17]D不再将身體的傷痕損耗當作外在秩序所要求的條件和結果,而是自我生命的痕迹。正如《局外人》的默爾索臨死前,回想起家具的每一道劃痕,那是生命的痕迹,是一個人的曆史,不帶有任何功利的懸想。D清空了職業的負累,從持久的外部負累中突圍,回到了原初空白,因而具備了向廣闊未知空間開放的可能:“一切樂趣都是新鮮的,像孩童一樣無知而歡樂”[18]。當他放棄成為一個“演員”,便與其“背景”不再離異,不再時刻面臨自身價值形象堕落的危險。也可以說,D已經是一個沒有“社會背景”的人,正如“我”在故事開頭陳述“沒有一眼認出D來也許是因為背景”:“他惬意地陷在角落的軟椅中,而不像過去我所熟識的那樣,置身于一片翠綠和山呼海嘯間。”[19]
從自然崇高者處追溯生命之源,或蟄伏于内在經驗探尋出路,文學對記憶的超越還在于自反式的想象——從曆史的連續性中浮出,觀看它的流動本身。這是人所獨有的對于記憶最高層次的追索。李宏偉的《神奇五俠》将流動的時間切割開,并剪輯成一篇和諧的宇宙樂章,時間在人生追溯和當下現實、細碎思緒和整體思考之間來回跳躍。當下的他第一次邀請她到宿舍作客并看了一部漫威電影《神奇四俠》,其間叙述不斷穿插與這次經曆有着模糊關聯,卻從屬于他們此後五十八年間生活的片段,當下與曆史在場景的頻繁切換中交彙:“後續的時間段……”“是那兒往後跳至……”“場景連續跳躍至……”[20]在這裡,他和她的過去和未來并非線性發展的關系,而是在浪漫的想象中被立體地結構起來。當“神奇四俠”在一次雲團加速中獲得了各種超能力,她問他想要擁有哪種超能力,他冒出穿梭時間的念頭——僅僅是往時間内裡探看,看看他的未來裡面有沒有她。盡管沉浸于當下的生活,他有時看不清時空的面貌,甚至不小心“忘掉坐在身邊的她”,“把她還原成了可能坐在旁邊的任何人”[21]。但在主人公的想象之中,“宇宙流如此強大,雲團的速度如此之快”[22],時間将映照在他朝向她“綻放”的每一個瞬間(桃花),最終凝成一朵擁有無限層疊空間的紅玫瑰。
《海與荒漠之間》将破碎的現實和詩性的想象結合,從夢境/現實/寓言打開了後疫情世界的整體視野。美國籍主人公在阿富汗戰争中失去了自己的左腿,并且不得不面對這場戰争虛無的終結。随後疫情爆發,主人公裝上假肢艱難地适應着隔離生活,和中東男、俄籍斯拉夫女人烏托邦式地同居在美國北部沿海城市的中心。世界在帝國、戰争和瘟疫種種陰影下運轉,不斷“被喪失”的生活早已支離破碎,主人公重拾漫畫家的夢想,創作了《我的左腿》:在另一個平行世界的荒漠上,左腿、地雷、海星互相和解,結成逃出荒漠的友盟。他們期盼回到南部的大海——在海裡,海星就能長回原來的樣子;在海濱,地雷碎片可以生成鏟子挖土種花;而那條左腿将在主人公夢裡南海的新年舞會上重新變成人。正如海星說,天上的星星擁有各自的海但都已幹涸,“地球也是星星,可是幸運的地球這顆星還有海”[23]。在小說中,“海洋”成為希望所在的應許之地、關于和平的浪漫寓言。人們被驅離水域之後,世界經曆了種種痛楚,是以當主人公從頂樓眺望,城市始終是陌生的,“入海的河流之上橫亘着連成一片的鋼鐵橋梁”[24]。但在腳手架和海水之間,隐藏的不止是結構的欲望和侵占,還有對生命最後的愛意以及突圍的希望。
三
或許可以說,一切追憶的行動都面臨着一系列創傷性遭遇。在小說《跳馬》中,阿毛和福元到蘆葦蕩躲避即将到來的敵人,一派祥和的鄉野風景舒緩了戰争時期的緊張情緒。沿着這樣的節奏,小說圖繪了戰時上海留存于日常生活的民間人情。如果是孫犁、汪曾祺等作家田園牧歌式的戰争書寫,那麼背後總有一個和諧統一的思想信念,而路内的《跳馬》卻暴露了連續的日常情景之下人們内心的破碎,将随性的玩笑或粗話揭示為創傷的後遺。前者日常化的平淡叙述往往自然化地過渡掉不尋常的經驗資訊。故事開端,主人公阿毛的身分不明,隻知道是上海本地人,家人都死了,讨飯時不知怎麼跟定了遊擊隊副隊長;阿毛原本讀過點書,隻是滿嘴髒話,極憎恨日本人;跟福元和芳蕙的兩次對話中,他沒來由地認定日軍轟炸時“甯可跳水裡,不可躲樹林裡”[25],還遭到了福元的嘲笑。與此相關的真相被掩蓋于輕快和諧的牧歌背後,直到後來才被揭開:日軍戰機轟炸上海時,阿毛的家人跟随人群躲進樹林,炸彈引起樹林大火,人們燒成了焦炭。他在橋洞下面逃過一劫,卻目睹了一切。面對戰争的恐怖,阿毛既像大人一樣早熟,也有小孩本來的恐懼。是以小說從不稱阿毛為阿毛,而是反複提醒讀者一般,稱他為“小孩”。正如射擊在和平年代是奧運會上争奪國際榮譽的競技,是日常的體育運動,但在戰争年代卻是殘忍的殺人行徑。原本從事體育教員的大隊長讓阿毛練習跳馬,期盼阿毛将來能得奧運獎牌。對這兩人來說,跳馬與其說是對和平的期許,不如說是同田園生活一體的、浪漫化的自我療愈。通過跳馬,通過田園日常,他們對和平進行演練和預習,而暫時忘卻戰争時期扭曲的人性和創傷記憶,找到當下自我的支撐。最終大隊長還沒能看到阿毛跳過木箱便犧牲了。以田園為表象的詩意叙述,也無法遮蔽戰争當下救贖的無望。
《小野先生》則從抗日戰争的加害者一方印證了救贖的不可能性。曆史學家小野先生在“我”的帶領下參觀僞滿洲國的遺留建築,途中他試圖從牆壁照片中找尋父親的身影,并向“我”講述了他的父親——老小野先生作為一個侵華者充滿負罪感的一生。過去小野先生曾在學校裡被霸淩,父親到場制服了霸淩者,卻不若其他父親那樣責備他的怯懦。侵華時期的屠殺記憶造成父親長久的夢魇,他認為自己和戰友都不配甯靜地死去,是以臨終前“抹掉了他所有的生活痕迹”[26]。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當下僞滿洲國遺址堆滿了迎合旅遊需求而刻意“做舊”的物件,“真”的曆史被消費景觀所掩蓋。抗日戰争的宏大曆史默然退場,唯有“小人物”的創傷經驗變成了活生生的記憶,并被後代隐秘地傳承:“用字詞和叙述把老小野先生清除掉的東西一點一滴地還原回來”,“總好過一片虛空”[27]。小野先生直面與反思曆史的勇氣,不是丁香花下面對歹徒不假思索的肉搏,而是反抗遺忘和虛無的力量。同樣探讨勇氣的話題,董夏青青的《禮堂》寫實地記錄了駐中俄邊境艇隊士兵的集體生活與個人記憶。小說開頭,教導員在驚恐中誤将草甸子當成了死人的頭顱,相比于淡定上前檢視的艇組長,他發現自己“慫了”。反思之餘,他追溯起父親在前線當炮兵的經曆,以此重獲對抗恐懼的能量。因為榮譽軍人進禮堂需要家屬在場觀禮,艇組長一直對争取榮譽不積極,他内心深處埋藏着一段往事:野熊闖進家裡時他抛下母親和妹妹自己跳窗求生,受到母親的譴責,後來當兵是為了改變當地人對他“沒長心”的評價。兩個士兵的講述在追憶和當下間橫跳:即使他們是軍人,面對生活的意志也并非與生俱來。在朝向創傷的反複回歸與對位中,自我不斷地掙紮、解脫和生長。
班宇
不同的是,班宇《緩步》中的主人公拒絕欺騙性地将記憶中的裂縫“縫合”[28]起來,或任何形式上對創傷的自我調解,他甚至不想擁有“自我”:“人一旦有了這種意識,就很可怕,像島嶼上叢生的密林,沙沙生長,不止不歇,直至遮蔽全部的光芒與道路,長久困在噩夢之中。”[29]從小說本身來看,缺乏實體填充的“裂縫”遍布于主人公的生活,叙述是以呈現出殘缺的形态:緩步台“左側如懸崖,下面是無聲的幽暗”[30],居民們拉着簾布的北窗,白色的牆壁,熒光屏裡的海水,在風中飄着的答案,沒有聲音的手語和始終不得要領的手勢,突然脫離小說背景的想象、童話以及其中(如希區柯克的“群鳥”一般充滿非理性敵意的)數萬隻企鵝。它們是實在界之物——來自虛空世界的事物,被作者呈現在不可穿透的界面之上。由于隻有其表面可被捕捉,這些事物深不見底,而無法歸入現實世界的平面當中。主人公緩步在深淵旁,凝視着深淵——這條内在于他和理性世界(“一個科學的、可被計量的體系”)本身的傷痕:“這并不是我們個人情愛之事,無所謂奉獻與虧欠,忠貞與背棄,而是生命本身存有的無可彌合的裂隙,凡途經此者,必然陷落于一種更大的痛苦、神秘與真實。”[31]對這一失落構成喻指的是小林和木木的耳朵,随着器質性的衰變,關于聲音的記憶也逐漸失去。被忘卻的聲音指向現實的終極失落,主人公從“解救者”木木混沌而圓滿的世界汲取能量,在深淵裡長久地浮遊着。
了解一個時空的本質需要無數互相獨立的參照系。通過肉眼,我們隻能觀察宇宙在三維空間下的投影。《緩步》在投影中打開了一個黑暗的“居間次元”[32],其中居住着人類不可控的無意識,以及無數從現實中掉落的創傷結果。在這裡,夢境就是“真實”。正如莊周夢蝶并不導向一個懷疑論的認知程式,而是人在包含着現實與夢幻的“真實”面前如此被動,以至于不能認識它。郭爽《峽谷邊》的開頭作了一個逆反的嘗試。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外科醫生,為了更深地了解亡父陶勇,他憑借自己“可靠的大腦”練習控制夢境,并成功地代入到父親的身體,“還原”出一段記憶。和《盜夢空間》一樣,這一描寫可以說是充滿了技術意味的人類寓言,人物自如地操控和馴服着夢境,并且清晰意識到“邊界”的存在。對于這一行為的僭越性,主人公并非不自知,它被描述為象征界向實在界的反抗:“夢神在懲罰我。我竟然用人類的語言和文字來與之對抗。”[33]但重要的是,《峽谷邊》夢境對記憶的重制,僅僅是追尋關于父親的“真相”的開始。在“我”小時候關于電站的一幅塗鴉裡,父親充當着“龍”的角色,主角卻是“龍”噴出的一個個“三角形,綠色的”的火焰,揭示了父親作為下遊三角洲的“發電者”,被嵌在一個無法掙脫的結構性位置。此外,父親遠在新加坡的好友彭宥年向“我”說明了——“我”從夢境的練習中無法得知的——時代的壓抑與釋放:那是個特殊時期(小說指為1992年),人想的事、做的事,離瘋狂近一點,但反過來說,是生存的本能。不這樣,就會真的瘋狂。[34]彭宥年認為陶勇留守原地,是代他“把一半補上”;相應地,陶勇也感受到另一半的“失落”。或許可以說,這兩半分别是開拓的欲望和本性的純真。即使夢境被理性化,也無法還原一個總體的父親形象,隻能呈現出現實的裂隙,正如“我”不信神,卻被God在計算機的投影震撼了,最終計算機并不能取代God本身。這一追尋的結果是,為了對抗父親而遠赴澳洲的“我”,發現了内在于“我”、作為“我”另一半的父親。
後疫情時代,文學既要負載生活不斷發送給我們的新資訊,還要“被迫地”重新追憶我們的曆史,回應我們對了解時空與自我關系的需求和問題。以上的小說給出了各不相同的答案,它們在回溯的結構中暴露出關于“真實”的不同面貌,尤其突出了叙述對時空秩序的多重整合,這種整合并非逃離曆史的連續性,而是讓“真實”在虛構中得以回歸,展現出經驗的多重次元。
本文系《2021中國中篇小說精選》(遼甯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序言
作者簡介
THE WRITER
黃平,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李曉晴,1997年生于廣州,大學畢業于中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22級博士研究所學生(碩博連讀)。
注釋:
▲上下滑動檢視注釋
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歡迎分享到朋友圈
評論功能現已開啟
(公衆号編輯:華東師大中文系 何卓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