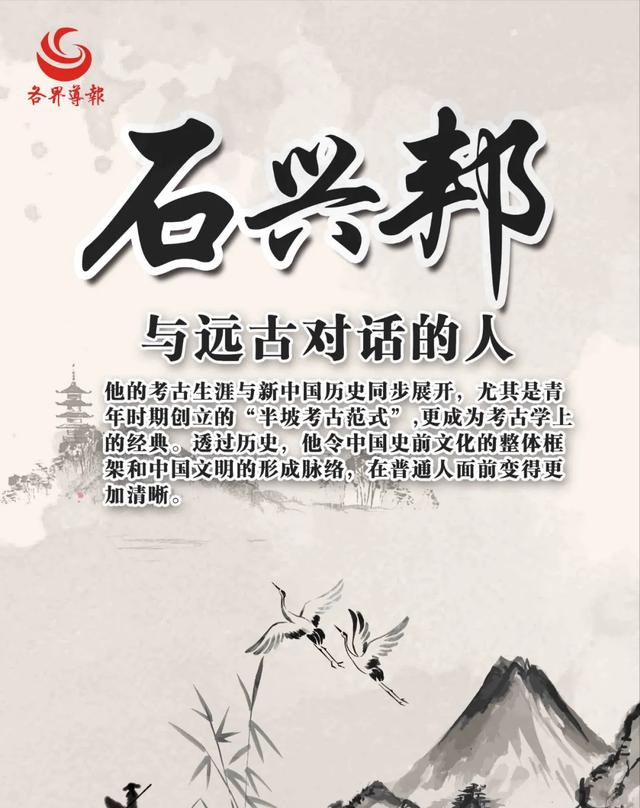
石興邦,陝西省耀縣人,考古學家,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陝西省考古學會會長,先後主持了河南、陝西、北京、山西等地多項重大考古發掘工作。在媒體公布的“20世紀中國百項考古大發現”中,石興邦主持的就有兩項。他的考古生涯與新中國曆史同步展開,尤其是青年時期創立的“半坡考古範式”,更成為考古學上的經典。透過曆史,他令中國史前文化的整體架構和中國文明的形成脈絡,在普通人面前變得更加清晰。
半坡遺址、兵馬俑、下川遺址、法門寺地宮……這些舉世聞名的曆史遺存世人皆知,但讓這些遺存重制天日、驚豔亮相的幕後英雄,知道的人卻不多。在西安這座“考古之都”坐鎮一甲子的石興邦先生,正是這些幕後英雄中的領軍人物。2018年第二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石興邦榮膺“終身成就獎”,這是對他一生緻力于田野考古的充分肯定與褒獎。如今,即将迎來百歲壽辰的石興邦老人,已然成為考古界的一座豐碑、一個傳奇……
歪打正着,一頭紮進考古領域
1923年石興邦出生于陝西耀縣石柱鄉。耀縣是關中通向陝北的天然門戶,素有“北山鎖鑰”“關輔襟喉”之美譽,而當地深厚的文化底蘊,也為他的成長成才提供了豐富滋養。石興邦家屬于富裕中農,養着上百頭綿羊,從小他就會放羊、擀氈和耕種。石興邦國小時上課是在鄉村的一個大廟裡,當時有一個叫寇懷義的老師,白天授課要求很嚴格,晚上和石興邦住在一起,向他傳授新思想,給他講了很多新鮮有趣的事情。在寇老師的督導下,石興邦還認真練習了書法,打下了厚實的功底。
1937年,石興邦就讀于西安一中,他隻在課堂裡度過了半年平靜的時光,就遭遇了全民族抗戰的爆發,日軍開始對西安狂轟濫炸,學校被迫搬遷至漢南,他轉學到了三原中學,學習生活也變得艱苦起來。不過不長時間,山西大學就搬遷過來,一些很有學問的教授、副教授主動為中學生講授課程,這讓他學到了地理、生物等多個學科的知識,成績也随之提高。1944年高中畢業時,他參加陝西省會考,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
石興邦一共填報了兩個大學志願,一個是當時位于重慶的中央大學政治系,另一個是新疆學院的民族系。原來,他從小就對班超定西域、張骞通西域的故事很感興趣,想通過大學的學習來增加對邊疆、對少數民族的認識了解。恰巧在那一年,國民黨政府對于蘇聯在新疆的活動十分忌憚,在中央大學新設邊政系,想借此培養一批精通少數民族語言,能夠安定邊疆的人才。招生老師看到石興邦的志願後,就将他調劑到邊政系。
石興邦
俗話說,歪打正着。正是在邊政系學習到的人類學、民族學、古代史、原始社會、村民社會、考古等課程,以及邊疆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等,讓石興邦對遠古文化有了系統的認識了解,在頭腦中建構起完整的知識架構,這些在他轉入考古工作後都發揮了極大作用。
韓儒林是元史權威,在他的熏陶下,石興邦對蒙古的曆史、文化、語言興趣大增。韓儒林治學嚴謹,授課注重點評啟發,然後列出需要參考的一大批資料,讓學生們在研究思考中不斷深化認識。蒙古史第一次期中考試,石興邦隻考了62分,居然是同學中唯一一個合格的。原來,韓老師出的大多數是參考書目中的題目,石興邦平時看書比較多,還算有些積累,其他人看得少,是以都無法及格。畢業那年,石興邦還和同學們一起翻譯了《蒙古秘史》。
因為學業基礎較好,石興邦留在中央大學擔任助教。他原本想着跟韓儒林先生讀研究所學生,但不巧的是邊政系被取消,相關教學資料都被移交出去了,韓老師也轉到了曆史系當主任。1949年,這一年隻有浙江大學還在招錄研究所學生,石興邦于是報考了浙大人類學專業,考場就設在導師吳定良教授家的客廳,連續考了3個半天。考試的形式也很簡單,吳老師從書架上随手抽下一本書,讓他就文中觀點進行評述,或者讓他翻譯外文書籍。當時他送出的論文還是别的老師臨時“支援”的。好在石興邦大學時經常參加社團活動,與吳老師關系還比較熟悉,幸運地被錄取了。
讀研期間,石興邦還向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學習考古方面的知識,随之參與了杭州玉泉山晉墓的發掘,這也成為他的首次田野實習。1950年,夏鼐被請到剛成立不久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了副所長,石興邦也跟随前往,擔任學術秘書。除了考古專業以外,他還學習了俄文版、英文版馬列主義著作,強化了曆史觀的培養塑造。由此,石興邦也漸漸成為新中國考古史上一個切身體驗者和重要開創者。
一次普通的田野實習,意外揭開“半坡”神秘面紗”
作為“十三朝古都”,西安有着豐富的曆史資源和文化積澱,向來是考古發掘的要地。1953年,石興邦與陝西考古調查發掘團進行合作,在西安東郊國棉三廠福利區的工地上進行“尋寶”。一天下午,他走累了,就找了個土坎坐下休息,無意中發現河對面地勢較低的土梁上有一道很整齊的斷崖,這一下子就激發了他的職業敏感。走近一看,取過土的斷茬上已經露出很多遺迹,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他用鎬頭敲了敲,還發現了不少整齊的石片,目測帶有石器時期的典型特征。刹那間,石興邦的内心激動不已,先民們用陶器和石器進行勞作的畫面,一下子生動地浮現在眼前。回到考古研究所後,他馬上向所裡打了報告。
但真正發掘這處遺迹,卻是在一年之後。當時各地建設如火如荼,不少工地都挖出了墓葬、遺址,但因為常年戰亂,考古方面的人才極為匮乏,人員還不足夠調遣使用。為此,中國科學院與文化部、北京大學聯合舉辦考古人員訓練班,每期3個月時間,使他們能夠快速入門,補充到一線考古崗位。為他們授課的是郭沫若、翦伯贊、夏鼐等名家大師,這在考古界也算是空前絕後的。這個教育訓練班先後組織了四期,被人形象地稱為“黃埔四期”。
在石興邦的大力倡導下,1954年舉行的第三期教育訓練班,被安排赴西安半坡村進行田野實習,由他擔任總輔導。誰也不曾料想,這次實習發掘開展不過幾天時間,居然揭開了一個人類6000年前的實地生活場景,這就是震動中外的“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
半坡遺址發掘領隊石興邦先生
在此之前,大陸的考古發掘主要按照蘇聯範式,多采用打探溝、切條分割的方法,把文物器物取走了事。當年不過31歲的石興邦,經過慎重思考,提出了一種全新的考古範式——為保留遺址的完整性、曆史性,先進行全方位的探測,并以層位、層次向下發掘,等到對遺址有了充分認識後,再決定下一步的發掘計劃。
石興邦帶着學生們,通過這種方法發掘出一座儲存完整的倒塌的圓形房子和一座大長方型房子的殘迹,發掘出的其他房屋建築遺迹,也都迹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這是中國考古史上首次有這樣的發現,引起了極大轟動。教育訓練班結業時,北京文物考古界的上司同志都來了,對石興邦的探索給予了充分肯定,鼓勵他一定能取得更多發現。
半坡村的發掘維持了3年時間,期間還換了好幾批實習學生。整個遺址面積約5萬平方米,發掘1萬平方米,呈現出一個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遺址。經過鑒定,這裡被确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在這裡出土的人面魚紋盆被載入中學曆史書,為全國人民所熟知。其實,這種盆是放置在孩子的甕棺上面的,寄托着父母對于夭折孩子的哀思,盆的内部繪有一個眼睛,被認為是靈魂出竅、通往天堂的通道。
發掘半坡遺址1号大房屋
石興邦記憶深刻的還有一罐小米,當打開罐子時,幾乎所有人都啧啧稱奇,原來6000年前的小米和現在的幾乎一模一樣,隻不過因為時間的流逝,小米隻剩下了空空的殼子,稍微有些風,就會飄舞起來。這份寶貴的小米,成為研究史前人類生活的寶貴實物資料。
而他更引以為豪的,則是在考古史上的又一次創舉——進行開放式發掘,允許當地百姓,尤其是村民入場參觀,因陋就簡地組織起臨時性的文物展覽,将史前人類的物質創造和生活場景一一展現在人們面前。當大家參觀時,考古隊員就充當義務講解員,通過繪聲繪色的講解,提高了村民們的文化普及與文物保護意識。自此,不斷有市民提着家裡挖出來的“寶貝”來考古隊報到,而令他們感到心滿意足的唯一獎賞,有時不過是一張照片或證書,有時甚至是來自考古專家和有關部門的口頭表揚。
一天,一位大娘交來了一個尖底陶瓶,其實她也搞不清楚這個都沒辦法放穩的陶瓶是幹什麼用的,隻是想着考古隊員有文化,交給他們準沒錯。石興邦他們經過研究發現,這是一個取水瓶,用繩子挂在脖子上,到河邊取水時,尖底很容易在水裡翻轉,一下子就能打上水。當地村民叫這種陶瓶為“美人瓶”,但有些村民從墓中挖出來以後,認為不吉利,随手扔在了廁所旁邊的地方,或者幹脆就地打碎。每每聽到這樣的消息,石興邦都會極為惋惜。
石興邦曆來主張,考古學家決不能不分五谷、不問世事,如某些人所誤解的那樣埋頭“挖泥娃娃”,而是要成為有擔當意識和協調能力的“社會活動家”。正是廣大群眾的“現場”參與感,讓半坡村的文物發掘和保護變得更加厚實,為深化仰韶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半坡遺址的發掘,是新中國考古史上一座重要的裡程碑,它不僅深化了人們對仰韶文化的研究,還為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全新的範式,更是開創了全景式聚落考古的類型,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而立之年的石興邦,也伴随着半坡遺址的出土發掘,一時間聲名鵲起。
發掘“下川遺址”,考古生涯有苦有樂
結束半坡村的發掘工作後,石興邦一度回到陝西任職,先後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博物館、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直到1976年才重返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院。不久後,他開始了山西沁水下川遺址的發掘,這也成為他考古生涯中又一座裡程碑。
下川村是典型的舊石器時期的遺存,文物十分豐富。由于特殊的曆史年代,跟随石興邦進行挖掘的大多不是專業的考古人員,而是由各行各業人士組成的“訓練班”,有的甚至連考古發掘是什麼、到底該怎麼做都不知道。那時的石興邦,身穿一套褪色的中山裝,腳穿圓口布鞋,走起路來身體微向前傾,面帶微笑,讓人感覺和藹可親。但在工作中,他卻是極為嚴格的,先從基礎知識教起,再帶大家到野外實習,像老師傅帶徒弟那樣,手把手教大家考古挖掘的方法。
在整整4年時間裡,石興邦最初住在一戶老鄉的耳房内,後來住在老鄉放置糧食、農具及雜物的樓上。當時下川條件還比較艱苦,偶爾會用柴油機發電,大部分時間是靠着點煤油燈來照明的。在這裡,石興邦過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房間内隻有一張簡單的床,一張表面凹凸不平的桌子,一個腿不穩的小方凳和一盞幽暗的煤油燈,即使這樣,他每天堅持看書學習,寫心得、寫記錄。在他的帶動下,參訓學員們晚上都不閑着,自學講義、傳抄筆記,掀起了空前的學習熱潮。
也許是出于職業敏感,石興邦對于接觸到的一切東西,哪怕是農民紮起的窩棚、圍起的豬圈羊圈、編制的有本地特色的竹籃子,都要一一照相、留存資料。有學生好奇問他,這些東西随處可見,到底有什麼記錄的價值?他說,恰恰是這種日常記錄的整理很重要,日積月累,必有大用。
仰韶文化 人面魚紋彩陶盆 國家博物館藏
石興邦還帶着學員們參加了當地村民的麥收,讓大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知識分子應當更多參與勞動、經受鍛煉。勞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看運氣是不是好到能夠發現從土裡新翻出來的“寶貝”。一次,他們在老鄉地裡發現了一件砂岩石闆,石興邦就以此為教材,手把手教會大家如何識别文物,以及這類器具的發展曆程和主要功能。學員們圍在他旁邊,饒有興緻地聽着。
考古工作大部分時間既要求細緻又單調枯燥,一些學員有時難以忍受這種經年累月的機械工作。每隔一段時間,石興邦就會帶大家去遺址附近的村莊,上山摘松子、撿木耳、采野果,既能換換腦筋,又能改善夥食。美麗的自然風光,讓單調的工作生活得到了調節,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很多學員對“八一”建軍節刻骨銘心,當時考古隊的生活很艱苦,為了慶祝建軍節,他們特地派車到長治買肉。回來的路上,到了沁水縣城就下起了大雨,汽車上不了山。當時天氣很熱,幾天下來,肉就有些變味,隻能在縣城煮熟,但是已經沒有什麼油水了。等到了發掘地以後,蒸出的包子連林場的狗都不吃。一些學員期盼落空,難免會有怨言。對此,石興邦帶頭拿了兩個包子,并吃得津津有味。很多人看石興邦都吃了,也不好再說什麼,跟着他一起吃完了自己的包子。
下川遺址的發掘持續了4年時間,有人形象地稱之為“下川大學”。很多學員表示,在考古現場得到的鍛煉極大,取得的進步也極大。除了專業知識,大家也更多地從石老師身上學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此後,石興邦用了近30年時間來對下川村的文物和遺迹作進一步的深化研究,接連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意外發現”的法門寺地宮,其實也在意料之中
1987年,石興邦主持發掘法門寺地宮,這是他的又一個代表作。雖然有些人用“意外發現”“運氣真好”來形容地宮佛指舍利的重見天日,石興邦卻說,用“意料之中”才更能代表考古工作的意義。
1981年夏,法門寺的寶塔轟然倒塌。因這所寺廟弘盛于唐代,聲名遠播,國内外佛教界紛紛提出要重修寶塔。為了配合寶塔重建工程,當時擔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的石興邦,從1987年2月開始,帶領一個考古隊對塔基和外圍進行發掘清理,結果意外地在塔基正中部位發現了唐懿宗時修建的一個漢白玉質地的藻井蓋。當掀起井蓋一角僅幾秒鐘,裡面露出的數不盡的金銀珠寶就讓大家大受震撼。相關情況上報後,上級十分重視,安排警衛進行保護,調派專家進行支援。
按照曆史記錄,法門寺建有地宮,内藏有佛指舍利。但地宮的入口到底在哪兒,誰也搞不清楚。石興邦與擔任副領隊的韓偉商議,文物不可能通過藻井放入地宮,應該還有其他出口。于是,考古隊員們在附近展開地毯式搜尋,3天後在羅漢殿的北側發現宮口。宮口北面有一段踏步漫道,沿着19級台階下去,是一個方形的平台,上面散置着近萬枚銅錢。清理完平台後,用巨石封堵的地宮門露出一角。石興邦通過浮雕雙鳳門門楣石,斷定地宮是唐朝修建的,這讓大家感到異常歡欣鼓舞。
考古隊運用工程器械吊走巨石,這才發現石門上鎖着一道35厘米長的鐵鎖。經過細緻地探測得知,整座地宮共有4座石門,按照“30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和”的規矩,鑰匙由不同的高僧掌管,每次開地宮都是一時盛事。但這已經過去1000多年,顯然已經無法找到鑰匙了。好在考古隊中人才濟濟,一名隊員在不損壞宮門的前提下想方設法打開了鎖。
這一天,是1987年4月10日,石興邦帶領考古隊進入地宮,一個金碧輝煌的地下宮殿,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盡管已經過去了許多年,但是石興邦每次與人談起發掘地宮的盛況時,還是會興奮得手舞足蹈。
地宮分為前殿、中殿和後室三大部分,裡面收藏的文物古迹數不勝數。大家把寶貝一件件往外清理、移動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幹勁十足,時常通宵加班也毫無怨言。後經統計,共計發掘金銀器121件、琉璃器20件、瓷器17件、珠寶等400件、雜器19項,所有的銅錢統計下來大約是3萬多枚,還有差不多700多件絲綢。儲存如此完好、藏品如此豐富的地宮,這在唐代文物遺迹考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這次發掘還有一個重大發現,那就是讓世人目睹了此前隻在經書和傳說中才有的佛指舍利,而且一下就出土4枚。按照文物分級規定,其他出土的文物都是以1、2、3共三個等級來分類,唯有舍利被編為“特1”至“特4”,因為大家一緻認為不這麼做的話,不足以展現其巨大的價值。
法門寺地宮的發掘,不僅是大陸唐代考古的重大發現,也是佛教界的一大盛事。唐代曾經有4座寺廟安放佛指舍利,隻有法門寺經曆千年風霜,一直留存至今,接受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源源不斷地前來瞻仰。
“糾偏”兵馬俑發掘,考古是件精細活兒
石興邦長期在陝西任職,與西安的著名遺迹兵馬俑有很多工作交集,這其中既有盡心盡力保護文物帶來的成就感,也有因特殊的曆史條件造成的永遠遺憾。
1974年,位于臨潼骊山腳下的西楊村村民楊志發抗旱打井時,無意中發現了規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由此揭開了兵馬俑為期數十年的漫長考古發掘曆程。一開始派去發掘的考古隊并不内行,居然用涼水澆、熱水燙的方法讓陶俑變得清潔,還調用翻鬥車等大型工具進行挖掘,就連一些新聞媒體都看出了其中的問題,稱其為“刨洋芋式考古”。1979年,夏鼐帶領國家考古所的專家來現場考察,被這種野蠻的發掘方式震驚了,回去後聯系其他考古專家,聯名向上寫了報告,果斷予以叫停。1984年,石興邦被指派回到西安,代表國家文物局專門指導填埋、清理和後續發掘的工作。
兵馬俑彩繪殘留
石興邦先用了半年多時間,指導考古隊對已經挖完的坑道進行回填,對于填埋不夠細緻的還要組織返工。其後,他才開始組織新的發掘。大家自覺摒棄大型機械裝備,主要靠着雙手,用小刷子、小鏟子耐心細緻地清理陶俑,盡力予以保護。但是當時技術條件有限,一些陶俑剛出土時顔色還很鮮亮,遇風後不長時間就會褪色,變成了現在的黑灰色。石興邦感到,如果用現在的科技手段,一定能夠讓“彩色”的兵馬俑長久儲存下去,也能夠讓觀衆看到最佳的視覺效果。
他們邊進行發掘,邊開展科學研究,把諸如秦“車兵”和“步兵”這種不同兵種協同作戰、古今兼有的指揮系統等類似的軍事學術問題,十厘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特别是“雙車編組”這個“有前有後”的關系,更是增進了人們的新認識。通過這些兵馬俑,“地下軍團”的戰鬥盛況變得栩栩如生起來。
在發掘期間,還發生了一起離奇的“将軍俑頭被盜”事件。原來,考古隊雇傭了一個叫簡七一的臨時工,負責看管倉庫器材。他結識了一個叫王更地的人,就約他到考古發掘現場來參觀遊玩。不曾想,這個王更地打起了陶俑的主意,趁着夜色潛入庫房,偷走了極為珍貴的将軍俑頭。要知道,當時發掘了那麼多兵馬俑,将軍俑頭一共才有6個。
案件驚動了高層,公安機關迅速展開了偵破工作。後來,王更地被抓捕,五花大綁地穿過鬧市區,震懾了那些文物盜竊走私分子。考古隊也展開了責任調查,一大批人受到處理,石興邦因負上司責任也做了深刻檢讨。
從1984年擔任陝西考古研究院院長以來,石興邦深耕三秦大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包括在銅川、綏德、漢陰等地建立考古工作站,主持一系列重要的文物發掘工作,在諸多領域實作了重要突破。有人形象地說,石興邦與西安,在考古方面實作了完美的互相成就。
乾陵考古成遺憾,探索更有後來人
與石興邦其他成就毫無争議、頗受贊揚不同,他堅持開掘乾陵的主張,卻在考古界引起了較大争議,贊成和反對的聲音旗鼓相當,這也讓他的這一心願始終沒有機會得以實作。
乾陵位于陝西省鹹陽市乾縣的梁山上,為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墓。這是唐代“依山為陵”紀念性建築工程的傑作,更是漫長封建曆史上唯一的夫妻皇帝墓,還是已經發現的陵寝中唯一一個設有雙重城垣的。加之,陵墓各項防護舉措十分嚴密精巧,可以預測墓葬至今都保持完整,一旦發掘,極有可能是又一個震驚世界的發現。
民間傳說,唐朝末年黃巢動用40萬大軍打算盜掘乾陵,費盡力氣挖出一條40餘米深的大溝,也沒找到墓道口,隻好悻然作罷。至今在梁山主峰西側仍有一條深溝,被稱為“黃巢溝”。石興邦和其他考古學家多次呼籲,還聯合拟定了“乾陵開發計劃”,指出目前乾陵已經處于損壞之中,應當進行保護性開挖,使之得到有效的保護。
然而,也有一些考古學家提出,目前在文物保護方面的技術條件還有欠缺,一旦貿然開掘乾陵,大量出土文物反而可能因接觸空氣而發生病變,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這樣的遺憾,在考古界經常發生。是以,應當給子孫後代适當留下點财富,讓他們在更好的條件下進行發掘。對于這種觀點,石興邦無奈地感慨道:“我這輩子等不到了,隻能看後人的了!”
石興邦長期從事考古發掘工作,手把手帶出了很多徒弟,其中不少人成為了當今考古界的名家大師。王仁湘是石興邦帶出的碩士研究所學生,讀研期間跟着恩師走南闖北,先後發掘出諸多曆史遺迹,也吃過不少苦頭。後來,王仁湘不但跟着石興邦一起研究史前考古,還把自己對飲食的興趣帶入工作,别出心裁地開展飲食文化考古研究,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有很大的知名度,也算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年輕人是考古的未來和希望。石興邦寄語年輕人要有堅持到底的恒心,做好吃苦耐勞的心理準備,學好唯物史觀,同時還要練就世界眼光、全人類眼光。沿着大師指引的路徑,未來必将有更多的年輕人活躍在田野之上,用一個個特别的發現與遠古對話、讓文明接續。
來源:各界雜志2022年第1期
作者:李祝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