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中原文化研究》雜志社賜稿
原文載《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引用時請注明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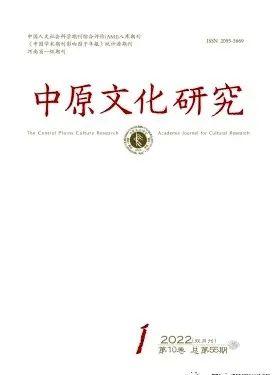
宋代墓志所見女性割股療親現象探究
文丨焦傑、李薇
作者簡介:
焦傑,女,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性别史和文化史研究。李薇,女,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所學生。
摘 要:宋代墓志中有不少女性割股療親現象的記載,有的是女事父母,有的是婦事舅姑,有的是妻事夫,也有個别是婢女事主等。受到當時社會文化環境、家庭氛圍和心理因素等方面的影響,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現象較之前代有所激增,成為治療疾病與孝心表達兩者合一的表現方式。宋代墓志書寫多強調割股療親給個人、家庭和社會帶來的效應,而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幾乎毫無關照。盡管宋代女性的割股療親行為表現出很強的主觀能動性,但其本質依然是對父權文化認同的一種實踐。
關鍵詞:宋代墓志;割股療親;形象書寫;身份認同
割股療親行為在正史中的記載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不過數量較少。到了唐代,割股療親的現象有所增加,但見于傳世文獻記載的都是男性,女性的相關記載幾乎沒有。到了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現象較之前代有所激增,并對後世女性孝行觀産生重要影響。然而關于女性割股療親現象的研究,學界的關注點主要在明清時期,對宋代時期着墨較少①。本文拟從墓志的記載入手,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讨,抛磚引玉,借以引起婦女史學界的重視。
一、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現象
割股療親指的是割掉大腿上的肉作為藥引入藥,用以治療生病親人的行為。這種行為的産生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孝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随着“百善孝當先”觀念的普及,割股療親在宋元以後漸漸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宋代之前,實施割股療親的人主要是男性,女性雖有,但數量極少,目前僅見一例。《唐會稽郡夏氏夫人墓志銘并序》載道:
大孝因心,挺然操志,兩持霜刃,割左右股,奉膳二親,上天降祐,疾皆平愈。州縣聳觀,鄉闾仰止,褒賜累加,蠲免徭役。夫人以禮敬奉上,克修嚴祀,六親緝睦,琴瑟諧和,閨門積善,增業家肥。[1]867
會稽郡夏氏天生仁孝,嫁入夫家後,公公婆婆得了重病,她先後兩次割股入藥來救治雙親。夏氏的孝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不僅親人的疾病得到了康複,還成為被褒獎的對象,獲得了良好聲譽。據2016年以前各種公開出版的墓志著錄圖書不完全統計,唐代女性為志主的墓志至少有4932方,加上合志和附載墓志總計有9574方②,但記載女性割股療親行為隻有這一方,顯然這種現象在唐代女性中是不多見的。
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現象很多,僅墓志記載所見至少有27例。下面根據割股者的身份及其救治對象,将其事迹分類清單如下:
從上表來看,婦割股療舅姑類型最多,有12例,約占總數的44.4%;其次是女割股療父母類型,有11例,約占40.7%;妻割股療夫類型和其他特殊情況各有2例,約各占總數的7.4%。可見,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的對象主要是舅姑,其次是父母,顯然宋代女性割股療親行為受傳統孝道觀念和出嫁從夫婚姻制度的雙重制約。
女嫁為歸是先秦宗法制社會以來的傳統,婚姻六禮的實施和親迎、共牢、說纓與見舅姑及舅姑飨婦等儀式,使得女性歸屬完成了從本家到夫家的轉移,并實作了女性身份由女到婦的轉變,“成為丈夫家的一員,實作了‘歸’家的目的”[2]44。受出嫁為歸家觀念和出嫁從夫的禮教熏陶,大多數女性在嫁入夫家以後,不僅努力做一名賢妻良母,也努力侍奉舅姑如同侍奉父母。如果舅姑患病,她們會努力救治,有些人甚至以“割股療親”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孝心。趙仲轼妻劉氏十六歲嫁入趙家,平時侍奉舅姑“夙夜不懈”,其舅久病未愈,劉氏乃“刲股肉,為粥以進”。孟忠厚妻王氏知書達禮,“既嫁,事尊章尤能緻其孝”。她的婆婆生病了,屢次延請名醫救治都未能好轉,她于是“針臂血投湯液中以進”,婆婆一飲即愈。宋代女性多有信奉佛教者,她們有時也會采用自殘的方式向神明祈禱,請求神明保佑自己患病的舅姑。如趙士铙的母親病重,其妻李氏盡心照料,不但親自侍奉湯藥,而且“灼臂祈請”神明。結果,數日之後趙母的病便痊愈了。
女性割股以療父母的墓志有11方,其中有9方記載割股者都是尚未出嫁的在室女。徐佖病時,他的“室中二女”為其刲股肉;方天骥妻潘氏在室時“清貞淑謹,父疾革,嘗刲股以療之,孝感神明”;程澥妻譚氏未出嫁之前,曾經分别為患病的父母兩次刲股;鐘子度妻吳氏墓志記載她為其母剔股的孝行也是在未嫁之前;李旦之女十三歲那年,“所親病,日夜号泣,齋素持誦,燃臂懇祈”;趙必願妻湯宜人也是在室時為其母刲股刲肝入藥療疾;劉克莊妹與陳寬之妻的墓志雖未有“在室”“未嫁”的字眼,但根據志文的描述,她們割股療疾的行為都是發生在結婚嫁人之前。隻有舒邦佐女、趙公彥妻的墓志無法确定她們為父母割股時是否仍為在室女。
割股療親本是孝文化發展到極緻的産物,對女性來說,未嫁時孝的對象是父母,出嫁之後孝的對象變成了舅姑。但在宋代,女性割股救治的對象中居然也包括丈夫,而且僅墓志所載便不止一例。如晏昙得了重病,其妻李夫人不但向神靈虔誠禱告祈求丈夫病愈,并且“刲股肉羞為藥以進”。趙仲伋久病不愈,他的夫人傾盡所有,先後為其求醫、“祈祝禱祠”皆不見效,于是“自毀膚發”,但最終并未将丈夫救治下來。從孝道觀念來講,女性割股療夫的行為似乎有違常情。然而,傳統社會中的女子未嫁時以父為天,出嫁後則以夫為天,“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3]350,是以當“天”遭遇不測時,妻子有責任和義務像侍奉父母一樣來侍奉丈夫,割股療夫便成為合情合禮的行為。
其他類型的兩方墓志内容并不相同。趙嗣德母親的墓志中未明确說明她與救治者的關系,不過從行文中可以肯定在“親”的範疇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另一方墓志《宋故夫人席氏墓志銘》,講的是魏宜妻席氏對下人有恩,下人都很感激。席夫人生了病,有一個女仆便為她“刺骨肉”以報恩。這種超出了父母、夫妻親情的割股療親行為雖然較少,但也反映了一種新的發展趨勢,這無疑與宋代理學的忠君觀念有關。經學至宋代發展為理學,孔子的“正名”思想被進一步強化,理學家們不遺餘力地宣揚“三綱五常”,“忠君”成為核心内容。宋人石介就主張“為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4]卷14,160。程颢、程頤也大力提倡“事上之道莫若忠”[5]卷25,325等。君臣關系延伸到主仆關系,忠便是仆事主的大義。宋代墓志所載妾室、仆人對嫡室的付出,實則是公共領域“忠君”思想在私人領域的縮影。
二、宋代女性割股療親原因探析
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的行為,與她們所處的時代背景、社會階層和生活環境密切相關,這些因素都對她們的心理和行為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時代文化的影響
孝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自東漢以來,封建統治者便宣揚以孝治天下,而宋代是文治社會,士大夫階層壯大,理學開始盛行,儒家士大夫們對孝文化更加推崇。随着封建士大夫收族運動的發展,民間撰寫家訓、家禮、族規、鄉約等風氣興盛,宋代士人多著家訓或通過書信、詩詞闡述自己的治家理念與倫理道德觀念,其中孝觀念是他們宣揚的核心,墓志中自然也要展現出“孝”的社會特性。
割股療親作為一種孝行,早在唐代便得到政府的關注,并給予鼓勵和表彰。到了宋代,孝作為取士的一個重要标準,造就了割股療親現象的激增。蘇轼在《議學校貢舉狀》中提到:“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6]卷25,724政策層面的刺激促使割股療親行為不斷蔓延,漸漸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在“夫孝者百行之本也,女而孝于母,婦而孝于姑,其本立矣”[7]卷7013,264的社會大背景中,宋代女性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履行孝文化的要求,在室時孝敬父母,出嫁後孝敬公婆,即使是以毀傷自己的身體為代價,也要踐行孝道。
除了以孝取士之外,宋代政府也大力旌表孝行,對女性孝行出衆者,或賜予命婦封号,或賞賜财物、蠲免租稅等,希望借此在社會中形成“孝”的風尚,以實作宋王朝孝治天下的思想。如揭夫人黃氏未笄而能割股救親的行為得到了真德秀的贊揚,并命人在其居所前立牌坊,扁額題字“懿孝”,以示嘉獎。除了官方表彰之外,社會輿論對女性割股療親的行為也都贊譽有加。趙仲轼的妻子是宗室女性,其割股的孝行被大家知曉,“諸宮稱其孝”;陳寬之妻王夫人剔股肉救母的事迹傳開,“聞者嘉其孝焉”;孟忠厚妻王夫人的孝行被廣為傳揚,“至今内外屬人歎譽以為口實”;劉克莊的妹妹割股療親事迹傳開,“裡人皆稱其為孝女”,等等。社會大衆對女性孝行的褒獎、贊揚,使割股療親行為成為表達至孝的一種方式,促使着越來越多的女性效仿。
(二)家庭環境的影響
上表所列割股療親的女性共27位,其中12位女性有命婦的封号,她們是仁壽縣君、普甯郡君、碩人張氏、郭安人、秦國夫人、吳氏孺人、湯氏宜人等。《宋史·職官志》曰:“外内命婦之号十有四:曰大長公主,曰長公主,曰公主,曰郡主,曰縣主,曰國夫人,曰郡夫人,曰淑人,曰碩人,曰令人,曰恭人,曰宜人,曰安人,曰孺人。”[8]3837除宗室女外,國夫人以下封号的授予通常依據“夫貴妻榮”或“母以子貴”原則,也就是說隻有丈夫或子孫的品級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們的母妻才有可能獲得這些封号。毫無疑問,這12位婦女都是官宦家眷。其餘女性雖然沒有封号,但是根據志文的描述,她們或是出身于仕宦家庭,或是出身于地方鄉賢、處士之家,均屬于宋代社會的中上層女性。
宋代中上層女性在室時會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孝道是她們學習的重要内容,無論是班昭的《女誡》,還是唐代鄭氏的《女孝經》,或是宋若莘姐妹的《女論語》,都特别強調孝。如《進女孝經表》曰:“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9]卷945,9817據墓志的記載,這些宋代女性大多有孝的特質。如陳寬之妻王夫人“天性孝慈”;李旦女“生而秀麗,幼而聰敏,長而孝敬”;揭啟宗夫人黃氏“生有至性”;劉克莊妹“亦有至性,異于諸兒”,等等。這些記載雖有誇大之處,但亦可說明她們從小就接受孝道思想的教育,在幼年時期就養成了孝敬父母的優良品質。
自幼培養的特質,對她們成年以後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響。在室的時候,她們對父母有孝心;嫁為人妻之後,對父母的孝就自然而然地轉移到舅姑身上。且宋代女性大多信仰佛教,當親人患重病時,她們會以宗教的方式進行祈禱,并願意以割股療親的方式來救治親人。
(三)心理因素的影響
當然,割股并非正規的醫療救治手段,它隻不過是救命時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患者救治無效時才會使用。墓志所載割股事例都發生在疾病久治不愈的情況之下,比如趙仲轼妻劉氏之舅“飲藥未愈”,鐘子度妻吳氏之母“多方療之未愈”,孟忠厚妻王氏之姑“更數醫不能療”,等等。
“割股”真的可以起到療疾的效果嗎?上表共收錄27件割股事例,被救治者身體逐漸痊愈的有14人,其中有7人治療效果顯著:療效最快的有孟忠厚妻王氏的婆婆“一飲而效”、趙公彥妻朱夫人的母親“立愈”、陳寬之妻王夫人的母親“立汗而愈”等3人;“翌日”而愈的有趙仲轼妻劉氏之舅、趙公恃妻郭安人之姑、朱雲孫妻之姑和揭啟宗夫人黃氏之母等4人。救治無效者有4人,即劉克莊父、葛勝仲妻、張嵲母、趙仲伋,其中葛勝仲妻張氏在兒媳“剔股毀臂灼頂以禱”後,僅幸存了41天。另外9人經割股救治後是否有效,墓志并沒有加以說明,最大的可能性是無效。總體而言,割股療親雖然不是一定有效,但還是存在着有效的可能性。宋代女性采取這種方式救治親人一是因為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二是她們相信至孝可以感動神明,神明會幫助她們實作願望。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孝感神明”思想。
正是這種心理的暗示,“割股者在親人久病沉疴或投治無效的情況下,希望以己之至誠感鬼神、動天地,通過超自然靈力而促使病者康複”[10]211。為了使割股行為真正有效,宋代女性還以自殘的方式向佛祖、天神表達自己的誠心。趙士铙妻為救姑“灼臂祈請”;李旦女為親“齋素持誦,燃臂懇祈”;朱氏為救母發誓“露禱減紀一算,刲肝至再,和糜以進,第十立愈,延十有二年,亡之日與露禱之日合”。通過這種方式,一些被救治者的身體逐漸康複了。當然,這些康複原因複雜,最大的可能是患者已經到了病情好轉的時刻,割股隻是導火索罷了。不過,“甯願信其有,不願信其無”的慣習,決定着人們相信割股療親的神效。
關于心理因素的影響,清人賀長齡在《陶孝女刲股療母論》一文分析得非常透徹:“夫療親複何可議,而謂刲股可以療之,則其說非也。意其時必有純孝之人,遇其親疾瀕危,醫治百不效,至于智盡慮窮,無可奈何,乃由至性迫為奇想,以冀幸于萬有一然之天,而天亦遂憐而蘇之,是其是以蘇者刲股之心,而非刲股之能蘇也。……後之人踵而行之,往往而效者何也,則亦惟其心而已。”[11]461是以,割股療親雖然缺乏醫學合理性,但在醫療條件低下的時代卻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
三、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的影響
割股療親的前提是自損軀體,對割股者來說,身體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另外,與唐代相比,宋代女性割股療親的行為明顯增多,這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發生的。是以,宋代女性割股療親行為既反映了一定的社會文化,同時又對自身、家庭、社會,以及後世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一)對女性身體的影響
割股療親雖然是割股者與救治對象之間的行為互動,但墓志往往隻記載救治對象後續的身體狀況,對割股者的身體情況基本不加記錄,似乎割股是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行為。其實不然。唐代以前,割股者隻割大腿肉為藥引以療親,但到了宋代,除“割股”外,還有灼臂、毀膚發、刺血、刺骨肉、灼頂、針臂血、刲肝等自殘的方式。割取手臂、大腿上的肉,毀膚發、灼頂,這些屬于外傷,隻要不感染是可以痊愈的,但肯定會留下疤痕。但是趙必願的妻子湯氏、趙公彥的妻子朱氏刲肝則屬于内傷,即便痊愈,對身體的損傷也是難以想象的。如果一旦發生感染,則可能危及性命。然而,宋代墓志卻均未提及割股者後續的身體狀況。
雖然宋代墓志沒有記載割股療親對女性的傷害,但從明清文獻記載中卻可略窺一斑。如清代榮河縣有一位孝女,為醫治患病父親割左臂上的一塊肉入藥,不久後其父痊愈,而“後見女臂瘡痕”;孝女仇氏的母親得了重病,她悄悄“刲股療之,家人無知者”,後因生子才被家人發現股上有疤痕。肝是内髒器官,又是造血器官,刲肝肯定大量失血,失血過多會導緻昏迷,救治不及時會傷重不治。如明朝崇祯年間有孝婦張氏,其婆婆病重,聽說人的肝入藥能治愈疾病,她便私自刲腹取肝數寸為婆婆做成粥糜,而“血淋漓薦席上”。湖廣漢陽有一個孝婦為了給婆婆治病,三次剖腹取肝做湯藥,“當為湯時,婦全不覺。逾時,瘡甚,婦昏瞆”[12]93。不過,這些記載僅僅提到了女性割股療親行為後産生的即時傷害,如瘡痕、血流不止、昏厥等,而至于她們之後的身體狀況如何,是否完全康複,是否産生後遺症或并發症等,全部沒有提及。可以想象,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如果發生感染,她們會付出多麼沉重的代價。
宋代墓志對女性割股的身體傷害的選擇性回避,展現了墓志作為宋代士大夫傳播價值觀的文獻載體的本質屬性。男性撰寫女性割股療親事迹時往往有所側重,隻記錄女性的孝行,而對女性身體的傷害幾乎毫無關照。這種書寫形式既達到了傳播本家族聲望的目的,也建構了理想的女性形象和行為方式。
(二)對女性及家庭聲譽的影響
在宋代社會文化背景下,女性割股療親雖然對身體是一種傷害,但對本人的社會聲譽以及家庭聲望卻有着另一種“積極”影響。
割股女性的孝行對其家人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使其能夠在家庭中樹立良好的形象,并成為其他家庭成員效仿的對象。鐘子度妻吳氏在室未嫁時,“其母苦上氣疾,多方療之未愈。晨起剔股,和糜以進”。她的兄弟孝立為姐姐的孝行所感召,“亦齋戒露禱,穴胸析肝以救”,最終,他們的母親被救活了。呂仲洙患病瀕臨死亡,他的女兒傷心焦慮,萬般無奈之下,乃“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受到她的影響,年幼的弟弟細良也效仿姐姐拜天祈禱,表示願意以身代,也要割股為父親入藥。因為姐姐反對,弟弟則憤慨道:“豈姊能之,兒不能耶!”[8]13491
在傳統社會裡,妻子的責任是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禮記·内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又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而能否做一個好媳婦與其在娘家時的教育和品性有極大的關系。宋代墓志所雲陳寬之妻“既歸陳氏,能以孝于親者,移于其姑”,這在宋代是非常普遍的觀念。在注重孝文化的父權社會裡,女性是否有孝行對其個人婚嫁有積極影響。人們相信家教好、孝順父母的女子,結婚以後也會是一個孝順舅姑的媳婦。士大夫之家娶親非常看重婚配對象在室時的婦德,而女性婚前的孝行表現則是男方家庭擇媳的重要标準。如趙必願的妻子湯氏在室時曾為治母病而刲股刲肝,趙父聽到後,便“介同列為媒,願得以度支婦”,他相信“為女如此,則其為婦可知”,是以湯氏便嫁入趙家。
女性割股療親不僅可以給自己的婚嫁帶來便利,也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榮譽和嘉獎。從魏晉南北朝開始,封建王朝就将孝納入獎勵的範圍,如《南齊書·明帝本紀》記載建武元年十一月,“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從孫,義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闾,赉以束帛”[13]46。到了唐代,唐高祖在诏書裡提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闾”[14]5。之後,曆代帝王也都對孝行進行旌表。女性割股是極孝的行為,也會得到相應的獎勵。比如前文提到的唐代夏氏夫人,官府就對其家“褒賜累加,蠲免徭役”。而在宋代,由于理學的興盛,孝道更得到社會的重視,子女是否知孝成為衡量家風好壞的一個标準。李起渭患病,他的兒媳割股救之,人皆謂“肖望之道行于家,雖女子亦知孝雲”。《右監門率府率妻劉氏墓志銘》也稱:“截發教子,陶氏之母。割肌愈舅,趙宗之婦。千載之後,過者式墓。”志文将劉氏比作曆史上有名的截發教子的賢母,不可不謂盛譽之高。割股療親不僅使女性自身獲得了榮譽,也提高了她們家庭的聲望。整個社會衆口同聲對孝女孝婦自殘盡孝行為表示贊賞和頌揚,進一步影響了女性的行為方式。
(三)對明清女性的影響
宋代女性割股療親行為不僅在當代産生了影響,也廣泛影響了後世女性,她們成為後世孝女孝婦的模仿對象,開啟了明清女性割股孝親的極端風氣。
出于統治需要,明朝政府推崇理學,朱元璋甚至下令天下學子“一宗朱子之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15]卷2,14。科舉考試實行八股文,以朱子編撰的四書五經為準,程朱理學的婦德觀影響越來越大,宋元以來極孝的婦德觀念得以傳承。随着理學影響的漸臻擴大,女性割股療親行為在明清時期更為常見。
割股的孝行在明代依然受到贊賞,有割股療親孝行的女子往往更受士大夫階層的青睐,有人是以而嫁入官宦之門。山西有一孝女杜氏,其父久病不愈,杜氏聽說“得生人血肉可療者”,随即刲股肉哄騙父親吃下,“弗愈,再割”。她的事迹傳開後,衆人交口稱其孝,當地太守陳方瀾“聞而賢之,為子聘焉”。此外,各地方志《列女傳》中多記載割股療親的女性事迹。張文祿在《明清皖北婦女割股療親原因探論》一文對明清皖北地區女性割股療親現象進行統計時指出:“《道光阜陽縣志·烈女·孝婦》中有詳細孝行事迹記載的34人中,割股療親的有23人,占近68%;《光緒宿州志·烈女志·孝淑》卷中有詳細孝行事迹記載的36人中,割股療親的有31人,占近86%;”[16]105可見,明清時期女性割股療親的孝行是較為常見的。
墓志銘作為一種記事載體,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事者的生活狀況,同時也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需求和撰寫者的思想意識。墓志對割股療親女性事迹的記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事者至誠至孝的形象,是部分中上層社會女性真實生活的寫照。雖然割股療親損傷了她們的身體,但卻促使她們在家庭領域中擴大影響,為自己和家庭赢得良好聲譽,同時也影響了後世女性的行為。不過,她們的行為受到傳統孝文化和理學的雙重影響,是以,盡管她們的行為帶有一定的主體能動性,但依舊是在父權制文化體制下進行的對女性身份自我認同的一種實踐。此外,女性的墓志銘大多是由男性士大夫所撰寫,這無疑展現了宋代士大夫對女性理想形象的建構。
注釋及參考文獻
注釋:①參見張文祿:《明清皖北婦女割股療親原因探論》,《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曹亭,謝敬:《清代安徽地方志所載女性“割股療親”考》,《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4年第8期;徐鵬:《誰之身體?誰之孝?——對明清浙江方志記載女性“割股療親”現象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2015年第5期;方燕:《宋代女性割股療親問題試析》,《求索》,2007年第11期。②參見焦傑:《身份與權利——唐代士族家庭婦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頁。③參見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④參見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參考文獻:[1]俞福海編.甯波市志外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焦傑.附遠厚别 防止亂族 強調成婦:從《儀禮·士昏禮》看先秦社會婚姻觀念[J].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5):40-45.
[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
[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M].陳植锷,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5]程颢,程頤.河南程氏遺書[M]//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
[6]蘇轼.蘇轼文集[M].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7]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8]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9]董诰編.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方燕.宋代女性割股療親問題試析[J].求索,2007(11):210-212.
[11]賀長齡,賀熙齡.賀長齡集 賀熙齡集[M].長沙:嶽麓書社,2010.
[12]計六奇.明季北略[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13]蕭子顯.南齊書[M].周國林等,點校.長沙:嶽麓書社,1998.
[14]宋敏求編.唐大诏令集[M].洪丕谟等,點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15]陳鼎.東林列傳[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
[16]張文祿.明清皖北婦女割股療親原因探論[J].安徽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5(3):105-108.
一宋史研究資訊一
編輯:潘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