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京是合肥
而徽京卻是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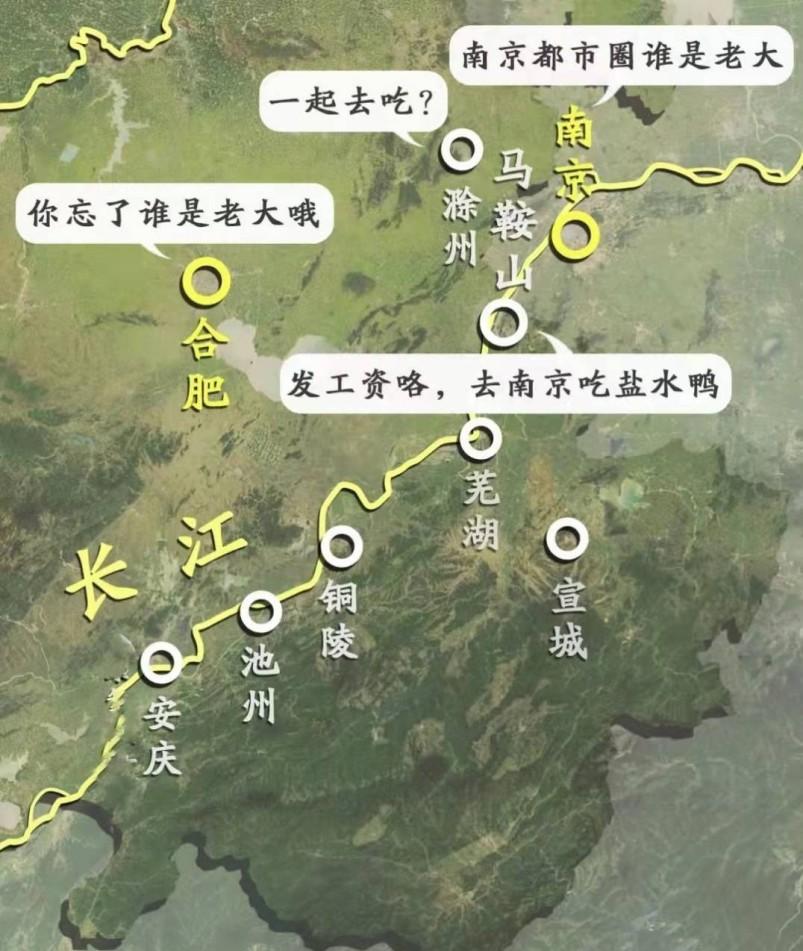
今日中國有近300個地級市,它們在諸如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地理環境方面,多少都存在着差異,可它們也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對省會都會有些不認同。
比如合肥的“霸都”名号,多少都有些名不副實,合肥以省會的身份登上曆史舞台,其實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安徽江蘇甚至還是一家人(江南省),即使在江南分治以後,安徽的行政中心也在安慶、蚌埠等地兜兜轉轉,其次作為安徽的省會,合肥在清末開埠以來,确實很少聽說過爆發過什麼重大戰役或者曆史事件,尤其是周遭省會都赫赫有名的情況下(風起雲湧的南京、各方角逐的鄭州,趕滬超津的武漢,即使是阿卡林省的省會也打響革命第一槍),更顯得霸都名聲不顯。
不過在中國古代的曆史上,位處巢湖北岸的合肥,可不像現在這般默默無聞。
比如在東漢末年至三國時期,曹魏和孫吳政權,就為了争奪合肥的控制權,曾爆發過五場戰役。畢竟對于孫吳政權來說,能否順利拿下合肥,已經成為了關乎生死存亡的大事。
熟知中國曆史的人,肯定都知道守江必守淮的說法,之是以這麼說,主要是由于長江中下遊平原,受到地形的影響被分割成三塊,分别是環太湖、環鄱陽湖和江漢平原,在科技發展到足以打破大山所帶來的的實體隔閡以前,要想将上述三個區域連接配接在一起,江東政權所依靠的就隻有長江了(南方水系雖多,可能滿足國家級戰略需求的,就那麼幾條,而且沒有枯水期的就更少了)。
淮河前線
請橫屏食用▼
當江東政權有南陽和淮南在的時候,長江完全可以作為軍事排程和後勤線集中調配資源,利用有利的地形和防守體系堅守待變,反之北方軍力一旦抵近長江一線,那麼江東政權三大核心區域彼此的聯系,随時都會被切斷,如此下來南方各駐守将領隻得各自為戰,即使難以攻下,也能利用聯絡不暢的優勢伺機挑起争端甚至策反,哪怕不能得到土地,也能削弱南方的綜合實力(印度就是這麼做的)。
其實看似天險的長江,實則處處都是漏洞,是以意欲以北平南的英雄們大都不太看得起長江天塹的作用,正如《三國演義》中荀彧為曹丞相劃策所雲:“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
江南政權所有大都會基本都在江邊或離長江咫尺之遙且無天險可供扼守,前者如南京,後者如杭州。而長線一旦被北軍突破,江南政權因為缺少緩沖,政權中心被兵臨城下很快就會勢如山崩——從南唐到南宋再到南明無不如此。
自古以來,北方政權但凡要南下進行擴張,在大方向上無非就是三條路,西線從關中、隴右出發,通過大巴山脈、巴蜀群山南下,中線越過南陽盆地和漢水,抵近荊襄将南方政權攔腰斬斷,而東線從皖北、徐州南下合肥,占領皖南跨江而過完成統一。
在上述三條線路中,西線太遠,隻能作為輔助路線或者不得已而為之的次要選擇(蒙古攻南宋),而采取中線方案的話,且不說荊(襄)襄(樊)防線非常堅固,而且在北方政權沒有在東西兩線取得重大進展的情況下,荊襄非常容易獲得巴蜀、江東的支援。而至于東線為什麼是合肥,而不是其他地區,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半個江蘇都泡在了海裡。
中路集合團戰
争取攻下許昌▼
除此之外,東吳政權進攻合肥,也可以利用南方衆多的水系,将東吳的戰力提升到極緻,從表面上看,東吳是占據地利的那方,其實不然,曹魏在合肥攻防戰中的地利優勢更大。
東吳在從蜀漢手中奪得荊州之前,若向北進攻的話,可供選擇的戰略方向有兩個:在長江下遊過江與曹魏争奪蘇北平原,進而威脅山東(青州);在長江中下遊交接處過江,控制淮西地區,進而對中原展開争奪。當白衣渡江東吳獲得荊州後,可以從荊州出發沿着漢水上溯,繼而設法在中原逼迫曹魏遷都(反之曹魏南下,也隻能這樣)。
至于為何沒有其他選擇,主要是因為鄂皖之間山地的阻隔導緻的。不過這三條路線都存在些許問題。而至于東吳在早期選擇了東線,主要原因就是相比較其他兩條,跨越長江拿下合肥是最好的選擇了,即使齊本身也存在了衆多問題,比如古邗溝水道經常淤塞,曹丕沿古邗溝水道南下時,就在這條水道擱了淺并最終戰敗的。而至于其他兩條,除了遠離東吳核心區域外,也與東吳不擅長陸戰有很大關系。
那麼如此下來,對東吳最有利的,就隻有東線了,隻要成功拔掉合肥這個大号路障就可以了。而且能否成功拿下合肥,對于東吳政權來說還有着關乎國家存續的重要意義。
三國時期的東吳,國土面積看似巨大(揚州加荊州加交州),可真正有價值的地方卻寥寥無幾。由于長江沿岸存在大量山區的緣故,緻使吳國真正有價值的精華國土,基本沿着長江分布,宛如絲帶一般貫穿吳國國土,而密布的山區又進一步制約了吳國的開發和發展,除此之外險峻的地形,又加大了吳國征伐蠻族部落的難度,緻使吳國不得不派遣大量軍隊分駐在南方各地。
其實我們攤開三國時期的地圖,就可以輕松的發現,吳國之是以如此熱衷于攻下合肥,完全是出于避免國土被曹魏貫穿,畢竟依靠長江沿岸勉強支撐的東吳,最怕的就是首(江東)尾(荊州)不能相顧,而這個最緻命的地點,就是合肥地區。
根據《水經注》的說法,合肥因施水(今南淝河)和肥水(今東淝河),在夏季河水暴漲之際交彙于此處而得名。而這兩條河流的存在,更讓曹魏有了必須占領的理由。
東吳水師
通過水路,直抵許昌▼
三國時期安徽地區最著名的河流就是濡須水了,而濡須水就是連接配接巢湖和長江的河流之一,而巢湖的西北方就是南淝河了,若再往西北的話,甚至還可以實作乘船從長江出發,直接深入中原沃野(甚至還能直接乘船兵臨許昌城下),反之亦然,曹魏軍隊也可以乘船直下江東。
不過相比較南淝河,東淝河對東吳更加緻命。别看如今的東淝河的水流已經很小了,可在一千八百年前的三國時期,東淝河的河道深到甚至能通行大中型樓船艨艟戰艦。
當時如若魏國想要南下伐吳,大軍完全可以在許昌集結乘船進入淮河,沿東淝河可以直抵合肥,休整後再走南淝河沿着巢湖西岸進入濡須水,若戰事順利的話就能直接登陸采石矶,威脅吳國都城建邺。
在黃河改道還沒禍害淮河流域的時期,南方割據勢力一旦占領合肥利用水軍優勢進入淮河,就能沿着穎、蔡、渦、汴、泗五條大的支流,可以抵達中原各處。這樣下來,隻要孫吳能夠維持這樣的局面,成功堅持到曹魏那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動蕩的發生,孫吳政權在中原将發出更大的聲音,而不僅僅是作為偏安東南的地方性政權。
從戰略角度分析,合肥對于長期被壓制的東吳來說,顯然是必須要控制的。這樣看來,後來吳國共計五次試圖打下合肥,也完全可以了解了,直到孫權基本死心了,才兵臨荊州的,可即使這樣,諸葛恪也仍然嘗試打下合肥。
東吳東線進攻▼
既然吳國有必須拿下合肥的理由,再加上吳國水師強于魏國,可為何吳國始終攻不下合肥呢?
合肥北邊的淮河流域,是曹魏控制下核心區域,隻要合肥沒有被東吳快速攻下,那麼合肥就能通過密布的水道,獲得來自曹魏後方源源不斷的支援。
而合肥西南邊就是大别山區的突出部,再加上合肥東部那綿密的江淮丘陵,緻使合肥的北側、東側、西側和西南側,都擁有一定的屏障,如此下來合肥隻能試圖從南方進攻合肥了。
這樣的局面,緻使吳國隻能從一個方向進攻合肥,而隻要合肥的北面隻要還屬于同一政權,那麼合肥隻需要確定正南方不出現問題就可。與此同時水上的情況也差不多,不管東吳軍隊從哪裡進犯,最終的登陸點隻能在合肥南部。
如此簡單的防禦方向,給了合肥在城外布置外圍防線的優勢——隻要把所有的資源都投放到南方消耗敵人就可以了。
東吳北上▼
孫權在前兩次進攻合肥的過程中,也吃了進攻反向少的虧,尤其是第二次,威震逍遙津之是以會發生,就是由于張遼确定自己不用擔心退路的緣故,才敢于放手一搏的。
經過前兩次打擊的孫權,徹底被打敗了,其害怕到躲在巢湖中不敢上岸的地步(随時準備撤退),如此下來,東吳的第三第四次入侵合肥自然也失敗了。而東吳也迫于無奈,隻能退而求其次在濡須口布防。
而至于諸葛恪的最後一次北伐合肥,完全是諸葛恪為了滿足自己野心強行為之。當然,曹魏之是以能夠長久地守住合肥這座重鎮,也與鄧艾脫不了關系,經過鄧艾的治理,原本荒蕪的淮河中遊地區,完成華麗的更新,随着曹魏占領區物産的日益豐饒,最終讓東吳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隻要魏國對吳守住幾個關鍵點
内修政理、發展生産
吳國是絕對耗不起的,對孫權而言
拿下合肥,至死都隻是個夢想▼
至于合肥最終為何會沒落,也與時代的發展、全國各地往來通道的轉移,有着非常大的關系,随着京杭大運河、海運時代的來臨以及鐵路的迅速發展,緻使合肥逐漸失去了昔日華東地區的南北樞紐地位,并最終迫使如今的合肥,隻能依托長江經濟帶才能進行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