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島渚是日本"新浪潮"電影著名的代表人物,也是日本電影史上極具争議的導演。從知名度最高的《戰場上的聖誕快樂》,到描寫情欲的《感官王國》(編者注:也譯作《感官世界》,此處沿用書中譯名),再到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儀式》和《絞死刑》,他的影片風格變化多端,具有獨特的個性,但幾乎所有作品的主題都有反傳統的觀念。該如何總結大島渚的創作主題?在日本電影史中,他占據什麼樣的地位?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大島渚與日本》,較原文有所删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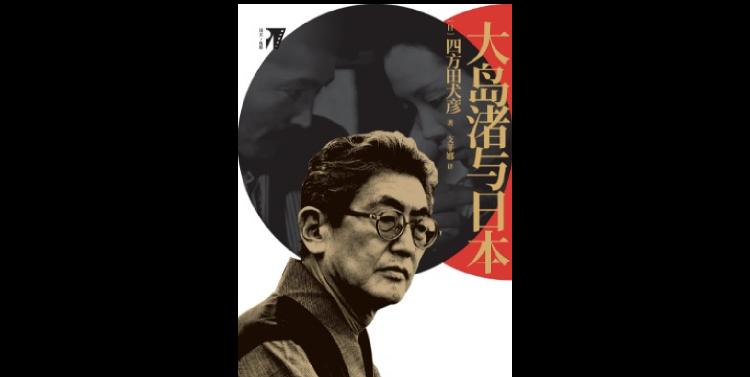
《大島渚與日本》,[日]四方田犬彥著,支菲娜譯,培文 |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站在當下的立場拍電影
電影史上著名的巨匠們大多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是以哪怕僅僅窺得影片的一鱗半爪,也能猜出是出自哪位導演之手。比如愛森斯坦是通過細小的鏡頭組接與重複來形成叙事詩式的精神探索;小津安二郎是徹底背離古典好萊塢的視聽語言,形成了低機位和正面凝視的畫風;與大島渚私交頗深的安哲羅普洛斯,則是在排程複雜的長鏡頭中詩意地展現多個時空。那麼,大島渚身上存在一種與這些導演相匹敵的、能夠簡單讀取的風格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簡直令人詞窮。
畢生風格變化多端,而且每一種風格都接近極緻,竭盡全力去追求每一種風格飽滿得即将崩潰的臨界點,卻絲毫不拘泥其中,在下一部作品中立即投身于開創另一種導演風格與剪輯秩序。他就是這樣的導演。某些批評家一直回避大島渚,其原因是他們被主題論和寓言交織成的簡單坐标軸所桎梏,腦中根本無法浮現大島渚的整體面貌。那麼,是不是根本沒有貫穿大島渚劇情片與紀錄片的要素呢?答案是否定的。
日本導演大島渚。
首先,我們隻要想想,他的那些影片中戶浦六宏、小松方正、小澤昭一或是大島渚本人的旁白聲是那麼铿锵有力,偶爾甚至是作為一個挑撥的叙述者存在,就明白了。在《被遺忘的皇軍》《忍者武藝帳》還有《絞死刑》中,決定整部影片基調的是粗糙而充滿自信的聲音。要綜合了解大島渚作品,隻有一種方法,就是把《少年》中年幼的主人公那磕磕巴巴的獨白和上述這些铿锵有力的聲音相提并論地對立起來看。聲音與聲音相重合的地方就産生歌聲。大島渚的演員們隻要一有機會就高歌放吟,這正是大島渚風格的本質。
其次,我們來看看他的場面排程。回想一下,《日本的夜與霧》中悄悄進入某個房間的攝影機,不留死角地拍遍了房間裡從中心到周緣的各個角落,似乎是要通過場面排程的力量,促使人們正在房間裡搞的僞善宴會解體。令人吃驚的是,在這部影片裡,大島渚比安哲羅普洛斯更早地隻用一個鏡頭就展現了多個層次時空間的沖突。
但是,大島渚從不執念于自己采用的這種場面排程風格。在他六年後完成的《白晝的惡魔》中,他用了約是一般劇情片鏡頭數四倍的2000個鏡頭,來表現關于視野的拓展、視點的轉換與凝視的閉塞。從《日本春歌考》到《歸來的醉漢》,他不斷擺脫完整的故事架構,在《新宿小偷日記》中達到了荒誕不經的巅峰。但在1978年拍攝的《愛的亡靈》中,這種實驗性又痕迹全無,他隻是用紮實完整的叙事來講述奇幻劇情。到了《禦法度》中,他又像是故意顯擺似的,在片頭和字幕上都用了複古手法,給單刀直入的故事開篇平添了反諷意味。
電影《禦法度》劇照。
最後,大島渚作品中沒有那些讓影迷着迷的、對經典電影的緻敬、解構或是影射。大島渚常常宣稱自己對指涉電影史毫無興趣,一直是站在當下的立場拍電影。有不少人是因為看了某部經典作品深受觸動才走上電影導演之路的,大島渚則完全不是這種路數——如果把《愛的亡靈》中約略影射戰前阪東妻三郎的電影《無法松的一生》這件事當作罕見例外的話。某一時期,大島渚隻要一有機會就寫文章關注戈達爾,就像是和戈達爾針尖對麥芒似的,不斷開展先鋒的影像實驗。不得不說,在制作态度上與戈達爾那種資深影迷式的導演背道而馳的,恐怕舍大島渚别無他人。也許大家還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呼風喚雨的電影研究期刊《盧米埃爾》一直無視同處一個時代的大島渚,而論及原因,正是在此。
大島渚的電影主題,
存在着許多不可否認的斷層
如若從年代的軌迹來爬梳的話,一目了然的是,在作為導演的大島渚眼裡,最重要的并不是電影風格,而是按照主題的要求來做出改變。一方面,他的風格總是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但另一方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主題總是極其舒緩地、不斷地發展着。不過,就像我們在此前的章節中已經厘清的那樣,他的主題中也橫亘着一些不可否認的斷層。
在委身松竹公司的早期階段,大島渚最為介懷的就是理想主義化的過去與現實之間存在的龃龉。有些人為了苟活于壓抑的現實中而不擇手段,有些人沒辦法如此堅韌終緻自我毀滅,這兩類人之間不斷進行着可悲的抗争。《日本的夜與霧》描寫的正是這種抗争。但是,正因為這部恢宏展現了過去與現在的沖突的電影,大島渚才被松竹掃地出門。
作為劇情片導演度過了暫時的沉默期後,大島渚直面“面對他者”這個宏大主題。不,與其說這是面對,不如說不管願意不願意,他都被卷入其中。他者首先在《飼育》中以極其概念化的形式出現,自《李潤福日記》以來以北韓人這種具象化的形式出現。他在《被遺忘的皇軍》中直面被褫奪了日本國籍、流落街頭的朝裔傷殘軍人,又在《李潤福日記》中直面日韓建交不久後樸正熙政權下的首爾。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後期,他以在日北韓人為主題拍攝了各種各樣的影片。他的在日北韓人題材作品終于從紀錄片轉向了喜劇。而且,以這些他者為鏡面,他漸次揭發了日本社會一直隐瞞和封印的醜聞,并在銀幕上逐一加以拷問。
1968年,大島渚獲得了決定性的轉機。他得以暫時從日本這個被詛咒的故事中脫離出來,以《少年》為契機,一方面将視野擴大到整個日本,另一方面也目光犀利地盯着當時作為混沌體存在的東京這個大都市。他通過與籍籍無名的少年聯手創作,總結出“凝視都市日常景象”這種做法,并重視其所具有的政治性。《東京戰争戰後秘史》中描寫的一連串日常景象,意味着大島渚暫時離開曆史這個時間軸,去面對空間持續無限延伸所帶來的恐怖。它也是大島渚進一步去探究他在《絞死刑》中流于概念化的國家現實應有的狀态。
電影《絞死刑》劇照。
但是,關于景象的探究被《少年》打斷,大島渚又回歸了曆史軸。《儀式》嘗試着給大島渚到此為止的整個主題體系打上一個完美的休止符。自《儀式》後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他開始面對那些在曆史軸上難以觀照的、存在主義式的他者,也就是女性。女性從《白晝的惡魔》時的自我控制中被徹底解放出來,君臨于《感官王國》與《愛的亡靈》,并坦然颠覆男性的視角與世界觀,指引他們走向愛與死的世界。《日本春歌考》等此前的話題作品中,可以看到他那種試圖把性沖動置于曆史語境或社會語境中來解釋的态度,但這種态度在《感官王國》中痕迹全無,這也是《感官王國》中最具特色的地方。
以1970年為分水嶺,大島渚描寫的傾向開始從欲望轉向了快樂。“作為禁忌的他者”這一主題在《馬克斯,我的愛》中甚至擴大到了生物學的層面。但是,一方面,這種對“性的他者”的直面變得更加本質化;另一方面,大島渚也不懈地探究男權社會的内在結構。
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電影曾無意識地描寫了同性社會性集體的内情,而他在《戰場上的聖誕快樂》和《禦法度》中冷靜地展現了這種内情實際上是帶有同志恐懼症屬性的。話雖如此,我們也不能僅僅從這個“性的架構”來裁斷《禦法度》。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它也是大島渚回歸京都的影片。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在1991年導演的紀錄片《京都,我的母親之地》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正是京都裁斷了戰後日本的時空。
對一個以國際化規模來拍電影的導演來講,這個城市是他一直保留到最後的、親密且愛憎交織的秘密花園。這部紀錄片闡明,京都這個被表述成母親子宮的隐喻的都市,無論對母親還是對大島渚自己,都逐漸變成了一個微不足道的地方。這個事實既甘美又悲痛,它是大島渚對所謂往昔這個時間概念第一次表達靜谧的哀悼。如果說《儀式》是通過強權化的父性性來描繪近代日本,那麼可以說,他一直忽視的家庭另一支柱——母性性,就像積年的負債一般,通過《京都,我的母親之地》得以成功償還。以上,就是從主題這個側面觀察到的大島渚作品的變遷。
電影《儀式》劇照。
大島渚在日本電影史上的革命性作用
我們再把距離放得更遠一點來觀察大島渚,看看在戰後日本電影史這個巨大的叙事體系中,他到底發揮了什麼作用。話雖如此,我并不是想要讨論他是不是和溝口健二或者黑澤明匹敵的巨匠這樣的無聊話題。為此,我們隻要預先指出一點就夠了,那就是,世界上哪裡都已經不存在巨匠的神話。所謂巨匠,隻不過是不斷重複“十年彈指一揮間”般的愚蠢懷舊而已。我也不是想宣傳大島渚有多麼偉大——他克服在區區日本的小規模制片狀況,單刀奔赴戛納電影節,并由此享譽國際,成為外國研究者長期觀照的對象。因為,今天的電影無論是從制片角度還是從市場寬容度來講,國際化已經不是問題,再以國際化來評價大島渚未免過時。下面,我們分六點來論述大島渚在日本電影史上發揮的真正的革命性作用。
1. 關于日本,無論在什麼場合,大島渚均是不折不扣的批判者和偉大的痛罵者。
大島渚批判戰争時期日本的新聞體制,揭發母校京都大學的反抗神話是多麼虛僞;《被遺忘的皇軍》批判了戰後日本褫奪舊殖民地出身者的國籍,絲毫不給補償就把他們抛棄;《白晝的惡魔》曝光了戰後民主主義的虛僞與虛妄;《感官王國》曝光了猥亵這個概念本身裹挾的國家層級的僞善。年輕人的犬儒主義本身,是他最為嫌惡的。
他不僅僅是批判,還激烈地挑釁觀衆。話雖如此,但他這種煽動的風格,與同時代導演如寺山修司卻大相徑庭。寺山修司誇誇其談地認為,所謂曆史,其實最終還是歸結到個人的情節劇,是以他專門描寫年青一代,把對觀衆的挑釁收斂于舞台化的結構中。而大島渚不斷糾結于日本人這個概念,對于隐瞞曆史與将曆史神話化,他都強烈反對并追索誰該擔負道義上的責任。正因為如此,北韓人的存在才不得不常常被提及。
大島渚式的批判有時候也會像發條壞了一樣,在宏大的無秩序中轟然倒地,以至于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荒誕不經。《被迫情死 日本之夏》最為典型,它摹寫了在場者舉行既沒有目的又沒有政治價值的酒宴,高歌放吟的結果就是拿起槍起義之時。順便說一句,大島渚不是作為神秘莫測的導演,而是以惹是生非的真實肉身顯現的正是這個瞬間。那個被稱為“大島渚”的惹事精,對各種事件所暗含的政治性有着充分的自覺。而且,在存在狀态上,他也一直努力去展現政治性。20世紀60年代,他意圖操控媒體,身體力行地展現政治,但自從《被迫情死 日本之夏》之後,他幹脆直接化身為媒體本身,來展現激進主義。
2. 在日本電影曆史中,大島渚是個例外,他從正面凝視他者,創造性地将與他者的對決作為主題。
大島渚在《飼育》中第一次明确地凝視他者,描寫了在他者面前搖搖欲墜的村落共同體。擔任編劇的田村孟滿不在乎地無視大江健三郎的原著,把山中的小村落寫得像大日本帝國的縮影一般。所謂他者,在這部電影中就是敵兵,影片以人種學的理由來強調他者的威脅感,即他的惹人生厭起源于他是黑人。
在《飼育》之後,沒有必要再描寫敵人了,但是他者這個認識架構頑固地存留下來。大島渚堅持把攝影機推到那些總是回避對視的日本人面前,并積極地将攝影機對準那些被無視的他者——說白了就是那些在日本公序良俗中惹是生非的他者。他們是隻有通過犯罪才能獲得自我表現機會的貧農之子,是在日北韓人中的榮民,是多次用同一手段犯罪的連續強奸犯,是被槍頂着前額殺死的越南人,是傷殘軍人及其碰瓷家庭……他們在日本社會中被無理驅趕到邊緣地帶,被剝奪了一切發聲機會,最終在貧困之中卑微死去。不管他們是什麼國籍、什麼民族,他們都是戰後社會一直努力排斥的他者。
電影《飼育》劇照。
大島渚凝視他者的目光在《儀式》中達到巅峰。這部影片通過一個從僞滿洲國回國的少年的奇妙儀式,描寫了日本人與日本人之間互為他者、互相殘殺的故事。從整個日本電影來看,大島渚的獨特性之一,在于他打破了日本電影不敢描寫惹人生厭的他者的禁忌,把日本觀衆期望回避的影像強行塞到他們眼前。
3. 大島渚堅決拒絕情節劇。
這一點,自從大島渚在以情節劇為基本方針的松竹公司裡導演了處女作《愛與希望之街》以來早已明确表達。多數觀衆期待在《愛與希望之街》的結尾獲得略帶感傷的和解,而大島渚借劇中哥哥手裡的來複槍,毫不留情地射殺了少年心愛的鴿子,讓人道主義的情節劇解體,就此結束全片。可以說,實際上從此時起,松竹公司以第二年《日本的夜與霧》下線為借口炒掉大島渚的戲碼已然拉開序幕。
從《青春殘酷物語》到《少年》,大島渚的電影多次差點堕落成情節劇。但是每一次他都穿插荒誕不經的諷刺,不讓觀衆掉眼淚,并把他們帶到不可名狀且暧昧的心理狀态。《絞死刑》在歐美被評為布萊希特式戲劇在日本的最高成就,這聽起來不免有些單純化的诽謗,但也不是漫無根據。《悅樂》是僞裝成鬧劇的荒誕劇,《夏之妹》是在無數情節劇屍骸上确立的“元電影”(meta-film)。大島渚講的故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沒有結局。無論是《被迫情死 日本之夏》還是《日本春歌考》,甚至連《禦法度》都根本沒有情節劇應該具備的感情升華,而是叙事突然被打斷,觀衆被置于情節懸而未決之處。
在角色配置設定方面,大島渚出于極其特立獨行的标準與戰略,對找來的出演者不進行詳細的演技指導。這也與他抗拒情節劇密切相關。無論是《日本春歌考》中的荒木一郎、《少年》中的阿部哲夫,還是《戰場上的聖誕快樂》中的北野武和坂本龍一,大島渚電影中的大多數主人公在整部電影中都面無表情,絲毫不表演出任何内心戲。他們像沒有生命的木偶那樣行動着,如若隻是把他們定義為導演心裡的寓意化概念的化身,是不能充分了解這種事态的。簡略到不能再簡略的彩排,還有呆若木雞的表情,是為了把演員身上所潛藏的張力激發出來。另外,這樣做也讓觀衆不能像看情節劇那樣輕易猜到結局,讓觀衆認識到人物超越了對内心情感的诠釋,人物是由不透明物質構成的實物。
電影《戰場上的聖誕快樂》劇照。
4. 大島渚既不“正确”诠釋,也不代表日本與日本文化。
隻要想一想那些比大島渚更早在歐美電影節獲得評價、赢得知名度的“巨匠”,是多麼輕易地被當作日本風格的诠釋者來接納,并被置于異國情趣和東方情調交織的坐标軸中來評價,就能馬上了解這個标題。
黑澤明把武士比喻成日本的道德形象,小津安二郎提出榻榻米與茶泡飯是日本簡樸庶民生活的名額。但大島渚不會像他們那樣,把了解日本的關鍵影像輕易傳遞給海外。說起來,那些看過荒誕不經的《日本春歌考》《東京戰争戰後秘史》的外國人,是否通過這些電影成功獲得了與日本相關的、像模像樣的新知識呢?《夏之妹》雖然以沖繩為舞台,但與汗牛充棟的沖繩題材截然不同,它完全不提供任何與沖繩相關的知識和資訊。《感官王國》不厭其煩地描繪男女的性事,卻對表現時代背景态度消極得令人吃驚。
是以,總的來講,大島渚的作品并沒有像日本人期待的那樣“正确”地诠釋日本。但也不是說,他用令人舒适的叙事來诠釋歐美觀衆期待的異國情調。他隻是将攝影機對準日本人不敢直視的日本,尤其是不想讓外國人知道的日本。沒錯,他是一位生于日本、用日語來拍電影的導演,但若是僅僅以此就認定他的作品大多是屬于被稱為“日本”的這個國家的,不免流于輕率。
電影《感官王國》(又譯《感官世界》)劇照。
5. 大島渚作為電影作者,打破了所有能被想象到的電影制作體制窠臼,并在每一次突破中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大島渚自年輕時起就被趕出了大公司商業電影的圈子。作為代償,他才能在主題、手法和類型上不斷挑戰新的嘗試。他還作為特别評論員活躍在電視上。對于近30年間大島渚頻繁在電視上露臉的現象,我想,應該把它看作大島渚在蓄意創生一種媒體:他非常了解電視是最為政治化的影像,是以他并不拒絕電視,甚至可以說正相反,他是以電視為媒介,嘗試把自己變為媒體。
6. 大島渚既是導演又是作家。他不但對自己的作品展開雄辯,而且也滿懷共鳴地對同時代電影人展開批評。
有不少導演不寫書,也不認為出版著作有多重要。大島渚在日本電影界是個例外,他出版了二十多本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大島渚從自己的導演經驗出發,對影像與政治、影像與曆史不斷發出原理性的索問。這些批評雖然不是學院派的、成體系的,但它們的意義不隻是了解他的影像作品不可或缺的文獻。這些批評把戰後日本社會中關于電影的倫理作為主題,是以超越了簡單的電影史範疇,到達了社會批評和曆史批評的層面。晚年,大島渚還把視野擴大到日常生活(比如夫妻之情等),寫了不少灑脫的随筆。他甚至借自己的康複治療這種極其個人化的話題,來表達他對人世的敏銳觀察。
從既當電影人又當作家這一點來看,如若問誰是大島渚的先行者的話,也許隻有日本戰争時期的伊丹萬作吧。從世界來看,也隻有伊朗的莫森·瑪克瑪爾巴夫或法國的讓–呂克·戈達爾能夠與之匹敵吧。我們不斷閱讀這半世紀間他留下的論述,不得不再次吃驚于他論旨的紮實、主題的寬廣,還有遣詞造句中流露出的嘔心瀝血。
大島渚說過:“敗者無影像。”正是因為人們想看到更為自由的人,是以才看外國電影。如若玉音放送時有人拍下昭和天皇的影像,并在電視上進行直播的話,日本戰敗的意義将會大有不同吧。大島渚憑直覺說出的這個警句,并不隻是闡釋自己的影像作品。對探求影像與政治關系的人來講,這句話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啟示意義。我們回想一下自1980年以來日本電影評論彌漫的頹廢吧:當時大家堅信,電影就像純粹的文本一般,創造電影的隻有經典電影——這種信仰在日本電影評論界像傳染病一樣蔓延開來。那時,從一開始就被評論抵制的正是大島渚,他所呼籲的“作為運動的電影”是逆時代之流而上的不幸插曲。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被我們銘記。
原作者 | [日]四方田犬彥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 | 青青子
導語校對 | 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