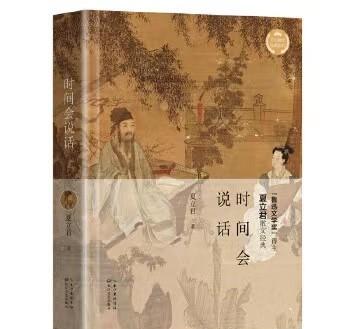
□ 李毅然
《時間會說話》是夏立君先生的第四部散文集, 2019年11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文集是作者繼《時間的壓力》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後,奉獻給當代文壇的又一部力作。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輯“生命有初衷”,講述印刻在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鄉情逸事;第二輯“時間會說話”,解讀從先秦到明末清初的一些代表性古人;第三輯“腳趾要自由”,回望西部支教遊曆的人文景緻及生命體悟。
實錄生命的初衷,寄情赤誠而深遠
文學創作大都離不開養育自己的故土,那裡既是生命的原點,又是創作的源泉。對于作者來說,故鄉就是位于沂蒙山腹地沂河岸邊的那個小村莊,它孕育和承載了彌足珍貴的生命初衷,成為一種凝結于時間單元裡的醇厚珍藏。
第一輯的11篇作品,作者真實記錄了彼時沂蒙山的貧窮落後,以故事形态細數了自己與親人及鄉鄰的過往,他們為了生存,為了活好、過好,便自然有了對生命不息的渴求,并通過内在的能量彰顯生命的意義,讀來不禁令人動容,主要表現在:
1、作者母親一生養育了七個子女,她從年輕時就體弱多病,但卻為了孩子為了家庭,一直頑強地活到了87歲,書寫了“卑微、真誠、高尚、樸實”的一生;作者父親在子女心中堪比大山,在鄉親們心中“有能為”,活出了一份“正直坦率、豁達真誠、活得不糊塗有細節”;作者二舅雖傻卻留下了異常勤勞的生命印迹;等等。這些生活在鄉村環境裡的人物,是衆多鄉村老人純樸和善良、艱辛和努力的真實寫照。
特别是在作者母親的身上,更多地呈現出被文字所照亮的美好人性:當她得知調皮的三兒用腳踩踏螞蟻時,埋怨兒子不該作踐螞蟻;當她得知屋檐下的燕窩裡有新出生的小燕子時,囑咐三兒千萬别吓着老燕子,生怕把老燕吓飛撇下孩子不管;當村裡一些人家将乞丐無情地拒之門外時,她卻将家裡不多的飯菜用來打發乞丐,還與乞丐進行溝通交流,她把自己最真誠的仁愛交給了素不相識的乞丐。在那個貧窮落後的年月裡,又有幾戶人家不過得捉襟見肘呢?在那種自顧不暇的情勢下,作者母親的所作所為委實令人感佩。這位被鄉親們視為“無能為”、看上去愚昧、卑微到離世前連用幾片蓆子都自愧的普通農村婦女,卻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财富。這些美德宛若星辰般璀璨奪目,照耀着孩子們成長的道路,這也就不難了解作者為何會給乞丐和漠虎食物,為何要為面目全非的河流和樹木鳴不平,為何要站在少年英雄夏完淳墓前熱淚長流,為何要主動請纓到遙遠的新疆喀什支教了。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心懷良知與悲憫,将内在的能量作用于社會,這是人類應該折射的深遠星輝。
2、對于年少的作者而言,飽嘗了貧窮所帶來的苦難滋味,但這并未妨礙内心對理想的追求,反而促使他以一種隐忍而強大的情感,努力追求生活的方向和人生的目标,進而樹起自強不息的人格魅力。作者在《生命的初衷》裡坦言:“我的人生追求,是從乞丐出發的。”在彼時的作者内心,當一個走街入戶的乞丐,既能擺脫饑餓的夢魇,又能見識外面的大世界。當他看到四弟因為耳朵裡的大豆生了豆芽而到山外的界湖和臨沂就醫時,也往自己耳朵裡塞了一顆大豆,結果卻挨了爹狠狠兩腳,隻好把有豆粒的那一側腦袋使勁往沙丘上摔,摔得天旋地轉才把豆粒摔出來。透過作品生動感人的描述,讀者可以感受到那顆渴望大世界的奔騰之心。正是這顆奔騰之心,激勵着作者“窮且彌堅,不墜青雲之志”,經過多年的努力,他作為全村唯一的師專生走出了大山,後又從沂蒙山跋涉到遙遠的喀什,又跋涉到海濱城市日照,直至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作家,終于實作了年少時立下的文學夢想。
在作者多年的遊子生涯中,那些故時的日常風景早已凝結成難以割舍的鄉愁,轉化為充盈于時間單元裡的文字,包括對彼時河流的深情描摹(《生命中的河流》),對童年世界和生靈世界的趣味書寫(《一粒大豆的喜劇》《蟋蟀入我床下》),對親人的深切懷念(《娘用她的影子》《你是我的爺》《傻子二舅》),對鄉村春節習俗的詳述(《門神門神扛大刀》)。這些飽蘸淚水的深情回憶,皆被作者賦予了特殊的意涵:老家雖然閉塞、貧窮、落後,但也是幸福、溫暖、夢想的精神濫觞,故鄉是永遠的根。
堅守精神領域的故鄉,注重制實與文化的重建
梁曉聲曾說過,“人應該有兩個故鄉,一個是現實地理的故鄉,另一個則是精神上的故鄉”。精神故鄉是通過自我尋找與自我構築建立起來的,一個人隻有過上良好的精神生活,才能保持思想、靈魂和精神的一緻性,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覺知。在《時間會說話》中,作者努力拓展精神故鄉的廣度和深度,審視自我在時間裡的特定品質,讓曆史與現代在别具一格的文化理念和審美精神中交融,以更開放、更宏大、更嚴謹的态度對待現實與文化的重建。
一、視曆史文化文獻為精神故鄉,在一種純粹的熱愛中,呈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堅守和創新。作者自小便喜讀史書,常常讀哥哥的課本,還常到村裡的知青點借書讀,那些《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小冊子,打開了最早通往文學夢想的精神路徑。這種自少年時代養成的興趣愛好陪伴了作者半生,他潛心研讀曆史人物并用文學方式表現出來。盡管作品中有些文字乍一讀好像挺突兀,但隻要耐心讀下去,便會發現愈讀愈有味道,甚至會喜歡上這種獨特的思考和獨特的氣息。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好作品必然要有與衆不同的靈魂,第二輯的10篇作品亦如此。這組作品彰顯了獨特的曆史意義和思想光彩:
其一,在借鑒前賢研究的基礎上,“疑前人所未疑,試前人所未試”,獨辟蹊徑,貼着人性往深層寫,對細微之處觸摸、拆解、重構事物,富有系統性和開拓性。比如,作者從多個角度切入,描述了李白、陶淵明、屈原、曹操、司馬遷、夏完淳等代表性人物的人生遭際、性格特征、精神追求、思想狀況,品評這些名人詩文的美學特征和曆史影響,深度開掘蘊藉在曆史文化中的人性秘密以及命運的悲與喜。
其二,敢于突出所述時間單元裡的生存本身、現實本身、曆史本身的不完美性和缺陷性,進而窺見人類文明史、精神史、審美史的長處與不足。比如,作者敢于對屈原和李白的“婢妾心态”、對“貶李揚杜”的千年傳統、對曹操的不公平待遇、對李斯身上透出的帝國體制之惡與人性之惡等等,進行大膽揭示與批判,努力做到“在批判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又如,作品中所描寫的幾個人物都深陷絕望境地,包括屈原對故國現實的絕望、李白對功名仕途的絕望、司馬遷對殘廢身體的絕望,但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反抗絕望,這與魯迅哲學中“反抗絕望”的核心概念一脈相承。由此可見,作者有着過人的藝術膽量,這既是一抹顯現批判力量的光輝,又是一抹顯現創新力量的火焰,真正展示出古人與今人對接的現實意義。
二、視大自然為精神故鄉,在勞苦跋涉中煥發寫作激情,展示燭照心靈的人生體悟。
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說:“‘讀萬卷書,行萬裡路’,二者不可偏廢。”作者對此深以為然。他為了攀登文學創作的高峰,甘願承受“行萬裡路”所帶來的磨難,特别是在西部支教的三年裡,除了教書,其餘時間幾乎全部用在了旅途上:曾獨自穿行于荒涼的戈壁沙漠,曾獨自騎車穿梭于綠洲間,曾獨自走近慕士塔格雪峰下的險惡峽谷,曾獨自流連于東湖邊,曾獨自堆沙為枕露宿于野外,曾獨自立于夏完淳父子墓前,大放悲聲予以追思……這一幕幕場景令人感佩至深。
品讀第三輯的10篇遊記,這些作品在繼承西部散文原有的體裁、風格、手法、體式的特征基礎上,融入了散文寫作中的議論色彩和抒情色彩,特别賦予了現實意識、生命意識和人文内涵,譬如:浩瀚、豐腴、純粹、徹底的沙漠(《懷沙》);有着家族團結和堅守精神的紅柳,有着悲壯勇士精神的胡楊(《根》);擺在大地上的唯美而浪漫的草原(《那拉提》);有着童貞般召喚力和誘惑力的麥積山(《麥積山》)等等,這使得作品并未淪為令人生厭的遊記垃圾,反倒成為饒有興緻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