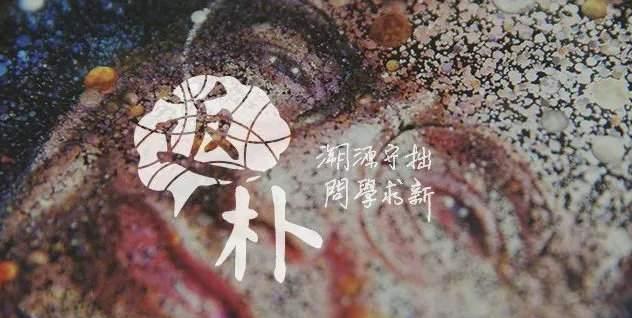
2022年1月8日是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80周年誕辰紀念日。雖然普羅大衆對霍金的科研成就所知所懂甚少,但這位傳奇實體學家對宇宙的純然熱愛和無畏堅持的精神依然感動并鼓勵着諸多尊重科學、向往科學的人。
湖南科技出版社向《返樸》讀者贈送《愛即生命:史蒂芬·霍金誕辰80周年紀念套裝》一份,前往“返樸”,點選“在看”并發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區,截至2022年1月15日中午12點,我們會選擇一條精彩留言,贈送套裝。前往“返樸”,點選文末小程式或“閱讀原文”可購買此套裝。
撰文 | 葛之
生于伽利略忌日的霍金,在愛因斯坦生日那天去世。作為英國人的驕傲,霍金的骨灰被安放在倫敦西敏寺中。在時間上與伽利略、愛因斯坦巧合,在空間上與牛頓、達爾文為鄰——看來霍金這人真是命裡注定的時空大師啊。
一說到霍金,廣為人知的必是這三件事:身殘志堅,理論泰鬥,科普大牛。隻要少了其中任一項,他就未必能廣為人知。比如彭羅斯、溫伯格就隻具備後兩條,知名度便差了很多——這其實是源于社會和市場的非理性。霍金恐怕是迄今唯一一位活到21世紀的、世界範圍内婦孺皆知的科學家。他是得獎電影主角的原型,還親自客串電視劇,他坐輪椅的樣子甚至進入了遊戲。更不用說他的科普經典《時間簡史》,暢銷30多年,經久不衰,以至于後來出了很多書均沿用“簡史”為标題,且大都不是拙劣模仿,有的甚至也成了經典,如《萬物簡史》《人類簡史》《資訊簡史》。是以有人感歎說,霍金既是棄子也是寵兒。
就在逝世的前一年(2017年),霍金通路了牛津大學,跟懷爾斯(費馬大定了解決者)、彭羅斯一起留下了這張珍貴曆史照片(下圖)。他們三位都是當代最具智慧的人:霍金留下了西敏寺的一席之地,懷爾斯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大樓,彭羅斯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地磚。
自左至右:懷爾斯(Andrew John Wiles)、霍金、彭羅斯(Roger Penrose)
2022年對霍金迷來說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年份:霍金80周年誕辰。在此之際,作為宣傳霍金并深得霍金認可的中國獨家機關,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愛即生命:史蒂芬·霍金誕辰80周年紀念套裝》。我想到霍金的1月8日生日肯定還會有不少活動,唯一有點小遺憾的是,這個生日往往是很多學生複習迎考甚至正在考試的日子。
本文不專門談及霍金具體的科學貢獻,這方面的文章已很多,也不探讨他科普作品的具體内容和風格,而是借此紀念時刻,聊一下現代以來科學和科學家(特别在我國)的形象之變遷,它們與價值觀的變化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關系(本文所說的科學家主要指數學家和以實體學家為主的自然科學家)。
國人了解霍金的過程
我還清楚地記得1990年代初第一次在書店裡看到包括《時間簡史》在内的“第一推動叢書”的情形,黑色封皮,紅色護封,擺放在書架上特别引人注目。其實,在此之前還有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的《時間的簡明曆史》等三個譯本,但都悄無聲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的版本終于一炮而紅。從此以後,我一直關注第一推動叢書。經典的科學和科普不會過時,第一推動叢書的生命力是長久的。本來是見一本買一本,後來認識了出版社的吳炜老師,我經常會收到吳老師寄來的書(包括不斷更新的叢書,也有并非叢書中的,比如《愛即生命》)。此外,因為工作關系,我也與《時間簡史》的譯者、霍金的學生吳忠超先生打過一次交道。他們都恰巧姓吳,令人聯想到霍金等提出“無”中生有的量子宇宙這樣的巧合。
《時間簡史》湖南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丨作者供圖
霍金一共來過中國三次,其中2002年第二次來參加國際數學家大會時在國人心中的名聲達到頂點(本來我已報名參加,後因故未能成行,幾位朋友去參加會議,有幸見到了霍金以及納什)。雖然霍金最引人關注的特點是身殘志堅,但國人廣泛認識他是從《時間簡史》開始的。1985年他初次來中國時,《時間簡史》尚未出版,行程幾乎悄無聲息。但當他第二次來中國,《時間簡史》已在全世界暢銷很久,霍金早已名滿全球。不過,我們也必須看到,科學和科學家在國人心中的地位,在1985年還是相當高的,而霍金後兩次來中國時,就稍微低一點了(這也是一個必然過程,1980年代“文*革”結束不久,大家比較講精神、談理想,後來人們就比較講求物質,我相信物極必反,是以不會無限地物質下去)。這也可以解釋為某種“超前”效應:今天科學和科學家地位的擡升,有霍金做出的貢獻(科學啟蒙要從娃娃抓起嘛,當年聽霍金演講的很多是中國小生,現在他們中的不少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當然也必須看到,要保持這一地位,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寄希望于霍金一人顯然也是不切實際甚至荒唐的。
中國人對待科學乃至科學家的情愫确實異常複雜。在古代,幾乎沒什麼科學概念或理論,主要是一些實用技術。近代開始,科學和科學家的地位就像過山車一樣上上下下。清朝時期,很多人對科學技術壓根就瞧不上。五四時期國難當頭,科學的地位變得很高,幾十年後急轉直下,不少科學家被視為“反動權威”“白專”遭到批鬥(當然軍事工業還是受到重視)。接着迎來“科學的春天”,科學家又被拔到極高地位,陳景潤是我們那代人所知的第一位(很可能也是不少人聽說過的唯一一位)數學家。而後呢,又有所下降。1980年代學校裡談理想,幾乎人人想當科學家,2000年後則不足兩成。隻是到了最近,由于量子實體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進展得到商界大佬和政府的大力支援,科學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又有上升。
西方在對待科學的觀念上也有起起落落,但周期很長,而且和我們的情形不同——至少在古代。古希臘可以稱得上是第一個舉起科學大旗的文明,主要是泰勒斯、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等人的作用(其他古代文明即使有科學技術,絕大多數也早就失傳或進博物館了,但古希臘包括科學在内的思想則不然——這就是雅斯貝爾斯說的“軸心時代”——不僅指在當時很出名,而且至今仍深刻影響着人們的觀念),但是後來羅馬以及中世紀的歐洲是另一族人的天下,想法和觀念本來就不同,他們不待見科學也屬正常。之後就是文藝複興,柏拉圖的主義獲得“新生”,柏拉圖主義當然是極龐大的思想體系,主要觀點是一種精英主義治國論,科學家是典型的精英,是以科學的地位空前地高,還産生了科學主義。直到20世紀,由于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原因,科學技術尤其是科學主義受到了沖擊。從中世紀到文藝複興再到現代乃至後現代,西方文明基本上沒有斷裂,是以嚴格地說,他們對科學的态度隻有兩次轉變,而我們的文明從來就沒有斷過,對待科學和科學家的主流态度在短短一百多年内竟然有了三次(細分達五次)變化。
當然,所有的轉變往往以第一次、第二次的幅度為最大,之後的振幅就比較小。最近數十年西方文化界對科學技術的批判,遠不能(也不該)把科學和科學家“怎麼樣”:諾貝爾獎照發不誤,沒有一個科學家遭到布魯諾的厄運。我們也是,從1980年代科學的春天,到後來科學、科學家遭到一點冷落,以及現在的回升,畢竟不算大起大落,用股票的語言說,就是小幅回落(是以粗分下我們的後三次其實也可以合并為一次)。在五次細分式轉變中,我本人經曆的就有三次。
下面略微詳細地談一下這幾次變化的一些特點。
明星科學家簡史
曆史往往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然後慢慢回歸正常化;當達到另一個極端時,仍不能完全消除前一個極端的影響。比如我國科學家在上世紀70年代末一下子從臭老九變成香饽饽,地位是反彈了,但俗話說無知者無畏,陳景潤走紅的年代,過去遺留下來的盲目自信就暴露出來,一大群民科在隻有國中甚至國小學曆的情況下,個個躍躍欲試,鑽研哥德巴赫猜想或尺規作圖難題,屢敗屢戰。有的人宣稱自己解決了什麼猜想,有的則宣稱愛因斯坦、陳景潤是錯誤的(盡管不會再從政治上打壓了,但從科學上“批他們錯了”還是有的),打擾陳景潤們的為數不少。其實不止民科,即使直到1980年代,科學家傳記裡還要塞進大量現代中國科學家的名字,與牛頓、達爾文等并列。蘇聯也有這個“毛病”——我翻過他們寫的科學家傳記,本國科學家至少要占一半。
民科們隻知道現代科學最熟悉的幾個概念,健在的科學家中,也隻知道“明星科學家”。在中國,明星科學家大概出現于1980年代,也就是我讀中國小時,這是時代的需要和必然。在通訊、媒體無比發達的今天,通過自身宣傳及别人包裝,使得自己的言行(無論是否與自己的本行有關)為大衆所熟知的科學家,就是明星科學家,它是我們處在海量資訊中的時代特有的現象。
中國第一個明星科學家應該就是陳景潤吧(重新入中國籍的楊振甯算是今天的明星科學家)。陳景潤身處兩個時代,後一時代是一個轉型期,轉變是根本的,但仍留下前時代的烙印。人們形容陳景潤有着“醜小鴨”般的經曆。在國外,霍金不是第一個明星科學家,費曼也可以算是,甚至愛因斯坦也已經開始有了明星科學家的味道。明星科學家本身至少是傑出科學家,肚子裡沒貨色,靠瞎吹隻能騙不懂科學的人,騙不了行家,嘚瑟不久。
不得不承認,在巨量資訊中,明星科學家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比如一看到熟悉的科學家新作,我就會毫不猶豫去買),甚至會鼓舞學生走上科學研究的道路。霍金的成就不亞于陳景潤,殘疾程度又甚于張海迪(陳景潤身體也不好),他不成為國際級明星科學家才怪。生物學家道金斯、威爾遜等都算是明星科學家,霍金則是最出名、最典型的一位。絕大多數名人去世時,一般都是壽終正寝,且已離開公衆視線很久,是以大家看到報道時不會有多少感覺,霍金的情形比較特殊,因為他的身殘志堅,是以他的離去不像一次平常的死亡,而是一種象征性的、勵志精神的消逝,引起很多人内心的觸動。
然而,也正是作為明星科學家一哥的身份,霍金也常被拿來做比較,并引發一些新老問題的讨論:一是霍金與其他科學大師的比較;一是實用技術和目前看上去沒什麼用的理論的比較;還有就是明星與科學家的比較。我管它們叫“三大比較”。本節闡述前兩個比較,最後一個放在後面一節。
在曆史上,科學家一般分為三類(或三個級别),它們呈包含關系:
公衆科學家,就是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寫入中國小國文教科書的人物,不超過十個,這些人不僅開創了學科的方向,而且開創了時代,影響力遠超科學範圍,與文化、宗教等也有密切關系。在今天,公衆科學家基本上已經“絕迹”。
偉大科學家,公衆科學家也在此列,此外如拉瓦錫、開普勒、麥克斯韋、高斯、玻爾等,才智不低于公衆科學家,由于極大地推動了科學的進步,享有顯赫地位,但影響基本未超出科學範圍,知名度明顯減小。偉大科學家在今天也非常稀少。
傑出科學家,其實也包含上面兩類,主要是一般的諾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或名校院士、博導等,才智也未必低于上述兩類,但因曆史機遇等因素,沒有機會發現新的礦藏,隻能下功夫去挖掘,做出深入的成果。媒體關注度較小。
此外,衡量一個科學家,存在直接影響力、衍生影響力、個人學術功力的綜合評價。歐幾裡得、牛頓的直接影響力高于達爾文(以學校學習内容為準)。達爾文的衍生影響力很大,明顯超出歐拉、高斯,但在個人學術功力上,高斯、歐拉應該不亞于任何其他人。
霍金在理論實體方面的成就是第一流的,但也不是說他可以與愛因斯坦比肩。愛因斯坦、牛頓身處科學革命時期,有他們的幸運之處。是以拿霍金跟他們比較不是特别合适,應該把霍金與同時代的科學家相比。同時代的科學家甚至同時代的理論實體學家中,有不少成就不在霍金之下,不要說諾貝爾獎、菲爾茲獎得主,就是那些年輕的通路學者也不是“吃素的”。但是媒體不會去青睐他們,他們沒有什麼“傳奇”可言。
霍金一生的言行和傳奇,完全符合他作為明星科學家的特征。至于他在人工智能、溫室效應等方面的言論受重視,是一種光環效應。霍金在這方面的警告沒什麼特别過人的見解,但名人說話自有媒體在乎,甚至有很多話是别人說了算他頭上的。
至于理論和實用,也不能做簡單的比較。比如核磁共振技術,這項技術獲得了好幾項諾獎,你說重要不重要?醫學重要還是霍金理論重要?顯然,至少在目前,我們可以沒有霍金理論,但不能沒有醫學!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醫學主要解決的是人的壽命和健康問題,但人活着決不僅僅是為了健康地活着,人有多方面的精神追求。霍金等人的宇宙學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了人類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對于提升人類的見識和精神意義深遠,這又是核磁共振技術所不能做到的了,畢竟,任何一件發明或發現都不可能承擔一切價值。
媚雅:高于文化消費
在今天,打擾霍金的人肯定不多。
與陳景潤相比,霍金在人們心目中又是什麼位置呢?我的回答是,當然遠高于知識分子“臭老九”時代的陳景潤,但未必比得過“科學春天”的陳景潤。
不過,這仍是進步。
霍金在中國紅起來的時候,正是中國市場經濟開始發展之時,接受他的主體是65後至90後,他們腦子裡沒有批鬥、打倒這類概念。此外,自65後開始的一兩代人受的教育比較好,是以少有動不動就躍躍欲試的民科挑戰霍金。相比之下宣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或成功三等分任意角、發明永動機等多了去了,鬧了大笑話還不自知。
霍金的暢銷書“打了頭陣”。不可否認,霍金能夠曆史留名主要還是靠他的成就,其次是勵志的精神,最後才是科普書,但在普通人心目中這個順序恰好相反:先是看了科普書,再是了解到他殘疾,最後才是成就(大多數人搞不清楚)。
但這并不意味着霍金能夠像陳景潤一樣,成為大家的榜樣(盡管這種榜樣有負作用——無視差距,生産民科),然而,這說明社會已經開始離開另一個極端了,恰恰是一種進步。
自由社會既然以消費為主體,盡管比“批鬥”“打倒”要好多了,但從消費的角度看,也不大可能太尊敬消費對象(現代人自戀着呢!)。但人家霍金有成就擺在那裡啊!于是,有人就造了“媚雅”一詞,跟媚俗相反。當然在今天,消費總是基礎,其他科學家既然沒有被消費的可能,也就失去了被集體媚雅的基礎(但被少數人尊崇還是可能的)。
“文化消費”的概念大家不陌生,于丹就是典型。霍金的情形不同,他是真正的學問家,但《時間簡史》走的是完全的市場路線。霍金的名氣和影響力、收入都大大超出那些水準不亞于他的科學家,但我想其他人也不大會妒忌的。霍金使得科學更受關注,有什麼不好?霍金的成就究竟有多大,由時間來決定最公正,這也算是一種“曆史決定論”。
霍金雖不是人們膜拜的神,但也是大家集體媚雅的明星科學家,比起陳景潤,大家尊重他不在霍金之下,但對其專業又往往太不尊重了。此時有人跳出來說了,幹嗎媚雅呢?一竅不通卻在那裡瞎起哄!自己去搞懂霍金理論,就是對霍金最大的尊敬。這話說得過了,至少在今天,霍金的學術水準和一般公衆的差距之大是難以改變的。達到“精神共富”得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高度發展後,目前是肯定沒有辦法的。就這一點來說,那些不懂實體學卻喜歡《時間簡史》、認為霍金跟愛因斯坦一樣偉大的人的媚雅,是可以了解的。
《時間簡史》的可讀性還是比較強的,相比之下,科學元典叢書才真叫讀不下去,但這書也賣得挺好。我對“買書就是要讀”這句話不是百分百地贊成。在經濟能力允許的前提下可以買少許看大不懂的書放在家裡供着,這就是媚雅。你可以說媚雅是一種虛榮心作怪,也是一種廣義上的文化消費,但另一方面,它比批鬥、打倒要好很多,媚雅至少承認自己同專家的差距,比純文化消費也要高一點。
當我們批鬥、打倒一個人的時候,肯定是采取俯視的姿勢;科學的春天發生“反彈”——近乎直角的仰視;文化消費呢,基本處于平視的姿勢;而媚雅呢,帶有一點角度的仰視。人們對于大科學家的态度總體上是越發正确,但仍有欠缺。
不過,我們如今也就隻能走到媚雅這一步了!霍金的離去,就像博爾特離開了田徑賽場,科技界很長一段時間将有些沉寂,除非又迎來一次革命性突破,或者出現一位傳奇人物。
西方的學院派和市場其實也一直存在對立。無論《哈利·波特》怎麼大賣,羅琳這輩子估計甭想得諾獎,如果能得早就得了。問題在于,人家的這種對立似乎保持着比較好的張力。我們國家因為窮了幾千年,一旦開放,很多思想觀念都不成熟,是以就會出現一邊憤世嫉俗、一邊媚俗等比較極端的心态。陳景潤廣為人知後,也有兩種極端的聲音,一種是把他捧上天,說他刻苦鑽研,為國争光;一種是笑他傻,不懂生活,隻會研究毫無用處的數學題。現在的情形好多了,大家都比較寬容,幾乎沒有人盯着問霍金的理論“有什麼用”。
特别有意思的是,科學大牛的價值觀竟然感染了一些看上去三觀似乎完全背道而馳的企業家,如稻盛和夫、邵逸夫、紮克伯格、米爾納、馬雲、馬化騰、任正非等,他們不惜出重金任用、獎勵科學家,包括霍金在内。這正展現了企業家的眼光和見識,他們也看出市場的缺陷——難以對原創性科學成就進行評價。有人可能會說,那些企業家獎勵科學家,不也是希望更多的科學成就更好地轉化為商業價值,話雖有理,但是别忘了,有很多大獎是獎給純理論研究的。
其實,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尊崇或忽視,以及學院派和市場的沖突,都來源于西方。中國在傳統意義上并沒有科學家,有的是能工巧匠,不可能得到尊崇;此外,也沒有成熟的市場。是以從這層意義上說,科學家的日子過得不如明星,有人不滿意,對具體個體來說是理性的缺乏,對社會總體來說卻不無意義。對于遠離市場、沒有得到好處的人,抱怨是必然的,不抱怨倒反而有點不正常了。如果一個人發自情緒的抱怨,在理智上又能坦然接受,這不是不可以,但有點奇怪。
所幸市場并沒有徹底吞沒學院派和文化人,而是保持了必要張力,給了他們生存的空間。不過就總體來說,市場的力量還是太大(市場的“弄潮兒”企業家獎勵純理論科學家,看上去正是跟市場規律背道而馳的做法),人們努力的效果還是不夠的。如果市場一統天下,物質化内卷化嚴重,那麼霍金隻能被文化消費。媚雅也許可以看成是市場和精神文化價值沖突、整合的結果。
霍金熱離基礎科學普遍受重視還有多遠?
近30年來,霍金一直很熱,但霍金熱就真能說明基礎科學受到重視嗎?
比較合理的回答是:不太能,但熱比不熱好,媚雅比不媚雅好,比純文化消費好。如果要展望未來,就必須認識媚雅的不足了。
霍金去世後,看看都是哪些人跳出來公開哀悼:企業界、技術界、媒體,可是數學和實體學界呢?相對沉默。人家隻是把霍金看成是當代傑出實體學家的一員。而在中國這樣曾經盛行崇拜的國度,較易引起大家的“狂哀”。在歐美國家,即便諾獎得主平時也沒多少人搭理,一到中國就被捧上天。不過我覺得這是因為中國目前諾獎太少,以後也會變得越來越理性的。
目前,我們仍需要明星科學家——如果有比沒有好的話。相比耍嘴皮子和寫作的,世上許多發明家都是默默無聞的,但他們或許更為重要,我們在享受生活便利的同時,得時常懷有感恩之心。我們需要霍金,更需要千百個健康的霍金以及更多的宣傳。
如果說愛因斯坦是現代科學家的代表,那麼霍金就是當代科學家、後現代科學家的代表。60後70後們總覺得愛因斯坦真有思想,但世界終究隻是集中于接受他的科學成就,沒怎麼理會他的社會理想,這必有深刻原因。愛因斯坦的價值觀也許坐了柏拉圖主義的“末班車”(至少他知道自己當不了政治家)?柏拉圖在今天的處境跟孔夫子有點像,人們已将其從神壇上請下,甚至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他,另一方面,他的影響力其實還不小,甚至可能永不消失。具體地說,人們普遍認為,20世紀世界大戰就是圍繞着包括精英主義在内的一場決戰,此後世界進入後現代主義。科學技術依然發達,但柏拉圖主義失寵了。也許還要過50年、100年,我們才能看清這場深刻的變革究竟意味着什麼,其中人工智能是最大的變數。
當我第一次知道霍金晚年關心人工智能時頗感奇怪,我想很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有這樣的疑問:人工智能不是霍金的專業,霍金也無須依靠人工智能來蹭熱度,那霍金是為了什麼呢?也許這樣一個回答是比較貼切的:霍金是一位關心人類前途命運的學者。我覺得用一個詞來形容十分合适,那就是“文化自覺”,這是每個時代大科學家的思考方式中從來就隐含着的一種基因。
我也相信,這次不一樣——科學家和基礎科學再次受到重視,但那一定不是我們1980年代的樣子,也不是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樣子。雖說媚雅仍有不足,那比它還要好的狀态是什麼呢?這個我實在想不出來,隻能留給未來去回答。真的,當我一想到未來時,因為一無所知,總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感覺:有點困惑,但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