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作者的著作《亞文化批評》(『 』,2021),内容有修改和補充。本文原刊于南韓遊戲網刊Game Generation(https://gamegeneration.or.kr/board/post/view?pageNum=1&match=id: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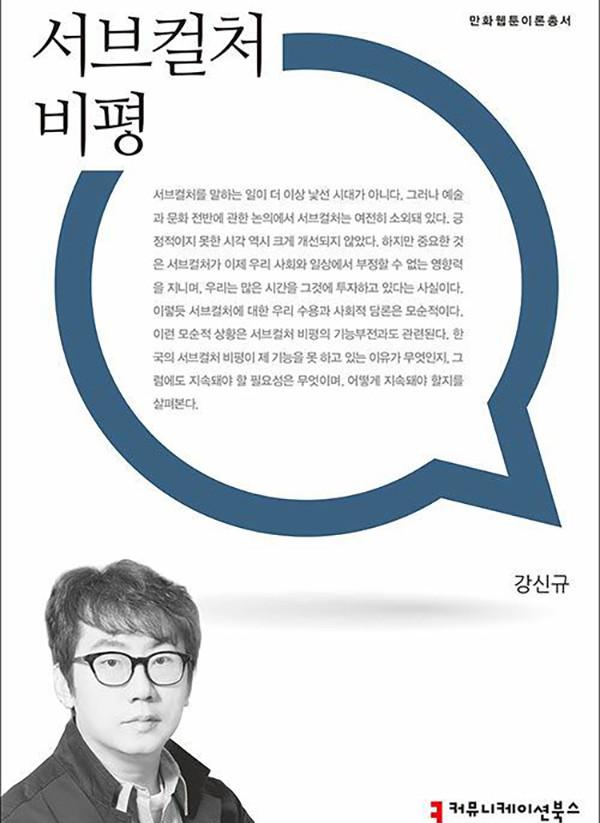
姜信奎《亞文化批評》
1.世界與南韓最早的遊戲雜志
世界最早的遊戲雜志是1981年發行于英國的《電腦與視訊遊戲》(Computer & Video Games: CVG),該雜志自2004年開始僅在網上發行,2015年關閉網站,變身為gamesradar+(www.gamesradar.com)。截止目前,gamesradar+依然在為玩家提供受期待的作品和新遊戲的試玩體驗、行業新聞,以及觀點犀利的遊戲批評等文章。
《CVG》(左)和《Gamesradar+》(右)
遊戲雜志首次在南韓亮相大概是十年後,也就是1990年代初期。與1980年代電腦的普及時期相吻合。遊戲雜志介紹了将任天堂紅白機國産化的現代COMBOY( )遊戲機。之後三星電子引進世嘉(Sega)的16位遊戲機Mega Drive,并發售其南韓版本“超級COMBOY”( )。随着人們對主機遊戲關注的急劇升溫,專門的遊戲雜志應運而生。
《遊戲世界》創刊号
南韓最早的遊戲雜志是1990年8月發行的《遊戲世界》( )(趙基炫,2012,58頁)。随着《遊戲新聞》( ,1991),《遊戲通》( ,1992),《遊戲冠軍》( ,1992),《遊戲情報》( ,1993)等相繼發行,遊戲雜志之間的大戰拉開序幕,展開激烈角逐。當時玩家最需要的資訊是新遊戲介紹、發行時間和遊戲攻略,但遊戲雜志卻将重點放在了突出遊戲的正面性和文化性格等方面,表現出對遊戲認知轉換的重視。
遊戲雜志還招募撰寫遊戲分析的編輯,并刊登他們的文章(1992年《遊戲世界》,1993年《遊戲情報》等);翻譯美國和日本遊戲雜志的報道(1994年《遊戲頻道》等);連載人們關于遊戲态度的文章(1996年樸炳浩在《京鄉新聞》的連載文章,1999年樸尚宇( )在《電影21》的連載文章)等。類似批評和批評的早期形态的多種嘗試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2.熱衷于附贈CD光牒的電腦遊戲雜志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随着電腦遊戲迅速發展,大部分遊戲雜志也将重點放在電腦遊戲上。當時遊戲雜志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随書附贈(bundle)CD光牒。早期附贈CD光牒主要是為了處理過時的遊戲CD光牒庫存。沒想到這一舉動反而受到玩家的強烈歡迎,進一步影響了整個行業的發展,最後附贈CD光牒成為遊戲雜志銷量的決定性因素。随着競争愈演愈烈,雜志社附贈的CD光牒也從以前的以經典遊戲為主逐漸變為提供新遊戲。1980年代遊戲雜志主要通過提供遊戲資訊和攻略來維系讀者,而1990年代遊戲雜志則憑借附贈CD光牒吸引了大批讀者。
雜志社競相引進遊戲新作,變成了過度競争,導緻購買遊戲CD光牒的費用嚴重超支,給雜志社帶來巨大負擔。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電腦遊戲盜版現象橫行,以及網絡環境的發達和網絡遊戲的出現,電腦遊戲市場開始走下坡路,遊戲雜志迎來了嚴峻的考驗( ,2012.1.4)。
3.從紙質雜志到電子雜志
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持續了約10年曆史的遊戲雜志在進入2000年代後,緊随視訊遊戲和電腦遊戲産業進入了衰退期。遊戲雜志失去了生存的根基,遊戲産業卻獲得了新的增長動力,即網絡遊戲興起。遊戲雜志也順勢變為以網絡遊戲為主要内容的雜志。與專門的遊戲批評相比,這些雜志的遊戲批評大多如蜻蜓點水。當網絡論壇出現後,以提供遊戲資訊、攻略和附贈CD光牒為主要賣點的紙質雜志逐漸被人遺忘,相繼停刊。
網際網路的發展給傳統的雜志媒體帶來了挫折與考驗,但也為玩家加速資訊共享和傳遞提供了基礎。當然,對于玩家來說,從浩如煙海的資訊海洋中迅速找到自己想要的資訊并不容易,而且玩家對更專業化資訊的需求也很難得到滿足。這種情況促使系統使用大量遊戲資訊的管道誕生,即電子雜志應運而生( ,2021.1.4)。
截至2021年6月,《GAMER’Z》( )是唯一一家傳統線下出版的遊戲雜志。除此以外,還有許多電子雜志,如《INVEN》( )、《GameMeca》( )、《THIS IS GAME》( )、《FOMOS》( )、《遊戲北韓》( )、《GAME FOCUS》( )、《DAILY GAME》( )、《gameabout》( )、《遊戲東亞》( )、《傾向遊戲》( )、《The Games》( )等。然而無論是《GAMER’Z》這一紙質雜志,還是其他電子雜志,内容都隻側重于為玩家提供遊戲測評和攻略等資訊,而非專業化的批評。
4.為拓展遊戲批評的種種嘗試
反而是來自其他領域的視角試圖更加仔細地考察遊戲的内部和外部,盡管其專業性和穩定性很難得到保障。不過這樣的嘗試并沒有持續下去。報紙、電影雜志或其它大衆文化雜志、電腦雜志等雖然經常提及遊戲批評,但大部分情況隻是短篇的策劃。民間财團遊戲文化财團自2012年3月起發行《遊戲文化》( )月報,聘請業内和學界的編輯發表高品質的遊戲相關文章和批評,然而沒能持續多長時間,自2012年12月最後一刊發行後,該雜志宣布停刊。
另外,回顧遊戲批評的軌迹時,不得不提到“遊戲批評征集大賽”( )。為增進人們對遊戲的人文、社會學關注,南韓從2008年起設立“遊戲批評獎”( )。該活動以提高文化、學術價值為宗旨,由文化體育觀光部主辦,南韓文化産業振興院( )、NHN集團、TheGames共同協辦。
全京蘭( ,2013)對2008年到2012年在“遊戲批評征集大賽”中的30篇獲獎文章進行了分析,認為獲獎文章展現了人們對遊戲各個方面的關注,但領域和切入方式有相當大的局限性。獲獎文章沒有從遊戲的内容和形式特征、沒有以遊戲玩法、遊戲結構及遊戲世界等為中心進行批評,而是采用了傳統的文化分析理論和方法論,對于了解各種遊戲現象存在局限性。不過該賽事也有一定積極意義,它是南韓為發掘業餘遊戲批評家并擴大遊戲批評影響範圍的首次嘗試。“遊戲批評征集大賽”自2012年第5屆後停辦。
第1屆遊戲批評征集大賽海報
批評家發表的單行本也有重要意義。如樸尚宇的《遊戲,變革世界的力量》(『 , 』,2000)與《當遊戲走來時》(『 』,2005),李尚宇( )的《遊戲,玩家,競技:用人文學解讀遊戲》(『 , , : 』,2012),李京赫( )的《遊戲,觀察世界的又一扇窗》(『 , 』,2016),人文學合作社( )成員的《81年生馬裡奧:記憶中的遊戲是如何學習人情世故的?》(『81 : ?』,2017)等代表作。這些作品的優點在于,通過共同的人文和社會科學,以一種相對新穎和多角度的方式探尋我們日常生活與社會、文化中遊戲的意義。然而這些批評沒有互相參考,卻都以正規批評自居,大多停留在對遊戲人文學的基礎讨論層面(特别是關于叙述學Narratology和遊戲學Ludology),觀點大多重複類似,之後也未持續進行更深層次地挖掘,這一點多少令人遺憾。
(左起)樸尚宇,李尚宇,李京赫,人文學合作社成員的遊戲批評
遊戲批評是現在進行時,讨論其成果為時尚早,但也有值得關注的嘗試。李京赫( )自2014年11月開始,在媒體批評雜志《MediaUS》( )上連載遊戲批評“Play the Game”,之後通過各大網絡新聞、遊戲公司部落格、雜志甚至《國防日報》( )等媒體刊發自己的遊戲批評。從遊戲文本到南韓遊戲文化文物級别的遊戲廳和電子競技(e-Sports),從遊戲産業到玩法/玩家,從關于遊戲的負面讨論到遊戲文本中蘊含的社會問題,他探索的範圍極為廣泛。截止2021年6月,幾乎沒有批評家能做到這一點,他的表現備受矚目。
5.遊戲批評存在的問題
南韓遊戲批評存在的外部問題有以下幾點。
首先,随着政府對遊戲監管的加強和遊戲負面言論的傳播擴散導緻遊戲行業萎縮,遊戲批評發展的基礎薄弱。強有力的監管和負面言論使遊戲變成“壞事”,人們認為對于遊戲“沒有必要認真讨論”。
其次,盡管市面上有許多遊戲雜志,但南韓沒有人對遊戲進行專業性的批評。這一點與海外的情況截然不同。例如英國的《PC Gamer》(www.pcgamer.com)與美國的《Computer Gaming World》(computergamingworld.com)等遊戲雜志,比起簡單的遊戲點評或攻略,更加注重向讀者提供深層次的資訊和批評。Kotaku(kotaku.com)是認真反思與思考遊戲的網絡媒體;刊登開發者和研究者對遊戲制作宗旨、遊戲批評、研究結果等内容的gamasutra(www.gamasutra.com)等則是專業的遊戲批評媒體。
當然,出現這種差異也是因為南韓與國外對遊戲的社會性認知、玩家嗜好以及遊戲批評成長土壤的不同。但是,南韓遊戲雜志涉及遊戲測評和攻略的版面過多,難免令人懷疑它們是否淪落為遊戲推廣公司和遊戲公司等廣告金主的宣傳工具。
内在層面的問題在于,由于遊戲所獨具的文本特征,人們難以對其進行批評。遊戲由符号和叙事組成,這一點與其他文化類型相似。但是遊戲包含獨特的享受結構,與其他文化類型存在明顯差異。這種享受結構也能影響文本本身。與其他文化類型不同,提前制作好的遊戲在玩家參與之前,其文本仍處于不完整的狀态。玩家是參與不完整的遊戲文本創作,并與遊戲互相作用的主體。隻有玩家參與,才能使遊戲成為完整的文本。
遊戲中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之間的界限是以變得模糊不清。遊戲文本不是接受,而是參與。這意味着,遊戲不僅是算法的展現,還是讓玩家體驗故事及虛拟情境的叙事環境(姜信奎,2016)。為此,遊戲批評的對象不應隻是文本本身,還應該探讨文本為玩家提供了什麼樣的經驗,玩家形成的經驗對下一次遊戲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等( ,2012.12.12)内容。
不僅如此,不同平台與類型的遊戲所具備的特征也完全不同。是以在批評遊戲時,人們很難将多種觀點和方式糅為一體。别的文化類型是“看”了才能知道,而遊戲是“玩”了才能知道。即使是遊戲專家或高水準玩家,也幾乎不可能去批評一個他從未接觸過的遊戲。玩遊戲通常需要志同道合的玩伴,是以根據遊戲類型、平台等的不同,玩家間會形成享受共同體。
玩家間“交流經驗”的過程會讓他們不自覺共享和評價遊戲内容,并直接反映到遊戲的玩法中。例如“玩”遊戲的玩家“接觸到”别人的玩法或相關資訊後,把接觸的玩法運用到“玩”遊戲中( · ,2011)。直接享受這些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多的資訊和經驗。而不在享受共同體之内,或沒有深入體驗遊戲的批評家很難真正地了解遊戲。
6.遊戲批評的條件
所謂“遊戲批評”,指的是分析和評價遊戲價值的工作。此時“批評”與現有的對文學、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的批評中使用的概念無本質差別。但就像每個領域的批評皆有其特點一樣,遊戲批評與其他領域的批評也不盡相同。因為批評的對象和條件存在差異。為此,考察遊戲批評的條件時,必須同時考慮批評的一般條件和反映遊戲差異性特征的條件。
另外,批評的條件并非一成不變的固定存在,而是根據批評對象的形态特征和批評所要求的作用變化構成。當然,不同批評者對批評條件的認識有所不同。但人們可以嘗試找到批評條件的共同點進行批評。
1)批評的一般條件
批評一般需要批評主體(批評家)、批評對象(廣義的作品)、創作主體(制作人/創作者/作家)、接受主體(享受者/接受者/讀者)四個要素。批評能對創作主體起到回報作用,引導接受主體是否選擇批評對象及選擇方法。批評主體有機會通過批評來表達自己對批評對象的立場。
如果說批評主體/對象,創作/接受主體是構成批評的基本要素,那麼批評的條件有以下三點。第一,批評必須超出讀後感的水準,是以必須建立相應體系。第二,成為批評家需要公認的程式。第三,需要專門刊發批評的學術雜志、日報、雜志、網絡雜志等媒體。媒體應當保證批評的穩定性和信賴性( · · · ,2015.5.8)。這三個條件分别涉及批評的專業性、穩定性和持續性。總而言之,批評可說是“批評主體以值得信賴的媒體為發表陣地,系統分析批評對象的有關事宜并進行評價的專業性工作”。
批評最重要的一點是,它超越了批評對象現有的可能性,通過不斷的提問、尋找答案,傳達着批評對象對我們人生有何意義,以及它所具有的社會内涵。遊戲批評也是如此。我們不應該隻局限于遊戲帶來的快樂,而是将視線放在遊戲的社會功能和遊戲未來的可能性,并通過這些解讀日常的變化和時代潮流的變遷。
總而言之,批評就是解讀批評對象的成就,并将解讀的認識公之于衆。為此需要以下幾個前提。首先,營造真誠探讨和研究遊戲的批判性風氣。其次,支援遊戲和遊戲批評的系統化。最後,為了能夠了解個人或社會的遊戲體驗,提供批判性工具、注釋、批評。
2)變化的規律與遊戲批評
但是,批評的一般條件與遊戲批評面臨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尤其在南韓,遊戲批評條件寬松,還達不到現有藝術、文化類型一樣的固定形态。當然,無論批評對象是什麼,本質而言都要靈活,不斷變化。如果說遊戲批評生存的基礎是遊戲和社會,那麼它必然會随着遊戲和社會的變化産生波動。遊戲的定義也在不斷重組。元宇宙(metaverse)時代的遊戲必然與網絡遊戲萌芽前的遊戲不同。
與現有藝術或文化類型相比,遊戲文化便利性( )高、封閉性強,難以形成專業系統的批評。遊戲的享受度與玩家的個人經驗高度關聯,這也是難以形成遊戲批評體系的一大制約要素。但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遊戲批評并不是不存在,反而遍地都是。制度化的批評顯得微不足道,是因為制度外的批評熱情超乎人們的想象。如果不考慮從傳統觀點進行的制度化批評,遊戲批評簡直可以用“過熱”來形容。在部落格、論壇、社交媒體等網絡空間,遊戲批評随處可見。玩家通過各種平台和裝置累積遊戲經驗,成立讨論遊戲的網絡社群,并擁有了專家級的資訊和知識。這為玩家成為準批評家奠定了基礎,但也導緻傳統的批評體系難以形成,令每一位玩家都滿意。
通過積極的享有=批評,可以拓寬批評的基礎或使批評變得民主化。但另一方面,這種情況會降低遊戲批評的水準,并模糊批評本身。如果說現有的藝術、文化題材的批評界已經成為制度化的專業批評領域和以網絡為中心新興的業餘批評領域之間沖突、關系密切交織的活躍空間,那麼本來就因不完善的制度化批評領域而定位模糊的遊戲批評,其真實面目将變得更加模糊。
而這種現象與遊戲批評的條件、作用等根本性問題息息相關。現有的批評概念無法運用在這種現象上。那麼建立一個專門的批評體系,是否就能夠成為遊戲讨論的發起主體,發揮積極主動性影響介入遊戲的發展呢?如果沒有制度化,批評有可能性嗎?對于制度化中所找尋不到的陌生想象力,是否可以通過批評的民主化進一步進行挖掘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首先對于那些在沒有制度化的批評中出現的“沒有中心的周邊”批評,應該重新定義其規則條件。也就是說,在影響批評場的變化中,與其辨識批評與非批評,不如通過創造新的條件擴大批評的外延。
遊戲玩家應擺脫被動消費批評的角色,通過網絡主動撰寫、釋出、共享批評,成為新的批評主體。他們發表批評的網絡空間,是讀者閱讀批評并發表感想的全新且充滿活力的批評空間。但是,問題在于如何從他們的文章中界定哪一部分屬于批評。
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進階/好”的批評和“低級/壞”的批評。正如傳統批評所追求的,批評面向的對象不隻是進階讀者。考慮到遊戲的特性和玩家,人們勢必要修改或擴大傳統批評的概念。提出明确的标準和範圍不再是專家的特權。遊戲批評具有不斷變化的特性,并出現在批評主體和讀者之間的沖突統一中。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堅守批評原本的目的和作用。不然批評就沒有了存在的理由。( ,2016)。
7.遊戲批評的發展方向
那麼應如何設定遊戲批評的發展方向呢?
第一,發掘創造性的理論和方法論。雖然尋找隻針對遊戲批評的理論和方法論并非易事,但我們必須持續探索遊戲所處的現實,以及能夠觸及社會脈絡的批評理論和方法論。批評對象不同,批評的語言也要随之改變。隻有通過遊戲所具有的固有屬性來建構批評的身份和作用,才能保證遊戲批評的可辨識性。
對于精神分析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新批評、讀者反應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構批評、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酷兒批評等既可以豐富文本又能深入觀察文本的現有批評理論和方法論,人們需要探讨和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将它們整合到遊戲美學中。另外,如何根據遊戲平台和類型将批評細化、專業化,鞏固批評的整體架構,也是值得人們考慮的事情。在媒介變型(media transformation)與媒介融合(media mix)日漸多樣化的形勢下,挖掘新的批評方式與形式顯得愈發重要。
第二,重新定義批評的作用。批評經常被指缺乏自我意識,或偏向解說、祝詞。原因在于沒有發揮批評的作用。批評不是吸收或透射批評對象,而是與批判性的視線一起反映或反射到外界。換句話說,批評的主要作用不是“吸收”,而是“回報”。批評的效果就是通過對批評主體和批判對象反複進行的回報,最終實作與批評主體的協同進化(coevolution)。
但是,遊戲批評的作用有必要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對特定文本進行缜密的解讀時,應當更仔細地審視行為者在批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挑戰和應戰的方向性。這意味着,遊戲批評在探索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形成的文化變化的同時,應當制定具體的對策,以應對靈活變化的文本的确立,文本在社會性上的應用,以及遊戲産業所面臨的變化,并培養讀懂這些問題的能力。
隻要批評滿足于次于寫作的地位,就絕不會發生批評引領批評對象的事情。遊戲批評應當超越文本,對沒有文本化的現實(當然是在與遊戲的關系中)産生影響。最終遊戲批評的作用是,指出應該解決的問題,檢討遊戲社會和生活,探讨我們如何與遊戲共存。
第三,無論傳統還是非傳統,現在對于批評的讨論需要的是對“完全”整合的不可能性或者不必要性的認識。批評與非批評,批評空間與非批評空間,批評家與非批評家之間的界限已然模糊。專家水準的玩家,具有專家所不具備的經驗的玩家,引發激烈争議的批評空間,随處可見的超越現有批評定義的批評。對這些進行界限分明的劃線已毫無意義。遊戲批評的前進方向應建立在對這一點的認識上面,由此開始向前發展( ,2021)。
但是,問題在于遊戲批評中存在好的批評和不好的批評。而不會遊戲批評,确切來說是不會寫好的批評。每個人都想寫好批評,但一開始就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一開始就想寫好批評會引發許多問題。批評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如果不注重創造的樂趣,隻貪圖結果,就會禁不住誘惑去模仿别人,或者單純地羅列學到的知識,甚至弄虛作假。擁有豐富的遊戲經驗并不能保證你一定會寫出好的批評。想要寫好批評,不管是傳統的批評還是新式的批評,首先必須具備自成一套的體系和專業性。
人們有必要摒棄對其他批評無謂的冷嘲熱諷。既然批評的總體性的整合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那麼人們就應該将重點放在接受其他批評上面(無論何時,無論是誰的批評),通過他人的批評反思自己的觀點是否妥當,努力為他人和自己的批評增添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