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文学爱好者那里,还是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那里,阿城都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坛大神级别的名字。
关于阿城,“江湖”上总有很多传说。形容他最多的一个词儿,是仙风道骨,如果你见过阿城先生,会觉得这个形容倒也贴切。如今,仙风道骨的阿城先生即将推出《阿城文集》,这也是阿城作品首次结集出版。其中包括最为著名的《棋王 树王 孩子王》,也有《遍地风流》、《威尼斯日记》、《闲话闲说》、《常识与通识》,还包括最新的两部散文随笔与谈话集《脱腔》和《文化不是味精》。
昨天晚上,《阿城文集》举行了新书发布晚宴,出版方邀请了众多文化学者、作家共同出席。阿城先生作为主角儿自然不会缺席,但席间一直沉默,只静听大家对他的作品发表各种感言。但在晚宴最后,阿城先生似乎来了点儿兴致,跟大家谈了许多他对小说、下乡岁月、写作生涯的诸多看法。书评君根据阿城先生的现场发言,整理了发言实录,供大家参考。
谈得最多,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阿城先生谈到的“不合作”的态度。人与权力,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任何一个人,哪怕无比主流、政治正确,也总会遇到与权力冲突的时刻,面对这样的时刻,一个渺小的个人,能够做些什么来保持自己的存在和观念?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生于北京,原籍重庆江津。一般被认为是当代寻根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家。除小说外,还创作和改编多部剧本。代表作品有《棋王》、《树王》、《孩子王》等。
1
谈《孩子王》:
它说的是“不合作”
有不少朋友问,你写《孩子王》是干什么?其实不干什么,都是当年知青传的东西。当年大家赶集,互相都会问,你那儿有什么(可以读)?人家回说我这儿有本日记。那也要拿来看看。大家有一种阅读饥渴,没有书看。所以当时很多人会写东西,写出来大家这么传来传去地看。跟我经验差不多的人,他看《孩子王》,他会看懂。不是的呢,就根本看不到。
它非常简单,就是和谁谁谁不合作。你叫我来,我就说我这一套。你说我这一套不行,你叫我滚蛋,那我就滚蛋。我不说我是冤枉的,你凭什么叫我滚蛋。没有(争论)这些东西。就是跟你不合作。在文革的时候,这是能够做到的,又安全、又保持自己的一个方式。不合作的人看这小说呢,就觉得你写最后这人笑了,这个好。咱们不是臊眉耷眼地走的,咱们是很有信心地走的。
现在的90后,将来的00后,他们难道不会碰到和主流不合作的时候吗?当然有,这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这个主题,人类和权力的主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不是爱情。爱情也是,但没有这么单独。因此它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合作的主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孩子王》已经成了古书了,但它还是留下了一点,就是你对主流权力,你自己能够选择什么。
2
谈《树王》:
很多联系用逻辑说不清楚
《树王》这个东西呢,本来在美国的时候,他们说想改成动画电影。后来有人挺鸡贼的,说:嘿,你不应该把小说给他们看。我说小说出版了就是谁买谁看啊。他说那个“阿凡达”,每个山头上有棵树,这是抄你的。我说这不是,是我抄云南的。云南就是这样,他不管怎么砍,一定要留一棵树。如果不留这棵树,人就不稳定,就觉得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我姥姥家是白洋淀的,文革的时候,那边的地头上都有个龛,很小。以前种地的时候会拜土地神,破四旧的时候就都给拆了。如果这个龛没了,这一带的人或者这个村的人心里就会发生变化。其实原来有这个龛的时候,你可能根本不会理它,但是一旦它没了,你心理就不踏实了,不稳定了。
为什么?不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不是我们都能说得那么清楚的一个逻辑关系。你把整个树晃动,瓦块啊这些会掉下来,最后柱子一倒。现在说什么要重建这个,重建那个,不可能了。重建东西都是要打地基的。没有地基,谁敢盖房,不是找塌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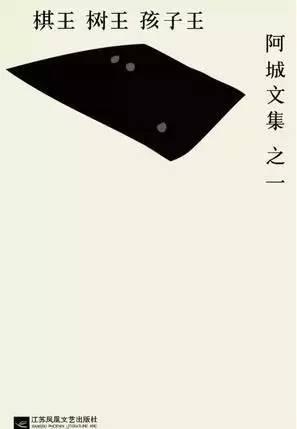
新版《阿城文集》中的《棋王 树王 孩子王》封面
3人在生活里都是“百科全书”
说一个人是“百科全书”,当然是对一个人的奉承了,我知道是个好意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周围的长辈呢,他们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怎么现在一下这种百科全书式的人没有了?这个是应该研究的问题,而不是谁现在是百科全书。
你去看以前那里院儿,有人在弹古琴,外院有个小孩,在那哇哇地哭。老头子“哐”把古琴撂下,说给他刮刮痧。他知道这个小孩哭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他。如果外头的阿姨说不会刮,老头就站起来自个儿去刮。古琴和刮痧,搭吗?不搭。如果是一个古琴的专业书,和刮痧的专业书,这俩书不搭。但是人在生活中,是搭的。你说你在生活中就只会干一件事儿吗?不会的。所以“百搭”我从小觉得是个正常的状态。
你要是想生存下去的话,你就得趁早多学一些东西。你不知道将来哪些东西能用上。我当时下乡了,还想着怎么离开这儿。我就去学烹调,我是有执照的厨子。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少一根弦。做了厨子之后,没有人要我。因为我出身不好,出身不好的人不能做厨子,怕下毒。学成了之后才想到这个。
所以生活一定是百搭的。这种百搭如果搭好了,就会被称作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笑)但其实,谁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些知道很多事情的人为什么没有了,这些人在我小的时候都有。
4
谈古董家具:
包浆这个词儿是沉渣泛起
我小时候出身不好,不能到街上去欢迎总统啊这些人物。每当有游行的时候,老师就念单子。我们班上有五六个同学不能去。我们几个就比其他能去的同学多了很多时间。我们当时学校一出校门就是一个琉璃厂。里头有好些老伙计,逮到人就喜欢跟你讲些瓷器知识。我们去了之后,老伙计们就跟逮到宝似的。他们会把你当人看,你到了,给你把凳子坐着,给你沏上水。这是成人的待遇。你翻书的时候,只要往上看一眼,他们就说,你要哪本儿?他去帮你够。后来到了九几年回来的时候,发现沉渣泛起,什么包浆啊,大开门儿啊,这些词儿又出现了。包浆现在说错了,伙计早就说过了,包浆是里面渗出来的树液,是里面渗出来的东西。外头加上去的,那叫脏东西,要把它洗掉。现在不是,上面的东西里里外外,什么都不管,都说是包浆。
我以前跟木匠学手艺。一般师傅开始都要给徒弟个下马威,不然他不老实。为什么说要给师娘端尿盆子,你能端得了师娘的尿盆子。行,你做人可以忍。师傅说,你把这凳子给拆了。我想肯定就是拿斧子往外打呗。结果打不动,才发现里面是隼。这个隼很复杂,你越摇这个椅子越结实。中国的老椅子不怕摇。越摇越结实。现在新的洋凳子你老翘着腿坐,有一天会散掉,因为里面没有隼。拆半天拆不开,师傅就得意了,说都念到高中了,连个椅子都不会拆。
从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中国椅子的结构。一套是佛教的,就是狮子腿,是由佛教来的。以前是罗汉啊,做的狮子腿的椅子,这是印度那边传过来的。它的发明者是伊朗人。狮子腿往东来就是咱们的明式家具,往西去到英国就是他们的贵族家具。所以狮子腿文化的扩散面积非常大。中国自己的东西是房屋结构,这个结构我们在《韩熙载夜宴图》里看到过。宋代的时候家具的隼是长出来的。为什么是长出来的?古时候比如说我们下午去南山去喝个茶,古人就把凳子拆了,拆了就扛着拿到南山上去。什么都能拆。到了南山再把这凳子装起来,坐下。所以宋代、明代的家具是能拆装的。到清代的时候,能拆的就比较少了。所以能拆的家具,能拆了再兜起来的家具是好家具。要投资就投资这样的家具。(笑)
新版《阿城文集》中的《常识与通识》封面
5
“你不是主流,
但你一定常常碰到主流”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套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书,房龙历史、房龙地理。我记得在房龙历史这本书的序言里头,房龙写到拿破仑,很多人骂拿破仑。说他恢复帝制啊,背叛法国大革命啊,但是房龙写到,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写文章,突然街上传来铜喇叭声,我出门一看,原来街上拿破仑的军队在招兵。那我会毫不犹豫把笔扔到桌子上,跑去参加拿破仑的军队。
这里面有一个差别是什么?是什么最吸引人。小孩子当然要做最吸引你的事。第二个是,他这个序言里已经说了,说拿破仑有很多问题,这个实际上就是说的政治正确。但是我一听到小喇叭,我根本不管政治正确不正确,我就要跟他们骂的这个人的军队走。这个给我触动很大。房龙的历史、地理可能写得过时了,但是他的精神(还在)。他也没递给谁,是我接过来了。他让我想到人跟主流的关系。
当然,这里面有我自己的东西。就是说,我不在主流里。由于家里政治的变故,你不是主流的。你不是主流的人,但是你常常碰到主流啊。包括政治课上你怎么背那些东西。按说这个简单,就是你把那些条目背下来,放到答案里去。但是这里面实际上是有政治歧视,而不只是你技术的问题。他就不相信你技术了。所以你跟主流有一个(冲突)。你会找出什么东西让我能够,给我一点儿养料,给我一点儿思维,让我怎么样跟主流相对。其实就是不合作。这个东西说起来也是把我害了,我就比较喜欢宅,像这样大老远跑到这儿来,跟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见面,不是我的性格,(笑)但是出版的人要赚钱嘛。
本文为独家文章,根据阿城现场发言整理。实录整理:新京报记者 张婷,编辑:走走,图片来自于网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