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孔子、墨子和老子这三位圣人都是尊崇的,但各有侧重,在他的求学时期、革命运动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倾向。而他的革命实践,更多地受到了墨家“兴天下之利”而刻苦自律、苦行救世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影响。他对老子和墨子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但对于孔子,则是早期崇拜,后来批判地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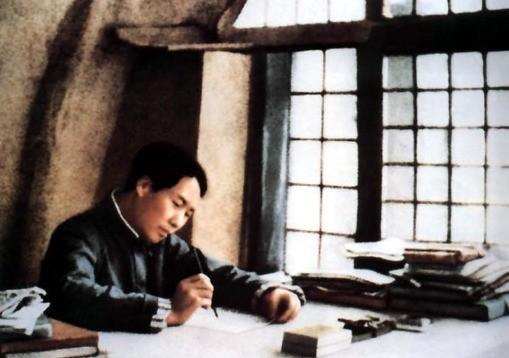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毛泽东常读的《老子》书有十几种</h1>
毛泽东外出视察,总会带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为毛主席管理图书的逄先知先生在大事记上记载:毛主席外出点名要带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人民网·毛泽东想读常读的书籍》)。
毛泽东重视对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他读过的老子版本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的《老子今译》,杨柳桥的《老子译话》,陈伯达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晚年视力下降后,又把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打印成大号字阅读。
1974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后,也是印成大字本来阅读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曾约谈任继愈,对他说:对于宗教问题要开展研究。一个好几百人的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道教呢?包括佛教、基督教,都要研究。
毛泽东赞成任继愈先生对孔子的评价,说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他不赞成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以“道常无名”以及“视之不见”等语句为例,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者。
但是任继愈先生并没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久,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仍坚持认为老子哲学是唯物论。
不过,后来的任继愈先生认为:用唯物论和唯心论来评价老子思想都是不合适的。
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在当时的确是很难得的,但任先生并没因此受到影响,这说明毛泽东对老子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的观点也不是特别坚持。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36">对于孔子:从崇拜到平视</h1>
毛泽东出生于晚清时代,科举制度依然是当时知识分子转变身份的唯一或主要出路。科举时代就得读孔圣人书。
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上学时每天都要叩拜孔子的牌位,直到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工人夜学开学仪式上,依然有一项议程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人民网·毛泽东谈孔子》。
这种崇拜一直到解放初期,他到曲阜参观孔庙、孔府、孔林的时候说:历代统治阶级给孔子戴了很多高帽子,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毛泽东自幼倾向于个性解放,具有“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年轻时就主张:“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这种思想变化,开始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跟李大钊的接触。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抨击康有为的“尊孔”行为,提出批孔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一直把孔子当做封建社会的圣人。他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尊孔读经”的复古活动,他提出: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后来他发动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是把批孔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林彪叛逃后,毛泽东认为,林彪与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儒反法的。所以决定在“批林”的同时“批孔”。
总起来看,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是早期崇拜,晚年批判,青年以后批判继承,就像他在解放初期说的那样: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杀。而主要的批孔大多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0">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h1>
墨子是下层人民的代言,他的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都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替劳动人民说话。
墨学曾是“显学”,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以其有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代表性,在兴盛时期足以与儒学相抗衡,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打压,直到清末才被重新挖掘,随着“德先生、赛先生”运动的兴起,墨学的工劳工精神和科学精神才得以复兴,当时的知识分子多以躬身践行墨家精神为荣,比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
1939年2月,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陈伯达写了篇写《墨子的哲学思想》的长文,请毛主席审阅。毛泽东回信说:“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并建议修改标题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家,是第一个提出认识论的思想家。毛泽东把墨子比作赫拉克利特,可见毛主席对墨子的推崇(中国政协报“毛泽东:墨子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毛泽东说: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如果全国党政军学都干起来,那不就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他引用墨家的信条“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
毛泽东对墨子的推崇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他在接受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我很喜欢那些正经书以外的小说、游侠,“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青年时代,他的偶像梁启超、胡适、谭嗣同都推崇墨家,梁启超说“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胡适则是少年时就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时,就听过胡适的墨子哲学课。因此,墨子的形象在他心中深深底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