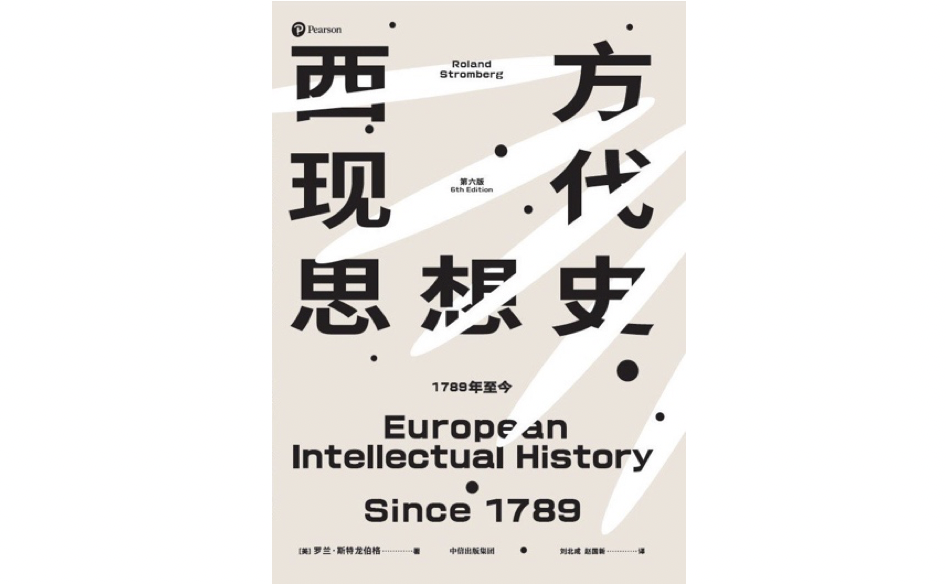
《现代西方思想史:1789年至今》,(美国)罗兰·施特龙伯格,刘北成,赵国新,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6月。
法国大革命
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在欧洲舞台上统治了几年。革命是由备受瞩目的"哲学家"运动领导的,该运动展示了一个浮华的思想领袖画廊。这些人物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在1860年代和1970年代,他们培养了未来的革命领袖。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引用了革命期间一位法国人的话:"他们用词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言语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些说法来自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和他的门徒。这些人被视为权威,后来甚至在革命政府的首领中受到崇拜。革命的主要派别更多地是他们所拥护的思想,而不是他们的社会阶级。一位著名学者指出,巴黎的革命世界观——无连裤袜的汉教"与其说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雅各宾派是1792-1794年的统治集团,由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组成。革命领袖也倾向于将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我们的革命不是起义的结果,而是半个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布里索在1791年9月吹嘘道。"哲学导致了法国的一场大革命,"1793年4月,一本重要杂志宣称。
不幸的是,启蒙哲学家在社会政治事务中的思想往往含糊不清,并且已被证明不足以指导革命。在英勇的开端之后,革命陷入了痛苦和血腥的内乱,导致了1793-1794年的恐怖。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混乱和矛盾,也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启蒙思想的不切实际。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成为所有法国敌人的圣经。保守派宣言指责革命是基于抽象观念的,认为在政治中只有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才能发挥作用。应该承认,正如现代思想史学家约翰·洛(John Lowe)所说:"试图找到启蒙哲学家对未来政府的看法,几乎总是一无所获。
事实上,几乎所有幸存的启蒙运动代表(那一代的大多数伟人都是在革命时期去世的)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震惊。归根结底,他们主张通过思想启蒙而不是暴力革命进行理性进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鄙视人民,希望有某种开明的独裁统治。他们相信理性的秩序和科学的方法,这些在革命的狂欢和无稽之谈中被践踏。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革命"这个词在启蒙哲学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在他们的期望中,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而是渐进的、有限制的、基本上可预测的改革的结果"。霍尔巴赫男爵是最激进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之一(一个无神论者,至少在没有仆人的情况下称自己为"上帝的私人敌人"),在他的政治著作《自然政治》(1773年)中写道:"在革命期间,人们愤慨,头脑发热,从不诉诸理性。大多数(不完全一致的)启蒙思想家在口头上敌视教会,但希望用理性的牧师取代基督教僧侣。此外,他们通常不想废除君主制,而是想让君主制成为启蒙的工具。
所谓的吉伦特派聚集了大部分启蒙知识分子。以罗伯斯庇尔和圣贾斯特为首的雅各宾派强烈谴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百科全书。1793-1794年,他们要么把吉伦特派的成员送上断头台,要么强迫他们无路可逃。"文人"几乎成了叛徒的代名词。激进的雅各宾派认为,他们的敌人是"受过最多教育,最忠诚,最奸诈和最狡猾的"。罗伯斯庇尔宣称,这些人"试图照顾自私的富人和平等的敌人"。雅各宾派只崇拜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到处都援引它,就好像他们是恶魔一样。罗伯斯庇尔称他为"圣人"。但是,他们崇拜的卢梭作为保护者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敌人。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启蒙哲学家,拒绝深刻的理性,更喜欢自然的情感。罗伯斯庇尔宣称,如果卢梭能活着看到革命,"谁能相信他的仁慈之心不会喜悦地拥抱正义和平等的事业呢?"但温柔的布里索和罗兰夫人也是卢梭的信徒,基于不同的解释和著作。到目前为止,这种差异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与罗伯斯庇尔相反,罗兰夫人的情人普佐在一封关于死囚牢房的信中写道,如果包括卢梭在内的启蒙运动哲学家还活着,"他们就会和他们一起死去"。如果他们不像我们一样流亡...孟德斯鸠、卢梭和马布利都将被判处死刑。
让-雅克·卢梭。
吉伦特派是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派别。他们反对流血和流氓暴力,憎恨政治对手用来摧毁他们的那种武力。关于如何处理国王(1792-1793)的争论导致了派系的瓦解,并最终导致了吉伦特派的垮台。吉伦特派不愿意让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因为他们担心这种激烈举动的后果。但正是在吉伦特派的领导下,法国开始了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二十多年来几乎连续不断的欧洲杀戮,使法国大革命成为一场世界革命。吉伦特派系中有一些最激烈的战士,他们最强烈反对"牧师阴谋"和"迷信",或百科全书,无神论者和叛逆神职人员。他们支持(事实上,他们创造了)有争议的《神父组织法》,该法将教会国有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基督教的改革,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建立非基督教信仰。
左翼的雅各宾派根据自己对卢梭"公共意志"的解释提出了一个民主概念。他们的目标是平等,而"公益"和群众行动的概念,往往是他们权力的基础,使他们赞美人民。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不太强调个人权利和议会制度,认为它们是自私和腐败的。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根本没有规定三权分立,也没有保障个人自由。它批准了基于人民意愿的基于公民投票的独裁统治,权力下放给少数人。
"我为人民说话,"罗伯斯庇尔宣称。有时,这种"极权主义民主"在深层次上是民主的,具有亲民的感觉,平等的激情和直接统治的愿望(罗伯斯庇尔希望建造一个可容纳12,000人的会议厅,让公众观看立法者的活动)。然而,它蔑视合法程序和个人权利。结果是1792年至1793年在极端战争条件下的恐怖统治。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是狂热的美德共和国时期一位伟大的革命宣传家和主要政治人物。作为启蒙运动的信徒,他怀疑基督教,但主张崇拜存在和理性的最高女神。他宣称无神论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他的神是人们的某种抽象化身。他是一个很好的公众鼓动人,但他与真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冷酷和不愉快的。他僵硬,真诚,耐嚼,善于说话和笨拙(罗伯斯庇尔除了发表演讲外几乎不做)。罗伯斯庇尔以正直为荣,他首先是一个演员,一个完全政治化的人物,没有自我利益。他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精神的化身。当他看到鲜血时,他会颤抖,但他可以以人类的名义下令处决数千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指责这场革命拖延了抽象的理论,缺乏务实的判断。这一指责似乎在罗伯斯庇尔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有原则的人变成了一个血腥的独裁者,最终被他用来摧毁敌人的革命机器摧毁了。
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并不是法国大革命最激进的产物。虽然雅各宾主义按照卢梭的社会契约精神,主张共同体优于个人,但它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志们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私有财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管理,但他们认为,正如卢梭所建议的那样,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允许每个公民拥有一点财产。这可以称为小资产阶级乌托邦或手工业工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革命中出现了,但直到全面发展才出现。在1795年的绝望日子里,革命似乎即将分崩离析,一小群社会主义者试图发动起义。由巴贝夫和博纳罗蒂领导的"平等阴谋"被击败,但留下了强大的传统。这些社会主义先驱也受到卢梭的一些著作的启发,尽管这些著作被粗暴地解释,他们憎恨私有财产、商业和奢侈品,颂扬贫穷、诚实劳动和简单生活的美德。博纳罗蒂幸存下来,并成为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趋势的联系纽带。这种无连裤袜的社会主义传遍了整个欧洲,对穷人阶级修辞理论的代表有很大的吸引力,接近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意大利的巴贝维斯特·鲁索(Babevist Russo)重申了萨沃纳罗拉(Savonarola)对回归中世纪的呼吁,呼吁富人放弃他们的珠宝。
革命的极端反而使革命名誉扫地。随着内战、迫害、恐怖和国际战争席卷欧洲大陆,最初在整个欧洲感受到的革命喜悦在19世纪90年代变成了失望和幻灭。起初,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大多对革命欣喜若狂,包括许多后来成为革命死敌的人。年轻的华兹华斯唱道:"活到那道黎明是多么幸福。除了华兹华斯,还有米斯特、霞多丽、康德、费希特、诺瓦利斯、歌德等等,很多人最初都有这种兴奋。卢梭在英国也有一个狂热的追随者,例如,托马斯·马尔萨斯的父亲只称他为"卢梭的朋友"。1799年,卢梭的信徒吉尔伯特·韦克菲尔德(Gilbert Wakefield)因公开希望法国入侵和征服英国而被监禁。在此期间,每个人都在阅读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落史》(The History of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吉本辛苦工作了20多年,于1787年完成了这部杰作。这部作品是共和的,至少在1789年的气氛中是这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似乎告诉人们,自第一位皇帝以来,古罗马一直在衰落,基督教终于结束了它。
但法国大革命迷失了方向,陷入了暴力、掠夺和不公正。最后,它以吞噬自己的"孩子"的可怕景象结束。结果,人们回顾理性时代的假设并拒绝它们,从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变。1794年后,最初的启蒙哲学家圣马丁成为与共济会的秘密分支有关的新神秘主义宗教的领袖。卢梭的影响也向直觉和想象力的方向传播。
反对革命
法国大革命很快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反弹。英国的伯克首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于1790年出版了《法国大革命》。伯克声称,革命之所以出错,是因为革命的领导人想摧毁整个政治体系,并在一夜之间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系。他将这一错误归咎于启蒙运动哲学家和政治理性主义者的基本思想。他们的方法就是抽象理论的方法,在这样一个领域玩抽象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种指控是有道理的。"小天狼星神父有许多鸽笼,里面装满了现成的体质,有标签,有分类和序列号,"伯克讽刺地写道。但是,宪法不应该从政治理论家出售的商品中选出,而必须像一棵大树一样从一个国家的土壤中生长几个世纪。
伯克的作品体现了他的风格,并对现实世界政治的微妙结构表现出惊人的洞察力。如果算是文学作品,则是新兴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散文作品之一。从这一雄辩中产生的主要思想是,社会是历史的广阔而复杂的产物,不能像机器一样修补;社会作为人类智慧的宝库,应该得到尊重,如果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体制机构的连续性。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观点认为,政治共同体是由历史塑造的,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自由政府可能存在;社会有机体有自己的等级制度,所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老百姓会尊重"天生贵族";一般规则和抽象原则根本无助于政治。他怀疑那些躁动不安的创新者,他们没有耐心吸收祖先的智慧,而不得不像先知一样,为激进的社会转型绘制蓝图。
《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埃德蒙·伯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7月。
伯克一方面拒绝法国人所倡导的"抽象权利",另一方面,他试图澄清人类的真正权利;他确实认为人们应该拥有这种权利,但他也强调,人们在进入文明社会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自由,以便获得政府的利益。这种真正的权利是以西方政治社会的基督教为基础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如果他脱离了维持其存在的古老习俗和传统结构,他就是一头野兽。此外,人是一种宗教动物,如果没有基督教,他会转向另一种可能不令人满意的宗教。因此,尊重上帝和尊重社会秩序是人生的两大责任。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历史是上帝旨意的彰显。伯克被指控崇拜教会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但他的崇敬是真实的。
这位爱尔兰演说家对后来的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版中重印。路易十六亲自将其翻译成法语。它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因为它的宏伟,还因为它看似神秘的预言性质,因为伯克在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宣布它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许多人认为,伯克的书超越了保守派,对政治思想甚至社会改革理论做出了真正的贡献。他并不真正反对变革,只要它得到适当的控制。他出身卑微,自己的经历是一场又一场激情澎湃的战斗——支持美国独立,倡导爱尔兰和印第安人的利益,最后反对法国大革命。从性格上看,爱尔兰人与保守派人士可能认为的完全不同。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指出:"他的本性总是最热切地敦促他为伟大的事业服务,并纠正一些可怕的不公正。伯克的许多想法被视为那些想要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的基本智慧。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Rasky)宣称:"不了解伯克的政客就像没有指南针的船只,在暴风雨的大海中迷失方向。当然,伯克的许多思想也被纳入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尊重社会秩序,不信任草率的改革者及其一次性计划,以及社会增长有机体的想法。
伯克的写作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当代,并在反革命事业和浪漫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50年代,当伯克还是一名苦苦挣扎的年轻律师时,他变成了一个文学家,并写了一篇关于《高贵之美》的文章。这篇论文通常被认为是从新古典主义到浪漫品味转变的标志。在他看来,当美的领域实际上被和谐、平衡和优雅的经典规则所支配时,还有另一个感知领域,那就是"崇高"。它唤起恐惧和敬畏,与古典美不同,古典美使我们有礼貌和相似,它使我们感到孤独,同时使我们兴奋和欣喜若狂。伯克本人一直都有点浪漫,尤其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许矛盾的是,他最后的伟大作品在内容上是保守的,在风格上是浪漫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重要的反革命倡导者也是革命家。
伯克的《法国大革命》不乏挑战者。1794年,潘恩进行了反击。他的《论人权》在伦敦卖得很好。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ldwyn)的《政治正义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Justice)充满了法国精神,建立了一个基于个人完美理想的理性主义乌托邦。戈德温是诗人雪莱的岳父。戈德温的妻子是女权主义倡导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他们被一个英国左翼团体包围着。格德温先生是一位哲学无政府主义者,他敌视国家和所有机构组织(例如,他还攻击公共教育系统)。"政府就像一件衣服,是失去贞洁的标志,"潘恩写道。"即使没有政府,一个共识的社会"也应该能够履行被政府权力篡夺的所有必要的社会职能。这个想法可能来自卢梭的思想。摆脱政府干预,社会将独立运作——这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想法,但更激进的是戈德温:"如果我们让每个人都倾听自己内心的进步,而不是找到用任何公共设施来规范他们的方法,那么人性很快就会成为唯一的真理。
随着英国与革命法国的分歧越来越大,格德温对卢梭的钦佩变得不受欢迎。著名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持亲法政治态度,一群暴徒摧毁了他的实验室。在蘇格蘭,嚴厲的批評迫使杜爾加德·斯圖爾特(Dugard Stewart)撤回了對法國溫和政治領袖康多塞(Condose)的讚揚。起初,科勒和他的朋友华兹华斯都同情革命,但后来"失去了尖锐的反叛号角",转而支持革命的异端邪说。在伯克的启发下,他被认为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但激进的报人威廉·科尔伯特(William Colbert)加入了反雅各宾派的事业。在英格兰教会内部,由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的福音派运动站出来反对18世纪教会对自然神学的纵容,并谴责不信的法国人。
拿破仑时代
伯克作为"守护者",捍卫传统和"惯例",可以说是逆流而上。正如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后来指出的那样,尽管发生了暴行,但法国大革命确实发生了,"它教导人们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视为权利的最高标准";它使男人和女人都习惯于改变;它无可挽回地扫除了旧秩序。就连伯克也无法想象,在欧洲恢复旧面孔是可能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久,法国军队将革命传播到整个欧洲。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1800-1814)导致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反对革命,但拿破仑的军事胜利继续颠覆了旧的模式。他还找到了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支持他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秩序统一欧洲,结束"封建主义"。
Bonjaman Gunsdang,Starr夫人和Rene Chardonnay领导着一群才华横溢的法国流亡者。这些人逃脱了他们所谓的暴君统治。其他人,如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歌德,从未对拿破仑失去信心,认为拿破仑的出现是天赐之物,上帝赋予拿破仑以进步的法律统一欧洲的使命。其他人则撤退以保持中立。在法国,所谓的思想学派,原启蒙运动哲学家达斯蒂·德·特雷西(Dusty de Tracy)的思想追随者(偶然逃脱了断头台),在面对革命的政治失败和幻灭时变得越来越冷漠和客观,并努力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一样研究人类的心灵:推进康多斯的"社会数学", "传达生命世界和生命世界"。(德斯特对孔蒂的影响表明了他与现代社会学兴起的关系。)
拿破仑喜欢。
包括生物学家拉马克(Ramak)和居维尔(Guvier)在内的一群杰出的法国科学家证明,在拿破仑的领导下,更中立的科学可以蓬勃发展。拿破仑也获得了那个时代对历史和东方的兴趣。在1798年对埃及的考察中,他陪同200名学者研究了这片迷人而神秘的古代土地。LaPlass改进了牛顿的物理定律,从而改进了经典力学。他发表了著名的《宇宙系统理论》,试图在没有牛顿"第一驱动力"奇迹的情况下解释宇宙的运行和演化。(当拿破仑问他为什么不提上帝时,他回答说:"陛下,我不需要这个假设。
当拿破仑私下讲话时,他喜欢用他的无神论和愤世嫉俗来震撼人们。但他坚信"只有宗教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期和平",所以他不能容忍任何公开的无神论,平息了革命与教皇之间的争端。私下里,拿破仑称通奸是"该地区的一个小错误,是化装舞会的一集",但拿破仑法典,他在主持下发展起来的新平等主义的伟大法典,规定了对通奸的严厉惩罚,因为"婚姻的稳定有利于促进社会道德"。他反对女权主义,称女性"只是生孩子的机器"。他鄙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所谓的文学风格"。他宣称,他收藏中最喜欢的是关于他的军队的统计数据!但他到处都读书。他没有放弃艺术,科学,哲学甚至政治方面的书籍,并且经常做出尖锐的评论。他真的不欣赏他的政治对手斯塔尔夫人和霞多丽所采用的新浪漫主义文学风格。总的来说,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投机思维没有发展。
拿破仑并不认为自己是暴君,他惊讶地发现人们这样看他。在被流放到偏远的圣赫勒拿岛后,他在去世前宣布,他的使命是消除封建主义,统一非洲大陆,并通过公平公正的法律"确保人的尊严"。为此,他调整了革命,使其务实,平息了法国的动乱,并以贤能政治的原则为普通人打开了机会之门。他将法治下的自由和平等输出到德国和意大利。他恢复了波兰的独立,因此他一直是波兰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支持者。在他执政的15年里,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中断,就像欧洲的内战一样,尽管法国以外的许多人认为这是法国帝国主义的表现。有些人,比如诗人雪莱,最初向他致敬,最终谴责他是自由事业的叛徒。贝多芬最初将他的"英雄交响曲"头衔献给拿破仑,但当第一届政府戴上他的王冠时,贝多芬撕毁了这个头衔。这个故事受到了质疑,但你不妨相信它。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其他重要思想家也是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人们对这位伟人感到困惑。根据荷兰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eter Gale)的经典著作《拿破仑:赞美与诽谤》(Napoleon: Praise and Defamation),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来自科西嘉岛的小家伙在一段时间内从未知上升到世界上的统治者,留下了一个不再一样的世界。他所表达和体现的力量,远比他自己非凡的个性更伟大。
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画作,"自由引导人民"。
在这个划时代的一年里,欧洲经历了巨大的冲击。神圣罗马帝国等古代地标被连根拔起,王冠倒塌,新的主人出现。拿破仑多年来一直是反派角色的最佳人选。据估计,从1803年到1814年,伦敦先知乔安娜·索斯科特(Joanna Southcott)拥有数十万追随者。这位文盲的德文郡村妇在宣布基督再来时引起了轰动。她的信息恰逢动荡时期,当时英国人担心法国入侵以及物价上涨和失业率。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cCauley)感到惊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老妇人,除了算命先生的狡猾之外一无所有,所受教育的不超过一个仆人,却被视为一位女先知,被成千上万的信徒包围着。这一切都发生在19世纪的伦敦。"当时,各种千禧一代的福音派人士也以宗教改革的传统在德国南部和瑞士出现。
关于拿破仑的争论是无休止的。英国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在得知拿破仑最终失败后,被他的朋友海顿描述为"身体和精神上都被遗弃了"。"他浑身是泥土,走来走去,白天很少醒着,晚上总是喝醉",持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仿佛他从一个大梦中醒来,从来没有喝醉过。海顿认为拿破仑可耻地背叛了他的真正事业,但当这位伟人于1821年去世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后代永远不会理解这个时代对拿破仑的感受" - 他的崛起,荣耀和失败对人们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些时刻令人兴奋。毫不奇怪,浪漫主义出现在从1789年革命开始到1815年拿破仑最终失败的动荡的二十年中。
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最明显的政治冲动是民族主义。它通常诞生于普鲁士在1807年耶拿战役中惨败之后。费希特和霍尔德,德国思想大师,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家和年轻的组织者,宣扬民族主义。启蒙运动本身一直在宣扬普世教会主义。费希特确信,这是贬义斥责时代的众多错误之一。法国人领导了启蒙运动;现在,歌德、贝多芬、席勒、康德时代的德国人正在承担起欧洲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主导作用。费希特在他广为流传的《德意志民族演说》(1807年)中宣称,德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已经觉醒,在政治上也应该觉醒。革命的目标——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确实值得追求,但权利需要植根于特定的人类家庭,而不是模糊的普遍人类。革命本身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分子。这是一场法国大革命,因为它发生在那片土地上,它曾经是国家在各个省份的高度封建。(可以说,巴黎是革命的中心,许多省级城市也是如此。反对革命敌人的战争使全国团结起来。这伴随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和统一文化的冲动,例如通过将当地方言统一为法语。
民族主义是革命的正确含义。一旦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分崩离析,国家就成为新的社会平等的自然载体。为什么人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是祖国的孩子。国家不再由特权者统治,而是所有人的财产,是平等权利的守护者和象征。德国民族主义者高呼:"自由王国!人人平等!在人民国家中没有特权等级,只有属于同一人民的平等公民。
民族主义在19世纪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意识形态,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它。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军队铲除了旧的君主制,阻止了它的恢复。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后,政要们聚集在维也纳重建欧洲。他们试图用"王朝正统"作为政治权威的指导原则,但无济于事。很快,意大利人率先试图将意大利半岛从奥地利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木炭燃烧派对,青年意大利派对跟随。这是自1820年以来最浪漫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
作者:|(美国)罗兰·施特龙伯格
编辑和编辑|李永波
指南校对|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