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的学术随笔集《进学丛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收录五十篇篇引人细读、唤起共鸣的学术文章,其中对林庚、聂石樵、周先慎、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回忆尤其于思考学术进阶多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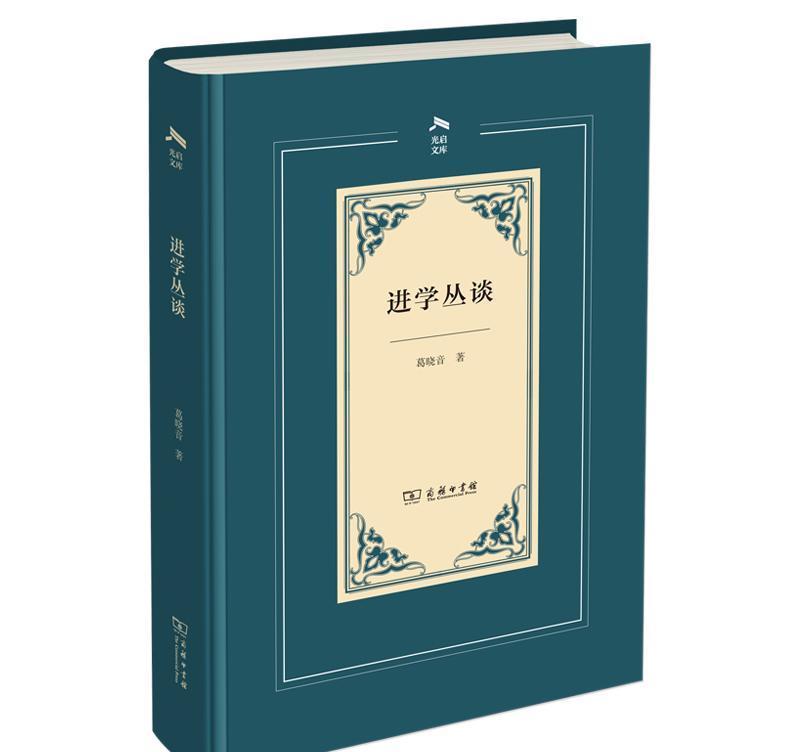
葛晓音,1989年起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雅荣休教授,国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八代诗史》《汉唐文学的嬗变》《唐宋散文》《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唐诗宋词十五讲》《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唐诗流变论要》《杜诗艺术与辨体》等等。
葛晓音教授是林庚先生的得意弟子。《进学丛谈》一书共五辑五十篇,葛晓音教授用“杏坛探颐”“师友遗影”“书刊因缘”“新著撷英”“潮头点滴”等五辑在追溯进学之路上的点滴时怀人忆事,如对林庚、程千帆、陈贻焮等先生的回忆,良多感怀;亦在追忆不同人生阶段对进学之道的感悟时提点后人,颇多启发。此书可谓葛晓音教授“朝花夕拾”之作,文字朴实,感情真挚。
试读章节:
作者/葛晓音
黄昏时分,远处又传来了悠扬的钟声。我放下笔,静静地听着。“客心洗流水,遗响入霜钟”,客居东京,每天都能在下午五点听到报时的钟声,才悟出唐人为什么如此喜爱暮钟。这宇宙间的韵律,能洗净世俗的尘滓,将人带进安宁恬适的心境。遥望西天,我的神思随钟声飞往彼岸。在那夕阳西下的地方,在北大燕南园林庚先生的书斋里,曾有多少个黄昏,我与先生隔着一张古旧的书桌,对坐清谈。斜晖透过疏林,照进窗棂。竹影摇曳,虚室生白,这是北大生活中最美好的境界。
学生时代徘徊在学术门墙之外的时候,仰望学界名流,几乎个个背后都有神圣的光环。待到自己跨进大门以后,才知道里面并不是理想的乐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影响,加上“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中国当代学者难以安心于学业。十年寒窗苦读,所搏取的往往是学术以外的目标。社会评价学者的标准不是学识的多少,而是职位的高低。多年来看够了新儒林的闹剧和悲剧,有时觉得在尘世的纷纭扰攘之中,几乎找不到一方可以安顿心灵的净土。只有走进林庚先生的书房,心里才觉得充实宁静。
凡是见过林庚先生的人,都说他仙风道骨,从里到外透出一股清气。他确是远离尘嚣的,他的超然似乎是因为无须介入世俗的纷争。每当我把烦恼和牢骚带进他的书斋时,他总是微笑着说:“到我这里来吧!我这里是一片净土。”他看待世事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我以前总以为这是他的资历和名望使然。但相处日久,才渐渐明白这其实是他的诗人气质决定的。林先生论唐诗以“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的观点著称于世。熟悉他的为人,才能体会这论点其实正出于他对诗的本质的理解,也是他本人精神面貌的写照。我的导师陈贻焮先生曾说:“人生犹如战场,只有少年和老年不必参与。所以我喜欢孩子和老人。”林先生的清高并非因为他是得道的老人,而恰恰是因为他到老都始终保持少年的精神。
我上大学的时候,林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但仍不失青年时代的风采。他上课时总是衣着整洁,神情严肃而高傲,学生对他十分敬畏。但1964年时极左思潮已席卷首都,一些革命同学从林先生的授课内容里嗅出“资产阶级的气味”,开始发起对他的批判,并要我这个“课代表”转达。林先生接到批评意见后,一言不发。在下一堂课上,将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一段话抄了整整一黑板,作为回答。现在想起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有这样的傲骨,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当时有多少学者在这种压力下“修正”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但林先生认为正确的意见就要坚持,对于外界会怎样看他几乎是不屑一顾。
林先生年轻时爱唱歌,能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唱西洋歌剧名曲。听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大家齐唱《东方红》,他的尾音拉得长了一点,结果遭到造反派的一顿批判。他不管《东方红》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只知道唱歌就要用西洋发声法。现在虽已八十多岁,但仍能唱男高音,而且自己录了音。我去他家,常常听到他在放自己的录音,底气的充足真不像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林先生还像孩子一样爱风筝,每年春天由女儿陪着到运动场去放。天气好的时候,他穿着夹克送客到门口,大家称赞他看起来很年轻,问他什么时候去放风筝。他便高兴地借用一句宋人的诗回答:“将谓偷闲学少年。”正是这种少年精神,使人从林先生身上看不到老年人的衰惫之态。他走路总是急匆匆的。想到什么事情说干就干,绝不拖拉。他从来没有耐心吃带骨头和刺的食物,如鸡和鱼之类,他说那太麻烦,浪费时间。他也没有老年人通常有的怀旧情绪和保守心理,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的思潮和新生的事物,他总能很快接受。有一次我埋怨用电脑打字还没有手写得快。他劝我应当尽快学会电脑,不要落伍。我常常觉得自己的许多观点比林先生要保守得多。像少年人一样,他总是向前看,很少听他回忆往事。
始终保持少年的活力和意气,这也是林先生理解生活和诗的出发点。他热爱一切朝气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新鲜事物。记得有一次闲谈时,林先生说他喜欢春天。在未名湖畔散步,年年看着柳树发芽,桃花绽红,都有一些新的感触。有一天在湖边看到几个十来岁的女孩子一起玩。过了一会儿,其他女孩都走了,只有一个女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凝思。他忽然想到《红楼梦》里所写的类似情景,体会到曹雪芹对这个年龄的女孩的特点把握得相当准确传神。林先生在治学中的许多思考都来自生活中这类诗意的感悟和触发。他强调少年精神,认为诗的原质就在于青春的活力和新鲜的生命,所以他喜欢盛唐诗,认为宋诗除了绝句以外,都已老化,因而对宋诗评价不高。他的学术见解和他的个性以及他的生活感悟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他的文学研究是活的,研究对象在他笔下呼之欲出,而不像在一般学者笔下有如被解剖的尸体。我读他考证楚辞的文章,常会不自觉地被文字中透出的生气勃勃的雄辩力量所打动,而忘记了这是枯燥深奥的考据。他在七十多岁时,为研究生开设“天问研究”的专题课,内容涉及许多难懂的古天文知识,上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听众并不仅仅是慕名而来,更多的是被他讲解“天书”的生动有趣所吸引。然而林先生对他的幽默感并无自觉,也从来不笑。这种幽默完全出自他与研究对象的契合、见解的敏锐和透彻,以及善于表达的辩才。
陈贻焮先生常说,林先生的艺术鉴赏力极高,他所称道的作品无一不是上品。因而我们这些弟子也自然而然地以林先生的眼光作为判断作品好坏的标准。林先生所作的现代诗有他独特的格调,要透彻解读,必须具有与林先生同等的对诗的感悟力。读他的诗和文章,我不止一次痛切地体会到作诗和研究诗都需要天赋。一到林先生面前,我就觉得自己是钝根,而且常常为自己达不到林先生那样生动活泼的治学境界而沮丧。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