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教授葛曉音的學術随筆集《進學叢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收錄五十篇篇引人細讀、喚起共鳴的學術文章,其中對林庚、聶石樵、周先慎、王瑤等老一輩學者的回憶尤其于思考學術進階多有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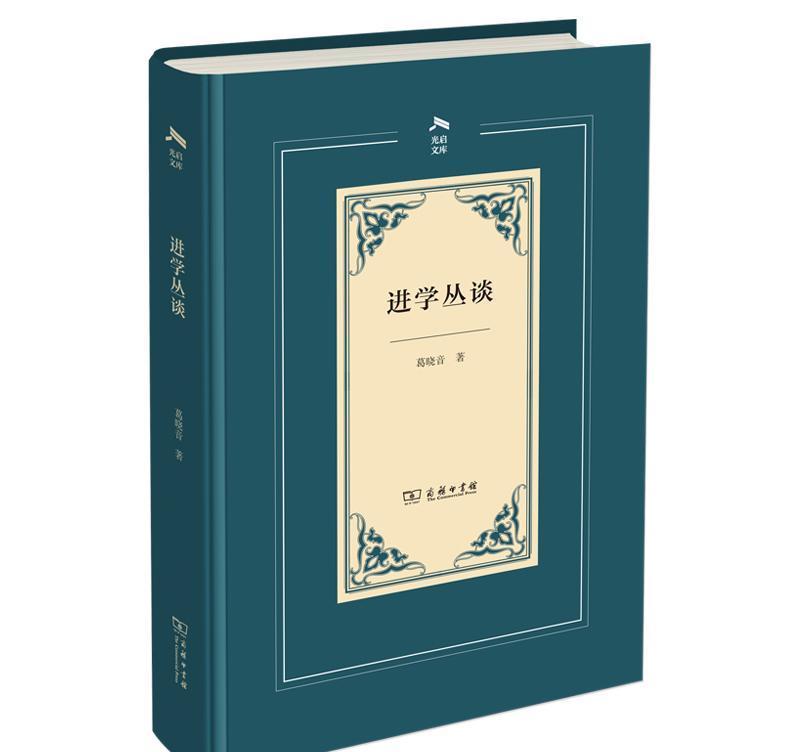
葛曉音,1989年起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即研究所學生院)人文社會系教授,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雅榮休教授,國學院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八代詩史》《漢唐文學的嬗變》《唐宋散文》《山水田園詩派研究》《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唐詩宋詞十五講》《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唐詩流變論要》《杜詩藝術與辨體》等等。
葛曉音教授是林庚先生的得意弟子。《進學叢談》一書共五輯五十篇,葛曉音教授用“杏壇探頤”“師友遺影”“書刊因緣”“新著撷英”“潮頭點滴”等五輯在追溯進學之路上的點滴時懷人憶事,如對林庚、程千帆、陳贻焮等先生的回憶,良多感懷;亦在追憶不同人生階段對進學之道的感悟時提點後人,頗多啟發。此書可謂葛曉音教授“朝花夕拾”之作,文字樸實,感情真摯。
試讀章節:
作者/葛曉音
黃昏時分,遠處又傳來了悠揚的鐘聲。我放下筆,靜靜地聽着。“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鐘”,客居東京,每天都能在下午五點聽到報時的鐘聲,才悟出唐人為什麼如此喜愛暮鐘。這宇宙間的韻律,能洗淨世俗的塵滓,将人帶進安甯恬适的心境。遙望西天,我的神思随鐘聲飛往彼岸。在那夕陽西下的地方,在北大燕南園林庚先生的書齋裡,曾有多少個黃昏,我與先生隔着一張古舊的書桌,對坐清談。斜晖透過疏林,照進窗棂。竹影搖曳,虛室生白,這是北大生活中最美好的境界。
學生時代徘徊在學術門牆之外的時候,仰望學界名流,幾乎個個背後都有神聖的光環。待到自己跨進大門以後,才知道裡面并不是理想的樂園。“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影響,加上“官本位”的社會風氣,使中國當代學者難以安心于學業。十年寒窗苦讀,所搏取的往往是學術以外的目标。社會評價學者的标準不是學識的多少,而是職位的高低。多年來看夠了新儒林的鬧劇和悲劇,有時覺得在塵世的紛纭擾攘之中,幾乎找不到一方可以安頓心靈的淨土。隻有走進林庚先生的書房,心裡才覺得充實甯靜。
凡是見過林庚先生的人,都說他仙風道骨,從裡到外透出一股清氣。他确是遠離塵嚣的,他的超然似乎是因為無須介入世俗的紛争。每當我把煩惱和牢騷帶進他的書齋時,他總是微笑着說:“到我這裡來吧!我這裡是一片淨土。”他看待世事自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眼光,我以前總以為這是他的資曆和名望使然。但相處日久,才漸漸明白這其實是他的詩人氣質決定的。林先生論唐詩以“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的觀點著稱于世。熟悉他的為人,才能體會這論點其實正出于他對詩的本質的了解,也是他本人精神面貌的寫照。我的導師陳贻焮先生曾說:“人生猶如戰場,隻有少年和老年不必參與。是以我喜歡孩子和老人。”林先生的清高并非因為他是得道的老人,而恰恰是因為他到老都始終保持少年的精神。
我上大學的時候,林先生已經五十多歲,但仍不失青年時代的風采。他上課時總是衣着整潔,神情嚴肅而高傲,學生對他十分敬畏。但1964年時極左思潮已席卷首都,一些革命同學從林先生的授課内容裡嗅出“資産階級的氣味”,開始發起對他的批判,并要我這個“課代表”轉達。林先生接到批評意見後,一言不發。在下一堂課上,将恩格斯《反杜林論》裡的一段話抄了整整一黑闆,作為回答。現在想起來,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有這樣的傲骨,是要承受很大壓力的。當時有多少學者在這種壓力下“修正”了自己的學術觀點。但林先生認為正确的意見就要堅持,對于外界會怎樣看他幾乎是不屑一顧。
林先生年輕時愛唱歌,能用英語和意大利語唱西洋歌劇名曲。聽說“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大家齊唱《東方紅》,他的尾音拉得長了一點,結果遭到造反派的一頓批判。他不管《東方紅》是一首什麼樣的歌曲,隻知道唱歌就要用西洋發聲法。現在雖已八十多歲,但仍能唱男高音,而且自己錄了音。我去他家,常常聽到他在放自己的錄音,底氣的充足真不像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林先生還像孩子一樣愛風筝,每年春天由女兒陪着到運動場去放。天氣好的時候,他穿着夾克送客到門口,大家稱贊他看起來很年輕,問他什麼時候去放風筝。他便高興地借用一句宋人的詩回答:“将謂偷閑學少年。”正是這種少年精神,使人從林先生身上看不到老年人的衰憊之态。他走路總是急匆匆的。想到什麼事情說幹就幹,絕不拖拉。他從來沒有耐心吃帶骨頭和刺的食物,如雞和魚之類,他說那太麻煩,浪費時間。他也沒有老年人通常有的懷舊情緒和保守心理,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新興的思潮和新生的事物,他總能很快接受。有一次我埋怨用電腦打字還沒有手寫得快。他勸我應當盡快學會電腦,不要落伍。我常常覺得自己的許多觀點比林先生要保守得多。像少年人一樣,他總是向前看,很少聽他回憶往事。
始終保持少年的活力和意氣,這也是林先生了解生活和詩的出發點。他熱愛一切朝氣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新鮮事物。記得有一次閑談時,林先生說他喜歡春天。在未名湖畔散步,年年看着柳樹發芽,桃花綻紅,都有一些新的感觸。有一天在湖邊看到幾個十來歲的女孩子一起玩。過了一會兒,其他女孩都走了,隻有一個女孩坐在一塊大石頭上凝思。他忽然想到《紅樓夢》裡所寫的類似情景,體會到曹雪芹對這個年齡的女孩的特點把握得相當準确傳神。林先生在治學中的許多思考都來自生活中這類詩意的感悟和觸發。他強調少年精神,認為詩的原質就在于青春的活力和新鮮的生命,是以他喜歡盛唐詩,認為宋詩除了絕句以外,都已老化,因而對宋詩評價不高。他的學術見解和他的個性以及他的生活感悟是融為一體的,是以他的文學研究是活的,研究對象在他筆下呼之欲出,而不像在一般學者筆下有如被解剖的屍體。我讀他考證楚辭的文章,常會不自覺地被文字中透出的生氣勃勃的雄辯力量所打動,而忘記了這是枯燥深奧的考據。他在七十多歲時,為研究所學生開設“天問研究”的專題課,内容涉及許多難懂的古天文知識,上百人的教室座無虛席。聽衆并不僅僅是慕名而來,更多的是被他講解“天書”的生動有趣所吸引。然而林先生對他的幽默感并無自覺,也從來不笑。這種幽默完全出自他與研究對象的契合、見解的敏銳和透徹,以及善于表達的辯才。
陳贻焮先生常說,林先生的藝術鑒賞力極高,他所稱道的作品無一不是上品。因而我們這些弟子也自然而然地以林先生的眼光作為判斷作品好壞的标準。林先生所作的現代詩有他獨特的格調,要透徹解讀,必須具有與林先生同等的對詩的感悟力。讀他的詩和文章,我不止一次痛切地體會到作詩和研究詩都需要天賦。一到林先生面前,我就覺得自己是鈍根,而且常常為自己達不到林先生那樣生動活潑的治學境界而沮喪。
南都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