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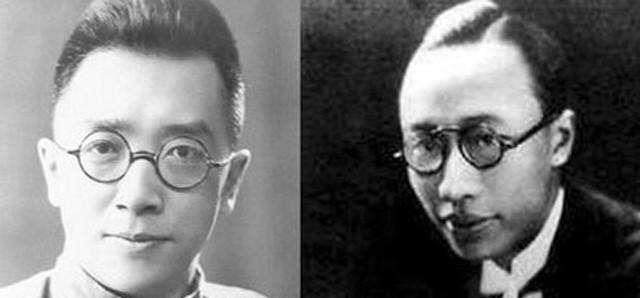
图 | 胡适和溥仪
胡适和溥仪,他们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晚清的末代皇帝,按理说这样两个身份极具差异性的人之间不应该有所交集,可就在1922年,胡适却应溥仪之邀进入了紫禁城。
然而,新人物与旧代表的交往,却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媒体对胡适的行为进行了指责,而胡适仍坚持己见为溥仪打抱不平,直言这是一件有“人味儿”的事情。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邀请胡适进宫
上世纪20年代,尚在紫禁城中的溥仪醉心于英美文化,还给自己取了个“Henry”的英文名,溥仪刚刚大婚,正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无心光复大清。
图 | 溥仪
1922年,紫禁城的养心殿内拉进了电线,刚刚装上电话,17岁的溥仪仔细打量着这个新鲜的玩意儿,心血来潮的他拿出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儿。溥仪先给京剧武生演员杨小楼拨了一个,接着又打给杂技演员,又给东兴楼饭庄打,几乎每个电话都是骚扰完就挂。
突然,溥仪想起一件事情,他的洋老师庄士敦曾跟他说起,有个叫胡适的白话文领袖,溥仪对这个人十分好奇,很想听听这个白话文领袖是用什么调儿说话的。
庄士敦是一位英国籍教师,他来到溥仪身边后,为自幼被束缚在紫禁城的小皇帝打开了一扇接触外界的窗户,这对长在深宫里的溥仪来说十分有吸引力。
不过,许多清廷旧臣此时仍在溥仪身边充当着他的“师傅”,这些老学究们并不喜欢庄士敦,只是一味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来武装这个小皇帝的头脑。可不管怎么说,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还是带给溥仪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出现的。
就这样,溥仪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对于他们当时通话的情景,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曾有回忆:
电话拨通后,溥仪好奇地问道:“你是胡博士吗?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啊?我怎么听不出来呢?……”胡适当然不会知道给自己打电话的是谁。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溥仪爽快地亮明了身份。
“宣统?……你,你是皇上?”胡适有点不敢相信对方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
“对啦,我就是皇上,我听见你说话了,可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有空的话你就到宫里来,叫我瞧瞧吧。”
胡适有写日记的习惯,同样,他也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件事: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其实,在接到溥仪的这通电话之后,胡适的心情很是复杂,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兴奋。虽说此时的溥仪已经退位,但根据当时民国政府与退位清廷的协议,清王朝仍可以继续统治紫禁城的一方土地,每年政府还要补贴四万银元,供小朝廷开销。
不得不说,胡适对于和溥仪的这次见面比较谨慎,虽然胡适常常自称少年,但他此时已经30岁了,行事沉稳细密,这从他没有立即答应和溥仪的见面就可以看出来。
胡适心里明白,在对宫中及溥仪近况还不太了解的情形下,贸然进宫仓促与其见面,很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尴尬局面,为此,胡适专门提前去拜访了庄士敦先生,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有关皇宫和溥仪的情况。
图 | 庄士敦与溥仪合影
见过庄士敦之后,根据庄士敦对溥仪的叙述,胡适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从胡适的这则日记中也可看出,他对于溥仪“自行其意”的行为作风是比较赞赏的,这代表着溥仪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与他见一面还是有意义的。
胡适进宫见溥仪,引起舆论风波
几天之后,胡适前去赴约,为此他一天都没有去上课。那天,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到胡适家里去接他,先被引至神武门前下车,通报之后得以入内。见面后,胡适向溥仪行了鞠躬礼,然后在溥仪为他准备的一张蓝绸缎子的大方凳上坐下。
图 | 胡适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形容他对溥仪的第一印象:
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
接下来,便开始了当天的话题。一位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一位是新文化的领军人物,坐在一起却是侃侃而谈。胡适与溥仪聊了很多,包括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出洋以后如何留学等等。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
“我们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情,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但这件事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尽管胡适不能够对溥仪说的话感同身受,但心里对他这种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是十分同情,谈话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溥仪抱怨说自己有许多新书都找不到,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
就这样,胡适与溥仪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交谈了大概20分钟之后,即起身告辞。
见过溥仪之后,胡适还写了一首名为《有感》的小诗,表达了自己事后的感受,其中有这样一句: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胡适却把它写得十分凝练而有意味,生动表达了自己对这个少年逊帝的关切之情。胡适对溥仪是有所同情的,然而,新文化思想领袖与旧制度帝王的私自见面,在当时却似乎并不能被大众所理解。
一方面,满清遗老对溥仪表示不满,在得知他们的“皇帝”和“新人物”见了面之后,便像炸了油锅似的在背地里吵闹成一团。另一方面,热衷于新文化的年轻人对胡适的做法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上都出现了诸如“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的标题。
对于胡适和溥仪见面这件事情,上海国民党人所办的《民国日报》就刊载有一篇带有嘲讽色彩的评论,其标题便是《胡适之请免跪拜》,其中这样写道:
溥仪请胡适之去谈谈,自然去谈谈罢了。不想这位胡先生竟要求免除跪拜。这种要求,如果由张勋徐世昌等提出,原极平常;今提出于胡先生,太觉突兀了。目中有清帝,应该跪拜;目中无清帝,何必要求;只有出入于为臣为友之间的,才顾念得到必须跪拜,顾念得到要求免跪拜。
溥仪允胡适之要求时,称他做新学界泰斗,大有许其履剑上殿之概,然而这是溥仪底大度,不是胡适之底尊荣。
那么,胡适当时是否有跪拜担忧,溥仪在后来回忆时也曾说过:“他(胡适)连忙向庄士敦打听了进宫的规矩,明白了我不叫他磕头,我这皇帝脾气还好,他就来了。”
不仅如此,鲁迅也在后来一篇调侃胡适的文章中写道:好像有人问过,你是不是见到逊帝跪下来磕头呢?你是不是见到逊帝还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
图 | 鲁迅
在这种背景下,为平息舆论,胡适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澄清事实。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胡适这样写道:
“一个人去见另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变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我没工夫去——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至此,这场风波才算稍微得到了平息。
其实,从客观的立场来看,胡适礼节性地去拜访溥仪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但他却为何因此招致了那么多青年人的不满,这个问题很值得大众去深思?
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中,尤其是那句“他称为先生,我称他皇帝”的话,广受争议。
当时,新文化的潮流是很强劲的,在激进的年轻人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自然是不能和晚清的皇帝去交朋友。
如果说胡适关注到的只是一个叫溥仪的十七岁少年,那么到了激进青年眼中,他们看到的更多的可能是溥仪背后的皇权象征,所以胡适和溥仪的见面在他们眼里自然不是一件平常小事。
胡适与溥仪的最后交集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直系将领冯玉祥率军进京发动了政变,成立临时政府,并修订了“优待条件”,取消帝号,强令溥仪出宫。
图 | 冯玉祥
在当时,支持溥仪出宫的言论明显占优势,革命党方面给出的态度是极力赞成,孙中山后来致电冯玉祥,直言移宫废号是“大快人心”之举,“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与此同时,一些同情清室的言论则大多只是在私下传播,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代表的胡适却主动出面维护溥仪,难免不引人注意。为此,胡适撰写了给临时政府外长王正廷的公开信,在信中明确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反对,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将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除了胡适,段祺瑞也在冯玉祥修改优待条件之后提出了异议,并在给冯玉祥的电文中强调:清室是主动退位,应予礼遇,且优待条件牵涉到国际方面;至于“优待条件”中规定的“移宫”,则是希望继续采取拖延的方法,“从长计议”,如今强行迫使溥仪出宫,有损民国信誉。
但是,溥仪被驱逐出宫的事情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改变,胡适遂就善后事宜又提出三点建议:
保证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妥善处理清宫古物,防止军人政客趁火打劫;公平合理估价清宫古物,按时足额付给清室。
果然,胡适的信一经发表,当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胡适的信主要在“信义”和“道义”上指责了冯玉祥的做法,随后,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也给出了正面回应,庄士敦在信中称赞胡适用正确的方式说了正确的事情,并表示溥仪看了他的信一定会高兴。
但是,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这样想。周作人在看到胡适的立场之后,在写给他的信中指出:
“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和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20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逐溥仪出宫)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绝不是污点。”
学者李书华、李宗侗联名致信胡适:
“我们读了这段新闻以后,觉得非常骇异,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样的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面对质疑和批判,胡适首先声明,自己的公开信在外国人(庄士敦)发表相关言论之前,不曾受其影响,他并没有受人指使和利用,他的意见只代表自己,大家在取消清帝年号上没有争议,只是他主张在取消方式上温和一点,多一点“绅士的行为”罢了。
其实,从胡适的为人不难看出,他是主张改良的一派,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立志要做“国民导师”,他试图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建树,胡适为人好打抱不平,替弱者代言,主张宽容和容忍,强调言论思想独立自由,反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胡适的思想也会跟着转变。
1931年9月的一天,胡适和徐志摩等人同游景山,在向下俯视故宫时,胡适语气沉痛地感慨道:“
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道怎么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
说罢,胡适长长叹了一口气,感慨这山河巨变……
图 | 小时候的溥仪
历史似乎和胡适开了一个大玩笑,他最终未能把他所同情的那位少年逊帝从那个“咬不开,锤不碎的核儿”里救出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溥仪后来竟坐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宝座,成了民族的罪人,这一点不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