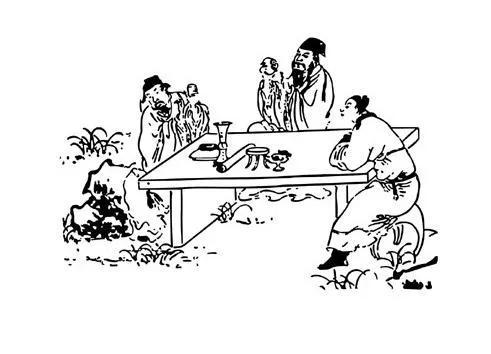
酒文化也是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名资深的美食品鉴者,袁枚常自称自己不饮酒。事实上,与其说袁枚不饮,倒不如说他对饮酒适可而止,不成瘾。袁枚在《随园诗话·茶酒单》中写道:“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深知酒味。”袁枚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品尝出酒的美味,是因为对酒有控制力。
《随园食单》中共提及17种地方酒,且袁枚绝大多数都尝过,并写下品鉴完酒的看法。例如,袁枚认为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掺一毫假”;金华酒有“女贞之甜,无其俗”;金坛于酒“一清彻骨,色若松花”。总之,袁枚的饮酒观独树一帜,反映了一种独特的酒文化。
魏晋以后,醉酒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文人骚客以饮酒为乐。袁枚是一位不善饮酒,甚至宣扬不饮酒的标志性人物。他曾在《酒友歌》中自嘲:“随园先生枉生口,能食能言不能酒”。偶尔在朋友百般劝说下不得不饮酒,袁枚只饮了半殇便头晕脑胀,不省人事。
袁枚也曾在自己的不饮酒诗中描述醉酒后的痛苦状态:“偶一问其津,身热头痛耳。”袁枚之所以提倡不饮酒,源于传统饮酒风气的嬗变。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认为“惟酒无量,不及乱”,即喝酒的量不限制,只要保证不醉即可。
西汉时期,“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无论是君子还是百姓,都极力提倡饮酒。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文人雅士通过喝酒来逃避痛苦,同时追求个性解放。到了唐朝,酒被李白、白居易等爱酒文人一捧再捧,以至于后世跻身于诗坛者皆要效仿,纷纷以能醉自居。
连李清照等闺中少女也要吟诵“浓睡不消残酒”等诗句,以此来表象自己饮酒量之大。由此可见,袁枚之所以大力推行不饮之风,主要是为了反对以饮为名士之风的现象。然而,对于饮酒,袁枚又是矛盾的。他虽自言不饮,却也离不开酒。袁枚曾坦然直言:“有酒我不饮,无酒我不欢”。
袁枚生性乐观洒脱,爱热闹,偶而也会摆酒席,撑排场。例如,家僮如儿女,纷纷罗酒浆……后湖七八月,载酒水中央。”尽显宴会的热闹盛大与家人好友间的其乐融融。
袁枚虽不善饮酒,却颇有饮酒的心得。他认为饮酒过后即是“酒痕如雨见风消”,所有的痛苦、烦恼与喜乐都会转瞬即逝,且不留痕迹。袁枚的酒量不大,稍饮便会头疼脑热,甚至吟诵了不少“不饮之诗”,可他始终离不开酒的根本原因在于“以酒会友”。身边尽是爱酒之辈,若不饮酒,则会显得格格不入。为了结交贤能之辈,袁枚不得不饮酒。此外,袁枚饮酒也是为了诗酒结社。由于清朝禁止带有政治性质的诗酒结社,因此袁枚只以赏景饮酒作为理由招客。
不过,文人向来诗酒不分家,畅饮之余也会做一些文字游戏亦或是提笔作诗。此外,酒还能刺激人们酒后吐真言,对于文人来说是最好的催化剂。因此文人雅士尽管不饮或是不善饮,也断断离不开酒,这也是袁枚离不开酒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