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鳴驚人”的典故流傳十分廣泛,它出自《韓非子·喻老》,講的是楚國春秋時期最著名的國君楚莊王早年的趣事。
上回說到,晉成公剛解決了内部的問題,就又不得不面臨楚國的威脅,那麼楚國最近的情況又如何呢?
自從上次楚穆王在厥貉大會諸侯之後,回來過了一年多就因病去世,他的兒子熊侶繼承了王位,是為楚莊王。
楚莊王剛即位的時候年齡不到二十歲,相當的年輕,也正因為如此,這時候的楚莊王和當初晉靈公一樣,完全不把心思放在朝政上,而是一味想着取樂,但楚莊王的運氣卻沒有晉靈公那麼好,他所要面對的是一個動蕩的楚國,不但内部糾紛不斷,周邊一些國家也接二連三的找麻煩。
楚莊王上任的第一年,令尹成嘉和太師潘崇起兵讨伐群舒,所謂群舒,是指盤踞在楚國東南方面的諸多偃姓舒族小國,其成員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龍、舒鮑和舒龔等,這些國家因實力弱小,長期以來都依附于楚國,然而在公元前615年的時候,楚國原先的令尹成大心病故,其弟成嘉接班,群舒便趁機連同他們的宗屬一起背叛了楚國。
不過這次叛亂很快就被平息,為了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成嘉才連同潘崇對群舒主動出擊,并特意交代公子燮和鬥克二人留守郢都,輔佐楚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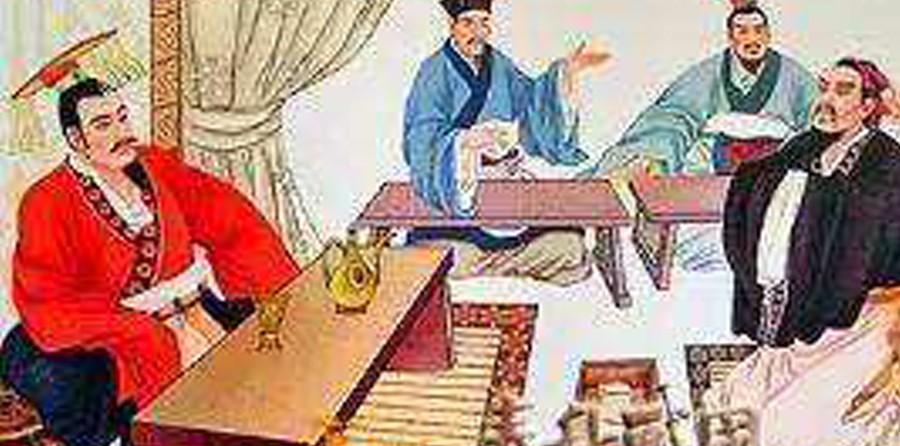
然而這兩個人都有些特殊,鬥克本是楚國人,當年秦晉兩國聯手攻打楚國的屬國鄀國時,楚成王曾派鬥克和息公屈禦寇救援,結果不料秦穆公利用反間計,迫使鄀國國君對二人失去信任,最終導緻鬥克被俘。不久秦晉兩國反目,并爆發了崤山之役,秦軍大敗而回,秦穆公為了穩住地位,重新與楚國修好,派鬥克作為中間人協調,楚成王采納了秦穆公的建議,但卻沒有賞賜鬥克,鬥克便懷恨在心。而公子燮在成大心病故後本想坐上令尹之位,卻被成嘉搶了先,心中也懷着一股怨氣,是以如今二人聯手,自然會有一番動作。
就在成嘉和潘崇帶兵離開不久,公子燮和鬥克就将楚莊王軟禁,又在郢都城外加蓋城牆,公然反叛。為了早日實作計劃,二人又派出殺手秘密行刺成嘉,卻被成嘉察覺,沒能得手,他們便索性挾持着楚莊王離開郢都,打算逃到商密再進行下一步謀劃。途徑廬邑時,廬邑大夫
戢梨已經得到成嘉密令,他帶着副将叔麇假裝追随鬥克,趁二人不備時将他們一舉拿貨,救出了楚莊王,這才平息了這場動亂。
經曆了這次事件,楚莊王心有餘悸,也更加明白韬光養晦的道理,是以自此以後,他徹底不問政事,心思全花在了飲酒作樂上面。
公元前611年,楚國發生了嚴重的災荒,糧食大面積欠收,整個國家籠罩在饑餓的陰霾下。國内的形勢不穩定,而外面的情況則更加兇險,首先是散居在楚國南面山區的戎人意識到楚國出現危機,趁機反叛,從楚國的西南面出發一路打到了陽丘。
接着北面的群蠻之首庸國也率領群蠻造反,西面的麇國緊跟着積極響應,号召散居在西南的濮人各部在選地集結,密切關注着事态發展,準備随時向楚國宣戰,楚國的申邑和息邑兩地岌岌可危。
不到三個月時間,各地的警報就如雪片一般飛往郢都,楚國在内憂外患之下幾近崩潰,面臨着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
如此嚴峻的形勢,大臣們如坐針氈,天天跑到楚莊王面前請願,可楚莊王依舊無動于衷,我行我素,繼續躲在深宮裡取樂,有時又心血來潮帶着一幫宦官跑出去狩獵,幾天幾夜都不回宮,成嘉、蒍賈等人隻有苦苦哀求,後來楚莊王被說的不耐煩了,幹脆在門口豎起一塊牌子,上面寫着:“進谏者,殺毋赦”。
要說這個辦法果然起作用,前來勸谏的人頓時少了許多,不過好在還是有幾個正直無畏的人。
第一個人是楚國的右司馬,名字叫做伍舉,這一天,他來到楚莊王的後宮,後者正一手摟着妃子鄭姬、一手抱着越國不久前進獻的美女觀看歌舞,看見伍舉走來,楚莊王眼裡露出殺氣,厲聲質問道:“愛卿可看見門口的牌子。”
伍舉不慌不忙的說:“看到了。”楚莊王冷笑一聲:“既然看到了,那你來此何幹?”
伍舉回答說:“我隻是想請教大王一個問題。”這個回答讓楚莊王有點意外,他問伍舉:“什麼問題?”伍舉說:“在我國的土山上面有一隻大鳥,落在那裡已有三年之久,既不飛也不鳴,不知那麼是個什麼鳥。”
楚莊王意味深長的笑了笑,然後慢條斯理的說:“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愛卿的意思寡人已經明白,你可以退下了。”
幾天之後,楚莊王的行為更加放蕩,整日攪得宮殿不得安甯,另一位大夫蘇從實在是看不下去,也冒着生命危險來見楚莊王,楚莊王依舊是當初接見伍舉時候的那般态度,問蘇從說:“大夫可知寡人的诏令。”
蘇從比起伍舉更加剛直,他目光堅定的答道:“臣了然于胸,可作為臣子,我決不能眼睜睜的看着父母之邦滅亡,如果大王能聽從臣的勸告,那臣今日就是死在大殿上也毫無怨言。”
楚莊王對蘇從的态度有些驚訝,又想起之前伍舉的隐喻和自己對他的承諾,當場向蘇從表示自己一定會痛改前非,将心思全部用在治國理政上。
第二天,楚莊王就下令,将後宮那些與國事無關的歌女樂師全部驅逐,又讓人将這些年積攢的奏章上全部拿到他面前,他要一一閱覽。對于當初他享樂時隻顧阿谀奉承的人,此刻大多都被治了罪,而像伍舉和蘇從這樣的則被委以重任。
這就是楚莊王“一鳴驚人”的典故,在《史記》和《韓非子》之中都有記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記》中關于這個典故還有另一種版本,說的是戰國時期的齊威王和他的大臣的事情,大緻内容基本相似,不過根據發生的時間和相關史籍判斷,發生在楚莊王身上應該更可靠一點。
擺在楚莊王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該如何解決眼前的危機。
楚莊王下令召開軍事會議,成嘉、潘崇、蒍賈、蘇從等人紛紛參加,不少人認為,目前形式萬分危急,敵人的攻勢太過兇險,必須盡快遷都以保宮室無恙。
蒍賈馬上出來反對,他對楚莊王說:“我們能逃到阪高,敵人也能追過去,現在敵人之是以嚣張,正是看中我們處于饑荒,認定我軍不敢出兵和他們決戰,我們就該抓住他們這一心理,主動出擊,先集中優勢兵力向庸國發起進攻,麇國和百濮不過是見風使舵之輩,一旦庸人敗潰,他們兩方定然不戰自退。”
楚莊王立即拍案道:“蒍賈之言,正合寡人之意,我堂堂大楚,豈能因這些宵小而遷都,寡人就是要讓他們看到,楚國的天威不是他們可以冒犯的。”
接着楚莊王又問成嘉:“如今國中可以調用的軍隊還有多少?”成嘉仔細算了算,回答說:“除過各地戍守邊境和赈災的,目前國中僅能湊齊兵車一百餘乘左右。”
楚莊王笑了笑說:“對付一個小小的庸國,這些人足夠了,請令尹告知各級将領,明日正午校場集合,點鼓發軍,如有遲誤,一律軍法從事。”成嘉唯唯受命。
第二天,三軍奉命集結,總計一萬多人,楚莊王親自擔任統帥,成嘉和鬥越椒分列左右,大軍自郢都出發,直奔庸國勢力最集中的廬邑方向,得知楚國進兵,百濮果然如蒍賈預判的那樣,很快下令撤兵,麇國也在不久之後向楚國求和,接下來就隻剩下一個庸國。
楚軍們個個士氣高昂,連戰連捷,不到月餘就已經收複十多個被庸國占領的縣邑,每到一處,楚莊王就下令開倉放糧,犒賞衆軍并救濟當地的窮苦百姓,
十天以後,大軍在句澨下寨,楚莊王指令廬邑大夫戢梨率領先遣部隊試探性的往庸國主力所在的方城發動進攻。
由于消息洩露,戢梨在方城遭遇庸軍的埋伏,損失慘重,他的副将子揚窗也被庸國人所俘。
三天以後,子揚窗趁着看守不注意連夜逃回句澨,楚莊王急于探聽方城的消息,第一時間召見了他。
子揚窗将自己所看到的情況一五一十的彙報給楚莊王說:“敵兵駐紮在方城的兵力極為龐大,又有蠻夷助戰,人數恐怕在我們之上,主公應從郢都再次調兵,将全國的兵力全部集中于此,再發動總攻,這樣才有獲勝的把握。”
成嘉聽了反對說:“這可不行,臨行時我已經向大王彙報過,如今我們能動用的部隊已經都在這裡,如果再将戍邊的部隊抽調過來,隻怕方城的危機沒有解除,反而會召來更大的麻煩。”
潘崇眼睛一轉,給楚莊王提了個建議:“臣有一計,不如有意向庸軍示弱,讓對方驕傲,時間一長他們的思想一定會有所松懈,我們再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以我軍之激而敵對方之傲,必然能大獲全勝,當年的先君厲王就是用這種辦法勝了陉隰。”
楚莊王聽完朗聲大笑說:“太師妙計,就依太師之言。”
第二天,楚莊王派鬥越椒、成嘉、戢梨等人連番向方城發動進攻,連續七次都以失敗告終,損失的戰略物資不計其數。
這樣一來,庸國人便覺得楚軍已經沒了往日的氣勢,不需要再過分擔心,于是思想上便松懈下來,外圍的警戒也不再嚴密。
楚莊王很快探知這一情況,他當即率領一支軍隊趕奔臨品,與成嘉等人會師,楚成王将部隊一分為二,一路由鬥越椒率領,從臨品過石溪,另一路由大夫子貝率領,途經仞地向方城包抄。楚軍所過之處,蠻人各部落包括秦軍、巴軍等見其勢力強盛,紛紛出兵支援,以此向楚莊王示好。
等楚國的兩路軍抵達方城時,庸軍正在為上一次擊敗楚國大擺慶功宴,全然沒意識到危險已經降臨,鬥越椒和子貝抓住時機,迅速投入戰鬥,向庸軍發起猛烈攻勢,庸軍在毫無防備之下倉促應戰,但哪裡是楚軍的對手,很快庸軍便向後敗退,死傷不計其數,庸主這時候想組織起一支生力軍來和楚軍做最後一搏,也沒能成功,在楚軍的重重包圍下,庸主隻得投降,楚莊王下令一些年紀尚輕的人之外,其餘包括庸主在内全部斬首,庸國也被納入到楚國的版圖,從此退出曆史舞台。
楚莊王用他令人震驚的雄才大略化解了楚國的危機,但他卻并未是以而到滿足,接下來他将着手自己的下一步計劃,而就在此時,鄭國忽然來信想要投靠楚國,這無疑讓楚莊王驚喜萬分。
那麼鄭穆公為什麼突然會背叛晉國,楚莊王又将利用鄭國進行怎樣的布局?
下一期的春秋典故:“各自為政”将會為您揭曉答案,敬請關注。
(或關注微信公衆号:典故大雜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