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體賦予史德、文德涵意的過程中,章學誠主張文、史相融,著、評耦合,使得《文史通義》的價值不隻停留于史學觀念的闡發,而且也涉及文學理論的闡釋,這就是史德、文德所蘊含的文學著者之德與文學評者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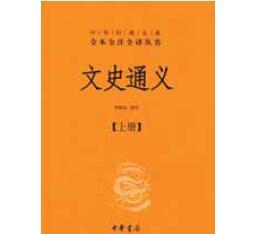
《文史通義》是古代中國史學理論的重要著作,清代學者章學誠在這部書中不僅批判了曆史上的文學和史學,也提出了編寫文史的主張。章學誠在承繼劉知己“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新唐書·劉知幾傳》)的論調之外,另立“史德”“文德”詞條(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中華書局1985版),以彰顯才、學、識不能涵蓋的曆史問題。在具體賦予史德、文德涵意的過程中,章學誠主張文、史相融,著、評耦合,使得《文史通義》的價值不隻停留于史學觀念的闡發,而且也涉及文學理論的闡釋,這就是史德、文德所蘊含的文學著者之德與文學評者之德。沿襲章學誠“史德”“文德”制詞的理路,評者之德便是“解德”,也就是解讀文本時應當遵守的一些原則。
心術要正
對一部作品的接受,有時會存在對立的情況。《西廂記》《金瓶梅》《史記》的接受就頗具代表性。《西廂記》在其傳播史上曾頗受争議:“文者見之為文,淫者見之為淫。”(《增訂金批西廂記》,中華書局1916年版)這種接受情況也出現在《金瓶梅》一書上:“(《金瓶梅》)曲盡人間醜态。其亦先師不删鄭、衛之旨乎?……不知者竟目為淫書,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卻流行者之心矣。”(廿公《金瓶梅跋》,丁錫根編著《中國古代小說序跋集》(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無論是“文者見之為文,淫者見之為淫”的說辭,還是樹“先師不删鄭、衛之旨”的大旗,都是流于現象的陳述,而沒有上升到具有說服力的理論辯護。今人解讀作品,允許存在多元,但事關作品性質判斷,多元有時未必就是寬容。
章學誠在為《史記》非“謗書”辯護時提出的心術要正,頗具一定的理論價值。在其看來,“謗書”是因讀者心不平而加之于《史記》上的“史識”,而非《史記》本身具有“謗書”的性質。換言之,《史記》為“謗書”是讀者的誤讀,也即“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為何讀者心不平會導緻誤讀?章學誠從“氣”“情”兩端予以闡發,認為:“文非氣不立,而氣貴于平”;“文非情不深,而情貴于正。”氣平情正,解讀文本才會趨于理性,行之于文,則文中正平和。反之,若氣失情偏,為文易墜于偏激、驕縱與沉溺。是以,解讀的心術要正要平,方能不因己之氣失情偏而使批評遠離客觀公允。
就《史記》而言,盡管有記錄漢家不善之事,但“言婉多風,皆不背于名教”,是以,以“錄漢家不善之事”概稱《史記》為“謗書”,實乃讀者氣失情偏之所然。同樣,解讀《西廂記》《金瓶梅》時,僅僅沉湎于張君瑞的翻牆及西門慶的行樂,而不顧“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及“有所刺”,那麼,接受的反映必然是片面甚至是錯誤的。
臨文主敬
心術要正指出了氣失情偏帶來的或嬌或溺,并沒有清晰點出以何為正的具體标準。在“文德”詞條中,章學誠提出了“臨文主敬”,彌補了這一邏輯上的缺陷。“臨文主敬”之“文”,泛指“一切文字”。對為文的态度,因“立言”不朽的内在限制,使得多數傳統文人持一種慎之又慎的敬畏。賈島的“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須”,“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紅樓夢》,創作的甘苦昭示了傳統文人“臨文”的不苟。
臨文為何要懷敬畏之心呢?在援引“迎而拒之,平心察之”(韓愈《答李翊書》)與“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的基礎上,章學誠提出了為文應有的姿态:“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心平”才能正,才能夠“合度”,而“度”即規範标準。韓愈強調“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柳宗元認為《詩》《書》對其為文有着綿綿的滋養功能:“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是以取道之原也。”由此而知,韓、柳二人以儒家經書為源,沉潛其中,含英咀華,抹去了自己的“矜氣”“昏氣”等,進而使自己的為文“闳其中而肆其外矣”(韓愈《進學解》)。是以,“臨文主敬”之“敬”是指對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論的捍衛,“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是對自己所持守文化理論的娴熟運用而又不逾矩。
論古必恕
魏、蜀、吳三國成為史家記錄的對象時,是紀魏傳蜀吳,還是紀蜀傳魏吳,不同時代的史家有不同的寫法。陳壽《三國志》與司馬光《資治通鑒》“紀魏而傳吳蜀”, 習鑿齒《漢晉春秋》和朱熹《通鑒綱目》則“起而正之”。一段史事,記錄時前後順序有别,對其進行解讀時讀者也會對陳壽、司馬光的做法提出異議:“論地則以中原為主,論理則以劉氏為主。論地不若論理,故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是以為正也。”(毛宗崗《讀三國志法》)陳壽、司馬光撰寫三國曆史,論地不論理,受到毛宗崗的批評,習鑿齒、朱熹依據尊理疏地的曆史評判原則,“起而正之”,因而深獲認可。這種史識頗為新穎,關涉西晉、北宋的都城方位與東晉、南宋“偏居一隅”而又以正統自居的文化心态。毛宗崗所謂的理,指的就是撰史者要心存正統意識。
如何評述這種摻雜正統意識的曆史現象?章學誠提出了饒有趣味的假設:“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人是生活在一定時空中的人,是以,對人行為的了解不僅要有一定的時空意識,更要有“諸賢易地則皆然”的換位思考。論文要知其世,這是傳統一貫的看法,而論文要知“古人之身處”,則是其一大發明,其内蘊着一定的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意識。知“古人之身處”,才會抱着“了解之同情”去了解其身處曆史的所作所為,這也就是章學誠所謂的“論古必恕”:“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如是,圍繞三國曆史寫法引起的評議,才能擺脫“尊理疏地”的偏狹,使得“理”既具有正統的意涵,又涵括撰史者不得已而如此的“當代”情境。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古必恕”提出了對待曆史的評述要賦予古人“了解之同情”;“心術要正”“臨文主敬”指出了深耕儒家經典才能有所守有所棄。在韓愈、柳宗元看來,持守傳統儒家的道統,才能避開世事複雜帶來的紛擾,撰文立論時才會不為“矜氣”“昏氣”等所蔽。
創作與解讀不是随心所欲的,“取道之原”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持守,而有不同的持守也就會有不同的“合度”。章學誠提出的“心術要正”“臨文主敬”“論古必恕”的解讀原則,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并非完美。在對“史德”“文德”的具體展開中,其站在儒家立場,指點“文史”,溯古求源,盡管學理滿滿,但也難掩崇古的好尚。回瞻章學誠提出的解讀三原則,“心術要正”“臨文主敬”關乎着操持的批判武器及與之相對應的立場。批判的武器偏了,立場自然會歪。“論古必恕”,意在“今人”論古時要回到現場,不作“今人”異地異時難為卻苛求“古人”理當如此理當不如此的輕薄之論。就此而言,章學誠的解讀原則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放之當下,對解讀中出現的解構曆史、虛無曆史以及臨文草率、心術不正等現象的評判,不無一定的借鑒價值。
原标題:《文史通義》的文學理論價值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建旺
聲明:本文圖檔來源于“東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