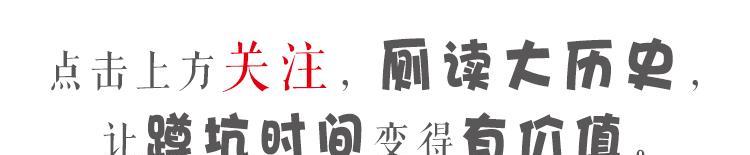
19世紀的東亞風雨飄搖,不僅中國處于内憂外患之中,東邊的近鄰日本也困頓不堪。為了救亡圖存,日本長州、薩摩兩個藩的愛國志士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推翻了僵化的德川幕府。西鄉隆盛、坂本龍馬、木戶孝允等,出身低階武士的政治家完成了一場偉大變革,史稱“明治維新”,後來西鄉隆盛卻起兵反抗明治政府,背叛了改革,表面上看是一場叛亂,實際上是日本“西化”與“革舊”精神的一次激烈沖突。
19世紀的日本下層武士生活很悲慘,雖然他們有固定的俸祿,但金額在不斷上漲的物價面前不值一提,甚至有時連這點錢也會被削減,因為武士的主人大名也陷入了财政危機,隻能“拖欠工資”。
迫于生計,許多武士放下體面,将花園改成菜園,或直接從事手工業,而那些恪守職責,保持自尊,不願從商的低階武士,隻能羨慕别人的财富,而自己過着拆東牆,補西牆的悲慘生活。商人階層雖屬于社會的“下層”,卻因為職業收入高,過得比武士好多了。社會身份和待遇之間的巨大差距,讓武士們内心憤懑,愈加對幕府不滿。
除了武士,農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去。1833年,在天災人禍的接連打擊下,日本爆發了慘絕人寰的“天保大饑馑”,至少數十萬人死于饑荒和瘟疫。米商借天災囤積居奇,大發“國難财”,政府卻放任壟斷,與之沆瀣一氣。憤怒的人民将矛頭指向了無能的德川幕府,在各地組織叛亂。深感危機的幕府雖然試圖以“天保改革”回應,但因為積弊日久,收效甚微。看到改革無效,群眾進一步失去了對幕府的信心。
西方憑借船堅炮利橫行東亞,在1840年的鴉片戰争中強行打開了中國國門。1853年,美國海軍準将佩裡率艦隊駛入江戶灣,踹開了日本國門,一年後與德川幕府簽訂“神奈川條約”,至此,日本維持200多年的鎖國政策正式結束。
後來幕府又在列強壓力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懦弱的妥協被日本人視為國家的奇恥大辱,重挫了幕府的威望,也使廣大國民嗅到了一絲日本淪為半殖民地的危機。
内憂與外患接踵而至,德川政權手忙腳亂,既無法處理内部的社會問題,也無法對抗外來的侵略者。面對山河飄零的現狀,日本人強烈希望來一次徹底的改革,一次震驚曆史的“改世”。
位于日本西南的長州、薩摩兩藩,民風剽悍,從古至今都是愛鬧事的刺頭。這裡的低階武士,對幕府與外國人造成的亂局十分不滿,是以以愛國主義為出發點,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這群“志士”主張推翻“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幕府,将權力交還給天皇,并驅除外國勢力,維持國家主權完整。
他們狂熱地執行對西方人的敵視活動,四處破壞外國人的财産,還在1864年策劃了一次失敗的政變。此舉引來了外國的報複與幕府的彈壓,但幕府此時早已日薄西山,無力控制因改革成功而日益強大的各地諸侯。
就在幕府試圖通過外國協助,建立現代化的軍隊以自救時,西南二藩也簽訂了“薩長同盟”約定共同對抗幕府。同時,由于帝國主義的全面入侵,日本的社會經濟瀕臨崩潰,各地都爆發了動亂。
混亂的頂點是1867年名古屋的“可好啦!”之亂,在持續數月的騷亂中,男男女女沖進商人和地主家,搶奪酒和食物,然後在大街上跳舞喝酒。這些百姓因對社會徹底絕望而癫狂,為了抒發情感與希望,他們編了一首歌:
從西方,長州蝴蝶飛進來; 從橫濱港,金錢湧出去。 有什麼不可以呢? 好啊!這樣不好嗎? 這樣可好啦!
看到整個社會已經忍無可忍,1867年11月,長州、薩摩、土佐、佐賀四藩宣布“大政奉還”,要求幕府将政權交還給天皇,是以與幕府正式爆發了被稱為“戊辰戰争”的内戰。不過,随着“可好啦”之亂擴散到全國各地,整個社會失去了組織能力,德川幕府人心盡失,完全無法與西南雄藩一戰。
戊辰戰争中薩摩藩武士
1868年1月3日,藩兵進入京都,4月幕府的根據地江戶投降,改名東京,1869年所有抵抗結束。統治了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正式終結,西南諸藩出身的低階武士,以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為首的愛國志士成為了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
戊辰戰争後,新的當權者明白艱巨的任務才剛開始,他們認為隻有徹底改革才能使日本脫離困境。比如伊藤博文在回憶錄中說,他們的目标是“繁榮、力量、文化”并且讓日本“在平等的基礎上被認可為世界上最強大、最文明的國家之一。”
為了實作這個目标,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日本新政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社會改革。改革派大緻按照三個步驟進行了自上而下的維新運動。
第一、廢除過去将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階層的做法,重新将社會分為貴族——華族,士族——進階武士,平民——廣大群衆,此後又陸續撤銷了關于職業與社會關系的諸多限制。
第二、廢藩置縣,實行中央集權。收回各地大名的權力,改為中央指派專人管理各縣,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第三、建立以征兵制為基礎的新軍隊。削減武士俸祿,剝奪武士帶刀的權力,結束了武士作為職業軍人的曆史任務。
可以看出,以上三條都在學習西方,第一條企圖建立西方式的市民社會;第二條模仿西方列強的政權組織形式;第三條通過建立新軍,積極向西方軍事系統靠攏。
由于步子邁得太大,這場大規模改革引起了民間一片嘩然,除了零星的民變,較嚴重的叛亂還是由不甘沒落的武士發起的。原因顯而易見,武士們剛剛幫助新政權打敗幕府,一轉身就被打翻在地,深感被新政府背叛的武士,紛紛聚集在了西鄉隆盛身旁。
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雖是戊辰戰争中的英雄,倒幕派的旗手,但他骨子裡卻是個活在過去的老武士,倔強地堅持傳統。是以,在跟新政府産生嫌隙後辭官回鄉,由于他身上濃重的武士氣息,并公開建立武士學校,心懷不滿的武士都來投奔他,他俨然成了舊武士的精神領袖。
武士與新軍的戰鬥
大量認為被明治政府背叛的武士圍繞在西鄉隆盛身旁,這些人撺掇他傭兵起義,最後西鄉隆盛不太情願地在鹿兒島揭竿而起,反抗自己一手拼殺出來的新政權,這就是1877年的“薩摩之亂”。然而,西鄉隆盛率領的武士卻不敵由平民組成的現代化新軍,最終戰敗自殺,他的失敗是保守勢力最後的負隅頑抗,戰争的失利也象征着武士時代的正式結束。
實事求是地說,明治維新不能了解為單純的“西化”。很多關鍵的改革比起模仿西方,更像是急于祛除過時舊制度的權宜之計,維新派為了實施更符合社會經濟環境的政策,不得不壯士斷腕,革故鼎新。即使是純西方背景的政權組織形式與經濟改革,明治維新也不照搬西方制度,而是根據日本獨特的國情,采取了一種漸進式的的操作方式。
西鄉隆盛等保守派的不甘與憤怒,相對于“西化”,他們更讨厭“革舊”,他們尊重傳統,維護傳統,并按照傳統生活,而所謂的傳統是根植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中的血脈,任何人都不會輕易放下。但退一步說,如果抱殘守缺,認為過去的傳統動不得,恐怕當社會危機尾大不掉的時候,傳統将在巨大的動蕩中完全毀滅。與其最終後悔不疊,不如趁着還能選擇,主動改革傳統以适應新形勢,這樣傳統就會以另一種方式生存下去。但是保守派的自命不凡阻止了他們接受新事物,傲慢的态度堵住了跟維新派和解的希望。
此外,西鄉隆盛之是以抗拒“革舊”,不僅因為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忠誠,還在于他的性格。西鄉隆盛曾對坂本龍馬說:“你前天所說的和今天所說的不一樣,這樣你怎麼能取信于我呢?”坂本龍馬回答:“不是這樣的。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鄉,你一旦決定一件事之後,就想貫徹始終。但這麼做,将來你會落後于時代的。”
從二人的對話我們能管窺一斑西鄉隆盛的性格:堅持、倔強,不肯輕易改變。他自始至終都堅持武士精神,雖然為争取下層武士的權益與地位來回奔走,是一個負責任君子的所為,然而他沒有從宏觀角度思考日本的前途,在危如累卵的苛刻國際環境下,明治維新是日本難以放棄的的生存道路。不管是“西化”還是“革舊”,本質上是日本的自救行為,西鄉隆盛執着于對抗“革舊”,等于對抗改革的浪潮,唯一的結局就是失敗。
參考資料:《簡明日本通史》依田熹家
《日本史》康拉德·托特曼(conrad totman)
《日本史》約翰·w·霍爾(john w hall)
《明治維新》威廉·g·比斯利(william g beasley)
《現代日本史:從德川時代到21世紀》安德魯·戈登(andrew gor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