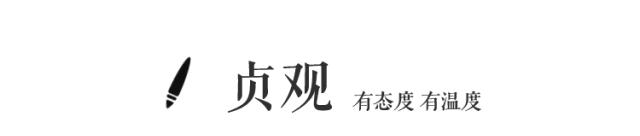
前幾天(11月1日)看到本地公衆号陝光燈發了篇《小雁塔南廣場的唐風雕塑背後,是一個怎樣的盛唐?》文中對小雁塔南廣場新修雕塑群的曆史原型、設計問題,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問和建議。
轉發朋友圈後,有人說讓他想起了清華博士生徐騰演講中提到的河北易縣奶奶廟,也有人說大晚上去看的話會不會被吓哭,更有人說這是把蒙娜麗莎捏成泥塑。審美這事仁智各見,我更關注的是這座疑似玄奘法師的塑像。
1
這座雕塑是取材于《玄奘負笈圖》,我們在各種書上、影像裡都能看到。
圖中僧人竹笈赤腳芒鞋、風塵仆仆,确實像一心向佛、萬裡前行的玄奘。然而稍加留意,我們就會發現疑點重重:
1. 長相。西行時玄奘不到三十歲,年富力強,而圖中圓臉彎眉,長眉毛一般會認為是表現老人長壽,有些不符。
2. 骷髅頭。原圖顯示脖頸處挂有九個骷髅頭。在密宗中,骷顱多和怒目兇神相關,和中土佛教規制完全不同,也隻有沙和尚那種妖怪才佩帶。很難想象作為法相唯識宗祖師的玄奘會佩帶骷顱項珠,穿過層層城池村寨一路西行。看目前塑像這個造型,大機率設計師根本不知道這是骷髅頭,否則不會改成這樣。
3. 竹笈。大家印象最深,應該是電影《倩女幽魂》中甯采臣的扮相,這在《清明上河圖》中也有類似,貨郎身背笈箧走街串巷。但此類造型集中出現在唐末到宋元,後世更多在日本流行。古人遠遊一般牽乘家畜馬車,徒步攜帶行李的話多用布質包裹或者褡裢一類。比如雕塑身後随行弟子,就是這樣攜帶行李,隻是想不通為什麼會扛根比行李重得多的樹杈。
4. 耳環。我們很難想象除了鸠摩智這樣西域番僧以外,哪個中原和尚會帶耳環?
5. 衣服紋飾。僧衣一般都是純色衣服,即便有花紋,也是萬字紋、回字紋等極其樸素的裝點,而這樣華麗的服飾,邊角繡花,胸前還有精美絲綢裹肚,不是本土風格,更不應該是行腳僧人所應有的。
6. 草鞋。中國傳統草鞋由麻繩編織,而不是圖中這樣的皮條。
■ 左:雕塑上的草鞋 | 右:中國傳統拖鞋
7. 佩劍。古代僧侶出門有帶戒刀的傳統,尺寸短小放于行囊,用于裁減衣物、修理頭發、切割食物使用。塑像上的長度和形制,更符合古代實戰武器尺寸,劍鞘是很清晰的明清時期式樣。 出家人慈悲為懷,不大可能出行佩帶兇器。
■ 佛典要求戒刀不應尖直,敦煌壁畫顯示應為近似右圖這種剃刀
很顯然,這個“玄奘标準像”疑點重重。
2
那這個形象從哪兒來的?
這個形象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有兩個,其一為絹本設色畫,繪于鐮倉(1185—1333)後期,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也就是小雁塔南廣場目前這尊塑像的母本。
其二為線刻石碑,就在玄奘法師靈骨塔所在地興教寺。
最早對這幅圖像進行系統研究的是日本學者松本榮一,此後還有王靜芬、李翎等中日學者紛紛參與其中。
中國古代有行腳僧主題的流行畫,番僧模樣身負竹笈手執棍仗,腳下往往還有隻老虎豹子之類猛獸,有人也認為這是伏虎羅漢的最初形象,類似圖案在敦煌有很多。
■ 敦煌莫高窟 唐代《行腳僧圖》
《玄奘負笈圖》應該是從這個母題借鑒演變而來,是結合運用日本元素進行二次創作的結果。其實在元代時候日本人創作的玄奘形象,也還都是傳統僧侶形象,是以可能原作者在創作時,畫的就是一個普通的行腳僧人,或者是伏虎羅漢,隻是後來日本人将其附會為玄奘。
■ 元代 奈良藥師寺藏玄奘取經圖
近年敦煌研究院專家在壁畫中發現6副《玄奘取經圖》,可能更接近當年人們心目中的玄奘形象。
1933年一位叫歐陽漸的著名居士把這幅日本絹畫的圖案引入中國,刻在興教寺的石碑上,拓片廣為流傳。尤其是角上清楚寫着“玄奘法師像”,更讓人深信不疑,随着現代印刷術和網際網路發展,使得它逐漸成為中文世界裡的“玄奘标準像”。
近些年,很多人都認識到這個問題。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早年間曆史課本中的“玄奘像”是這樣子的:
到後來,修改為郵票的畫面。
對比郵票畫面和日本絹畫,明顯看到,面部修改年輕了,衣服改為傳統僧袍,點綴了些西域元素,裹腿和鞋子也改成中國式樣,骷髅頭改為佛珠,腰部佩劍改為拐杖,說明中國郵政在設計時已經注意到原畫中不合常識的一些問題,在照顧人們慣有認知下,做了很多細節修改。
再看同一套郵票中老年玄奘法師形象,更了解設計思路。
3
玄奘具體長什麼樣子,史書中也有記載。
14歲出家時候,剃度官員就看他儀表堂堂相貌不凡,“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他個子很高,風度很好,既溫文爾雅,又氣宇軒昂。
在戒日王為他舉行十八日無遮大會上,因為學識淵博能言善辯,一時無人與其争鋒,是何等的意氣風發。被印度各學者尊為“大乘天”,也就是大乘佛教的神。即使他回國後50多年,很多僧寺供奉着他鞋子以及生活用品的畫像,“每至齋日辄摩拜焉”,奉若神明。
西行路上與各國王公貴族談笑風生,回國後拜見唐太宗,因其談吐高深舉止娴靜,第一次見面兩人就聊了一天。《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結尾頌贊他“迥秀天人”、“恢恢氣宇”,而塑像中這個肥頭大耳、目斜眼歪的形象,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大雁塔南廣場的玄奘銅像,對玄奘法師形象複原就比較好,目光堅定,法相莊嚴,手執禅杖,身體前傾顯得意志堅定,較符合史書上的記載。
大雁塔地鐵站裡絲綢之路主題壁畫中的玄奘圖案,比起小雁塔南廣場塑像,更接近日本原畫。
比如手中佛塵,可能因為原畫中佛塵前面的毛和畫面背景很接近,讓設計師給忽略了,也可能誤以為是變形的扇子,在小雁塔南廣場塑像,玄奘右手就隻剩下一個不知是以的搖桿。
長期以來,國内在進行曆史文化複原時候,誤把日風當唐風的現象比比皆是。雖然我們一向認為現在的日風,來源于唐風,但要說“正宗唐風在日本”,把日本的東西直接搬過來冒充唐代風格,有些太不講究了吧。
4
唐初之時佛教在中國已經傳播幾百年,各種典籍較多、譯本互異,年久學殊而繁,常常發現理論之異。玄奘發願去佛國聖地朝拜研習佛法,核實漢譯佛經中的偏差,一去就是十九年。
曾經穿越戈壁荒漠,曾經四天四夜滴水未進,正如邊塞詩人岑參所寫的“黃沙碛裡客行迷,四望雲天直下低。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曾經遭遇劫匪,險些喪命,也曾被人強制挽留,最終絕食相抗才得以繼續前行;穿越天山雪域,遭遇雪崩,一路險象環生,曆盡千難萬險,最終求取真經。
645年正月,玄奘法師回到長安。朱雀大街上人潮洶湧,身在洛陽的唐太宗李世民派丞相房玄齡率百官前來迎接,長安城百姓穿着最好的衣服,點燃香火、抛灑鮮花,各個寺廟的僧侶布置好幡賬、寶案,莊嚴肅穆誦念經文夾道歡迎。
玄奘精通梵文,洞曉三藏,是佛教史上達到最高成就的人物之一。随着《西遊記》的廣為傳播,說他是中國最著名的和尚也不為過。
唐代律僧道宣法師評價他:聽言觀行,名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性;不倨不谄,行藏适時;吐味幽深,辯開疑議。實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将矣。
玄奘是一個完美無瑕的典範,有着常人罕見的意志,無論是學術成就還是個人修行,都已近乎超凡。梁啟超贊譽他為“千古之一人”, 魯迅更是稱他為“中華民族脊梁”。
玄奘法師從現在高新城市客廳的大興國禅寺出發西行,回國後長期在玉華宮和大雁塔譯經,最後靈骨安葬于興教寺,他在西安留下很多足迹。對于西安,玄奘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資源,弘揚玄奘精神也是一種文化擔當與責任,紀念其人其事,弘揚其行其果,裨益世道人心。
之前有研究者甚至認為這畫的就是一個日本貴族的形象,與玄奘完全無關。當然,建設者也可以說這不是”玄奘“,他們隻是塑造了一個日本古畫中的人物形象。将這樣一個有争議的塑像矗立在西安世界文化遺産區域、著名曆史文化地标位置,恐怕是不合适的,何況在小雁塔薦福寺譯經的是另一個大師——義淨法師,而非玄奘。
附其他據說根據唐代壁畫、繪畫、陶俑設計的塑像,僅供欣賞:
作者 | 連艮 | 貞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