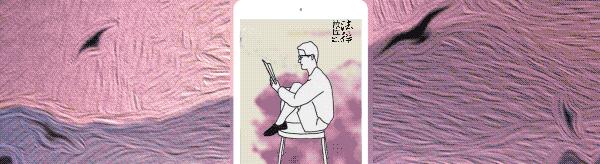
來源:麥讀
我們之中有誰真正了解他的兄弟?
有誰探索過他父親的内心?
有誰不是一輩子被關閉在監獄裡?
有誰不永遠是個異鄉人,永遠孤獨?
— — —托馬斯·沃爾夫《天使,望故鄉》
法律人永遠追求正義,卻無往不在面對不義的漩渦之中。盡管在同一案件中,不同的法律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擔着不同的職能,但我們始終有一個共同的職業信念,就是懲惡揚善,讓正義得到伸張。
殺人是人類曆史上最古老的罪行,在《聖經·創世紀》中,就記載了人類遠祖該隐殺死亞伯的罪行。殺人,也是人類最難容忍的不義,“殺人者死”正是對此最強烈直接的表達。但文明發展到今天,殺人不僅未曾絕迹,反而因為暴力工具的發展,慘烈程度更加駭人聽聞。
在那些至暗時刻,年輕的妻子被丈夫分屍36塊後烹煮,男子搶過超市推車裡的嬰兒活活摔死,血肉至親一夜殺死全家六口包括兩個親生兒子,還有在校園門口發生的慘烈屠殺,以及“獨狼”面對度假人群的瘋狂掃射……
一個又一個讓人驚恐的社會新聞,伴随着大量真實的圖檔、視訊,共同挑戰着人們的心理底線。邪惡現身之處,令人窒息。
更可怕的是,這些案件的兇手,還曾被周圍的鄰裡相識描述為「踏實穩重,待人随和」「挺善良老實的一個人」「想不到他會做出這種事」。也就是說,作案之前,他們看起來,跟我們身邊的普通人,并沒有什麼不同。
每次看到這些暴力案件,我都忍不住會想:
他們為什麼殺人?
當他們下手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
是什麼激發了一個普通人内心的兇殘,讓他變成一個殘忍的殺人犯?
在一起起殺人事件中,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原因在發生作用?
還有,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們能為減少暴力做些什麼?
至少,如何從這些暴力中幸存?
一個人生病了,負責的醫生不隻會做出正确的診斷,還會努力探尋疾病的成因,才有希望從源頭上根治。同樣,面對一個個暴力兇殺案件,一定還有許許多多的法律人,也像我一樣,想要更深入地了解人,了解人與社會的互相作用,了解犯罪行為本身,想要知道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
這也就是為什麼,麥讀譯叢系列的第7本,我們選擇了引進這本《他們為什麼殺人:人們何以變得暴力,我們對此能做什麼》。
在這本書裡,朗尼·阿森斯,一位在家暴中長大的犯罪學家,在深度訪談了數百名暴力罪犯後,簡潔有力地指出了一個普通人走向暴力化的關鍵。它讓我們了解,一個極端兇殘的殺人者如何在社會中誕生,我們每個人能夠為此做些什麼。
家暴中長大的犯罪學家
朗尼·阿森斯出生于一個充滿争吵與暴力的家庭。他的母親是一名金發、嬌小柔弱的白人女性,父親則是手臂強壯有力,長得像摔跤手的「希臘佬」。在童年和青春期,朗尼和母親是父親主要的施暴對象。
他還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母親讓他洗頭,他不樂意。一旁的父親就直接提起他的雙腳,把他整個人倒過來,頭浸到馬桶裡,然後沖水,沖水,一次又一次。
「我以為我就要被他溺死在馬桶裡了。」他後來回憶到。
長大後的朗尼,選擇了犯罪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一次,他回鄉參加姐姐的婚禮。婚禮上,他忍不住跟罵罵咧咧的父親吵了起來。父子倆越吵越兇,最終,他跳起來,一拳砸在了父親的臉上,然後跨坐在他身上,不停揮拳錘打,直到旁邊的人們把他拉下來。
萬幸,父親傷得不重。但這樣的經曆,讓他愈發想知道,到底是什麼驅動着一個人使用暴力去傷害另一個人?他也想知道,自己的暴力行為意味着什麼?為什麼自己會做出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還會再發生嗎?
罪犯獨白:走近兇惡靈魂的深處
進入犯罪學領域後,朗尼驚訝地發現,彼時那些理論型的犯罪學家,被社會認定為是刑事暴力的專家,自己卻從未有過任何暴力相關的體驗,也沒有真正接觸過暴力罪犯。
「他們的理論很難讓人信服。」朗尼認為。
為了了解罪犯們的真實心理,獲得一手資料,他不帶武器,孤身進入監獄,與數百名暴力罪犯面對面深度訪談,傾聽他們的内心獨白,真正走進了那些世界上最暴虐、最兇惡的靈魂深處。
「我想采訪那些暴力犯罪者,聽他們誠實地說說自己,說說自己的暴力故事,從他們那裡獲得真正的資訊。」
案例 2:刑事殺人
X和我已經一起旅行一個多月了,沖突越來越多。我開始厭煩他的大嗓門,他喜歡誇誇其談,還老是擺出一副強者姿态。我想早晚有一天我會受夠他的。我們在一處鐵路調車場停下來,開始嗑藥。他又像往常一樣開始吹起牛來,說着他和多少女人上過床,他多會開車,他教訓過多少男人。他想讓我聽他的話,但我能看出來,他其實沒那麼厲害: 不過是在撒謊罷了。他還端着那副強勢的架子,用風流浪子的口氣,說着這個妞兒那個妞兒。我開始厭惡他的聲音,他說話這麼響,震得我後背發麻。他開始表現出一副随時能把我打趴下的樣子,把我的沉默誤當作懦弱,然後他抓住我。
我說: “你跟人說話時,能不能不動手抓人?” 但他還繼續這麼做,我不知道他之後又說了什麼。因為我已經沒在聽了。在想着我最好向他證明,他其實沒那麼厲害,我讨厭他。他老把我當作一個懦夫,這讓我很惱火,我要打消他的氣焰,于是我說: “你再動我一指頭,我就開槍打你!” 他說: “你才不會開槍打我。” 我不喜歡他質疑我,我知道他還要來碰我,當他再來碰我時,我就快速朝他開了一槍。
案例 9:
有天晚上,我被父母卧室傳來的巨大響聲吵醒。我想先去洗手間喝杯水,再搞清楚發生了什麼。我走去洗手間的路上,聽到我母親說: “不要,我告訴過你不要這麼做,我不喜歡這樣。”
我自己思忖,他能對她做什麼?我開始努力想要聽清楚,我母親說: “請不要再對我這樣了!很痛!” 他卻說: “老子可不管你痛不痛!” 接着我母親尖叫起來: “快停下來,痛,太痛了!馬上停呀!别再繼續了,停,停!” 她哭了一會兒,痛得尖叫出來,接着又開始哭。
我回到自己房間,知道他一定把她弄得很痛,才讓她叫成這樣。我感到暴怒,簡直想殺了他,我想過要進去,把他從她身上拽下來,狠狠揍他一頓,但他對我來說太高大了我根本打不過。我知道自己什麼也做不了,隻能希望他住手,但他沒有。我躺在床上,聽着她哭泣,感覺很糟。因為自己什麼都幫不了她,我想把他弄下來,揍他,但我太膽小了。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就是一個小孬種,然後我試着繼續睡覺,假裝這一切隻是一場噩夢。
就這樣,在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案例中,在謊言與記憶編織的迷霧中,朗尼對樣本資料逐一分析求證,不斷探尋着心靈的真相。最終,他發現,一個普通人走向暴力化,會經過四個标志性的階段。這一程序,環環相扣,往往發生于犯罪者的内心,不被人察覺。然而,任何人,當他一步一步通過這四個階段,就會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冷酷無情的施暴者。至此,一個極端暴力的殺人者,已經成形。
這是一本令人不安的書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令人無法抗拒……你會被本書的一些結論和迷人的叙述所震驚。
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
令人不安,極富挑戰,但非常吸引人。
亞特蘭大雜志(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
羅茲值得推薦……不僅因為他又寫了一部精彩的著作,也是因為他讓我們了解了朗尼·阿森斯特立獨行的學術發現。
堪薩斯城市之星(The Kansas City Star):
必定會引起讨論,他們為什麼殺人是讨論一個重要議題的引人入勝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作者寫道:
當人們觀察一個危險的暴力罪犯時,如果着眼發展階段早期,就可能出乎意料地發現,這個危險暴力犯罪分子,起初可能是一個相對善良的人,更能讓他們産生同情而不是憎惡。更重要的是,人們會得出結論: 危險暴力罪犯的養成是大可防止的,與許多人類屠殺事件一樣,它們都是從無到有一環扣一環産生的。
愛因斯坦說:終将能夠毀滅人類文明的是我們内心的邪惡力量。
法律和道德都無法消滅邪惡,如果不能直面暴力犯罪的全部真相,如果不能阻止個體「暴力化」的程序,那麼我們每一個人,以及這個社會,就會成為默默培養他們的幫兇。一隻伸向那個快樂、陽光、敏銳、可愛孩子的援手,也許就能讓我們免受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恐怖利劍。
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