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了改革弊政,推行新政,大刀闊斧,力排衆議,借助皇帝的支援,将一個又一個政敵逐出權力中心,排擠出朝堂,流放邊陲。
他,發現推行新政的弊病,不顧個人得失,上書言事,反對新政,觸怒了一心改革、推行新政的皇帝,最終被貶谪到南疆蠻荒之地。
他們,是政治上的死敵。然而,當磨掉權力的棱角,抛開各自的政見,他們又成了彼此欣賞、詩詞唱和的好朋友。
他們就是“熙甯變法”的主導者王安石,和“烏台詩案”的主角蘇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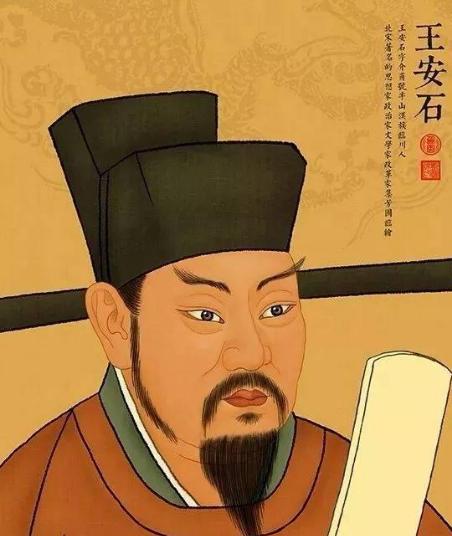
王安石和蘇轼有一個共同的身份——詩人,而且還都是大詩人。這兩位大詩人之間,有着複雜的政治關系和人生交集,卻共同樹起一座時代的豐碑——宋詩。
在《莫砺鋒講宋詩課》一書中,南京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莫砺鋒先生為我們生動地講述了很多宋朝詩人們鮮為人知的故事,同時,也為我們認真剖析了宋詩之是以能繼唐詩之後,獨樹一幟的深層原因。
後人對于王安石的認知,更多的是源于他所主導的“熙甯變法”,而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重身份——詩人。即便對他的詩有所了解,也大都停留在“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這樣的詩句裡。而莫砺鋒先生在他的書中告訴我們,王安石不但推行了一場規模巨大的變革運動,而且,還是宋代詩風的開創者之一。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這是王安石所作的六言詩《題西太一宮壁二首》。相對于五七言詩來說,六言詩缺乏單雙音步交疊的變化感,顯得單調呆闆,是以,唐宋詩人很少寫六言詩。宋朝詩人洪邁就說過:“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由此可見,六言詩是很難寫好的。然而,王安石寫的這兩首六言詩,卻被近代文學家陳衍評價為:“絕代銷魂,荊公詩當以此二首壓卷。”
當大文豪蘇轼蘇東坡在西太一宮看到這兩首詩後,“注目久之,曰:‘此野老狐精也。’遂次其韻”。蘇轼稱王安石為“野老狐精”,意思是說他無所不能,這是一位大詩人對同代詩人由衷的欽佩。蘇東坡在次韻詩中感歎道:“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萋迷。”
作者在書中也因之發出感慨:“政治上的歧見會使人們産生對立情緒,而‘絕代銷魂’的詩歌佳作卻能拉近心靈的距離。”
當蘇轼感歎王安石的無所不能,提筆寫下和詩的時候,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因抵觸“熙甯變法”而遭受的“烏台詩案”之痛。想當初,蘇轼被貶黃州,孤身一人,舉目無親,何等凄涼!在落寞之際,蘇轼在一座小土山上發現了一株海棠,使他想起了千裡之外的家鄉蜀地。因為海棠花是蜀中的名花。睹花思鄉,他把自己的滿懷愁緒都對着海棠傾吐了出來:
“江城地瘴蕃草木,隻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寸根千裡不易緻,銜子飛來定鴻鹄。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這首詩很長,就如同詩人的懷遠思鄉之情一樣悠長。這裡我們隻選取其中的首尾兩段與您分享。相對于:“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這樣的名句,可能蘇轼的這首詩并不為人所熟知。然而,蘇轼對自己在情緒極度低落之際寫下的這首詩卻是極為看重,視為平生得意之作。正所謂“政壇失意,詩壇得意”。
其實,豈止蘇轼政治生涯坎坷不平,政治強人王安石又何嘗不是如此!
“懷抱難開醉易醒,曉歌悲壯動秋城。年光斷送朱顔老,世事栽培白發生。三畝未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行。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争。”
在這首詩中,王安石發出了“懷抱難開,曉歌悲壯”的強烈感慨。為了實作變法圖強的夙願,他二度拜相,屢遭诋毀,功業未就,終老鄉野,眼看着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功虧一篑,付之東流,心情何等郁悶!然而,紅塵縱無路,心中尚有詩,從政治的枷鎖裡解脫出來,投入到詩歌的懷抱中,又何嘗不是一種全新的人生境界!抛開二人胸懷天下、憂國憂民的政治襟抱不說,單從他們在唐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言,也足以令人敬仰。
在政治上喜歡挑戰難關的王安石,同樣也喜歡挑戰詩詞的難關。莫砺鋒先生在書中給我們講了一個王安石與蘇轼“鬥詩”的小故事。
王安石看到蘇轼寫的《雪後書北台壁二首》詩後,見二詩分押“尖”“叉”二韻,韻險而語奇,不由見獵心喜,一口氣和作了六首押“叉”字韻的雪詩,真是名副其實的争奇鬥巧!
古人喜歡詩詞唱和,這固然是一種交流樂趣,其中卻也隐含着互相比試、一較高下的意味。在《莫砺鋒講宋詩課》這本書中,作者分别将唐詩和宋詩以及宋朝的詩人之間進行了不同層面的比較和評論。
作者認為,後人多将唐詩與宋詞并列,稱為文學史上的“雙峰”。實際上,宋詩也有其與唐詩迥然不同的獨特風格,其文學地位并不亞于前者。作者這樣講述二者之間的差別:“與唐人相比,宋代詩人的生命範式具有冷靜的、理性的、腳踏實地的特征,呈現為一種超越了青春躁動階段的成熟狀态。與唐詩相比,宋詩的情感強度稍嫌不足,但思理的深刻則獨緻高境。宋詩不追求高華絢麗,而以平淡美為藝術極境,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詩除了理性特征之外,還有一個與唐詩截然不同的特征:以俗為雅。用蘇轼的話說就是:“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熔化耳。”也就是說,人們平時說的家常話,都可以寫入詩裡,不過需要詩人将其由俗化雅。對于唐人來說,俗字俚語入詩是詩家大忌,也就是杜甫等極少數人偶爾以俗字俚語入詩,就連劉禹錫重陽日作詩都不敢用俚俗的“糕”字。為此,宋朝的詩人宋祁還作詩嘲笑他:“劉郞不敢題糕字,虛負詩中一世豪。”
相對于趨雅避俗的劉禹錫而言,蘇轼似乎簡直太俗了。因為他竟然以“牛矢”入詩!“牛矢”這兩個字,在我們現代人看來好像沒什麼不雅,但是,如果翻譯成現代文字的話,您就明白它為什麼不雅了。因為,“牛矢”就是我們現代人說的“牛糞”!那麼,蘇轼的這首詩是不是很俗呢?讓我們先來讀一遍,再下定論。
“半醉半醒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複西。”
這首詩的意思大緻是這樣的,詩人喝得半醉半醒之際,到幾個黎族朋友家裡走訪,回來的時候,暈暈乎乎地走在竹刺藤梢之間,迷了路。怎麼辦呢?循着地上的牛糞軌迹尋找回家的路吧,因為,詩人的家就在牛欄西邊再往西去的地方。
乍一看,牛糞牛圈都入詩了,貌似很俗,再細細琢磨,但見詩人之質樸率真可敬可愛,竟無一絲俗氣。為什麼?與蘇轼齊名,共同提倡“以俗為雅”的黃庭堅給出了解釋:“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所謂雅俗之别,在于人的心境和視角。俗人看雅物,隻當作俗物;雅士看俗物,可生出雅興。
兼具理性和以俗為雅兩大特征的宋詩,因其獨特的風貌樹立起一座時代的豐碑。這座豐碑的創立者,不止王安石和蘇轼,還有詩風平淡的梅堯臣、曉暢委婉的歐陽修、雄放直率的蘇舜欽、生新别緻的黃庭堅、簡樸古拙的陳師道,以及兩宋時期的諸多優秀詩人。
曆史的河流時而緩緩流淌,時而浪花奔湧。那些胸懷家國天下、腹有奇麗詩文的詩人們,已然将生命彙入這條河流之中,漸漸逝去。而宋詩這座文學史上的豐碑,卻并未因創立者的逝去,河流的沖刷而消磨浸蝕,始終如燈塔般巍然屹立在煙雨迷茫的河渡頭。那一個個響亮的名字,也永久地镌刻在這座豐碑之上,熠熠生輝。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用生命寫就的詩句,或許可以作為這座豐碑最好的注腳。
《莫砺鋒講宋詩課》給了我們一個近距離瞻仰這座豐碑的機會。讓我們與作者一道,走進宋詩,走進那些性格各異,卻個個有趣的靈魂中間,接受一次神聖的文化洗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