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了改革弊政,推行新政,大刀阔斧,力排众议,借助皇帝的支持,将一个又一个政敌逐出权力中心,排挤出朝堂,流放边陲。
他,发现推行新政的弊病,不顾个人得失,上书言事,反对新政,触怒了一心改革、推行新政的皇帝,最终被贬谪到南疆蛮荒之地。
他们,是政治上的死敌。然而,当磨掉权力的棱角,抛开各自的政见,他们又成了彼此欣赏、诗词唱和的好朋友。
他们就是“熙宁变法”的主导者王安石,和“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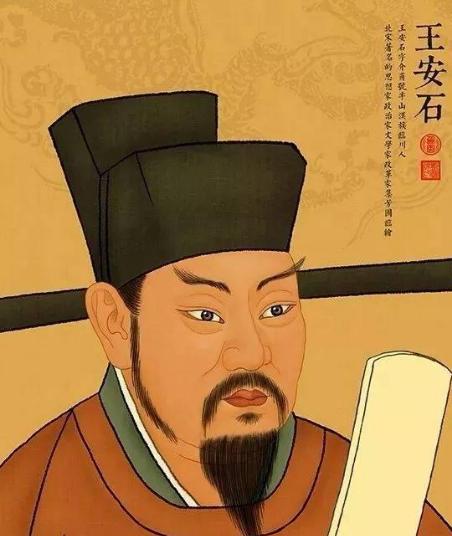
王安石和苏轼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诗人,而且还都是大诗人。这两位大诗人之间,有着复杂的政治关系和人生交集,却共同树起一座时代的丰碑——宋诗。
在《莫砺锋讲宋诗课》一书中,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莫砺锋先生为我们生动地讲述了很多宋朝诗人们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认真剖析了宋诗之所以能继唐诗之后,独树一帜的深层原因。
后人对于王安石的认知,更多的是源于他所主导的“熙宁变法”,而往往忽略了他的另一重身份——诗人。即便对他的诗有所了解,也大都停留在“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这样的诗句里。而莫砺锋先生在他的书中告诉我们,王安石不但推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变革运动,而且,还是宋代诗风的开创者之一。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这是王安石所作的六言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相对于五七言诗来说,六言诗缺乏单双音步交迭的变化感,显得单调呆板,因此,唐宋诗人很少写六言诗。宋朝诗人洪迈就说过:“予编唐人绝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而六言不满四十,信乎其难也。”由此可见,六言诗是很难写好的。然而,王安石写的这两首六言诗,却被近代文学家陈衍评价为:“绝代销魂,荆公诗当以此二首压卷。”
当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在西太一宫看到这两首诗后,“注目久之,曰:‘此野老狐精也。’遂次其韵”。苏轼称王安石为“野老狐精”,意思是说他无所不能,这是一位大诗人对同代诗人由衷的钦佩。苏东坡在次韵诗中感叹道:“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作者在书中也因之发出感慨:“政治上的歧见会使人们产生对立情绪,而‘绝代销魂’的诗歌佳作却能拉近心灵的距离。”
当苏轼感叹王安石的无所不能,提笔写下和诗的时候,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因抵触“熙宁变法”而遭受的“乌台诗案”之痛。想当初,苏轼被贬黄州,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何等凄凉!在落寞之际,苏轼在一座小土山上发现了一株海棠,使他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蜀地。因为海棠花是蜀中的名花。睹花思乡,他把自己的满怀愁绪都对着海棠倾吐了出来: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深谷。……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这首诗很长,就如同诗人的怀远思乡之情一样悠长。这里我们只选取其中的首尾两段与您分享。相对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名句,可能苏轼的这首诗并不为人所熟知。然而,苏轼对自己在情绪极度低落之际写下的这首诗却是极为看重,视为平生得意之作。正所谓“政坛失意,诗坛得意”。
其实,岂止苏轼政治生涯坎坷不平,政治强人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
“怀抱难开醉易醒,晓歌悲壮动秋城。年光断送朱颜老,世事栽培白发生。三亩未成幽处宅,一身还逐众人行。可怜蜗角能多少?独与区区触事争。”
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发出了“怀抱难开,晓歌悲壮”的强烈感慨。为了实现变法图强的夙愿,他二度拜相,屡遭诋毁,功业未就,终老乡野,眼看着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功亏一篑,付之东流,心情何等郁闷!然而,红尘纵无路,心中尚有诗,从政治的枷锁里解脱出来,投入到诗歌的怀抱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抛开二人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政治襟抱不说,单从他们在唐宋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也足以令人敬仰。
在政治上喜欢挑战难关的王安石,同样也喜欢挑战诗词的难关。莫砺锋先生在书中给我们讲了一个王安石与苏轼“斗诗”的小故事。
王安石看到苏轼写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诗后,见二诗分押“尖”“叉”二韵,韵险而语奇,不由见猎心喜,一口气和作了六首押“叉”字韵的雪诗,真是名副其实的争奇斗巧!
古人喜欢诗词唱和,这固然是一种交流乐趣,其中却也隐含着相互比试、一较高下的意味。在《莫砺锋讲宋诗课》这本书中,作者分别将唐诗和宋诗以及宋朝的诗人之间进行了不同层面的比较和评论。
作者认为,后人多将唐诗与宋词并列,称为文学史上的“双峰”。实际上,宋诗也有其与唐诗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其文学地位并不亚于前者。作者这样讲述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唐人相比,宋代诗人的生命范式具有冷静的、理性的、脚踏实地的特征,呈现为一种超越了青春躁动阶段的成熟状态。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情感强度稍嫌不足,但思理的深刻则独致高境。宋诗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诗除了理性特征之外,还有一个与唐诗截然不同的特征:以俗为雅。用苏轼的话说就是:“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也就是说,人们平时说的家常话,都可以写入诗里,不过需要诗人将其由俗化雅。对于唐人来说,俗字俚语入诗是诗家大忌,也就是杜甫等极少数人偶尔以俗字俚语入诗,就连刘禹锡重阳日作诗都不敢用俚俗的“糕”字。为此,宋朝的诗人宋祁还作诗嘲笑他:“刘郞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
相对于趋雅避俗的刘禹锡而言,苏轼似乎简直太俗了。因为他竟然以“牛矢”入诗!“牛矢”这两个字,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没什么不雅,但是,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字的话,您就明白它为什么不雅了。因为,“牛矢”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牛粪”!那么,苏轼的这首诗是不是很俗呢?让我们先来读一遍,再下定论。
“半醉半醒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首诗的意思大致是这样的,诗人喝得半醉半醒之际,到几个黎族朋友家里走访,回来的时候,晕晕乎乎地走在竹刺藤梢之间,迷了路。怎么办呢?循着地上的牛粪轨迹寻找回家的路吧,因为,诗人的家就在牛栏西边再往西去的地方。
乍一看,牛粪牛圈都入诗了,貌似很俗,再细细琢磨,但见诗人之质朴率真可敬可爱,竟无一丝俗气。为什么?与苏轼齐名,共同提倡“以俗为雅”的黄庭坚给出了解释:“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所谓雅俗之别,在于人的心境和视角。俗人看雅物,只当作俗物;雅士看俗物,可生出雅兴。
兼具理性和以俗为雅两大特征的宋诗,因其独特的风貌树立起一座时代的丰碑。这座丰碑的创立者,不止王安石和苏轼,还有诗风平淡的梅尧臣、晓畅委婉的欧阳修、雄放直率的苏舜钦、生新别致的黄庭坚、简朴古拙的陈师道,以及两宋时期的诸多优秀诗人。
历史的河流时而缓缓流淌,时而浪花奔涌。那些胸怀家国天下、腹有奇丽诗文的诗人们,已然将生命汇入这条河流之中,渐渐逝去。而宋诗这座文学史上的丰碑,却并未因创立者的逝去,河流的冲刷而消磨浸蚀,始终如灯塔般巍然屹立在烟雨迷茫的河渡头。那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也永久地镌刻在这座丰碑之上,熠熠生辉。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用生命写就的诗句,或许可以作为这座丰碑最好的注脚。
《莫砺锋讲宋诗课》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瞻仰这座丰碑的机会。让我们与作者一道,走进宋诗,走进那些性格各异,却个个有趣的灵魂中间,接受一次神圣的文化洗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