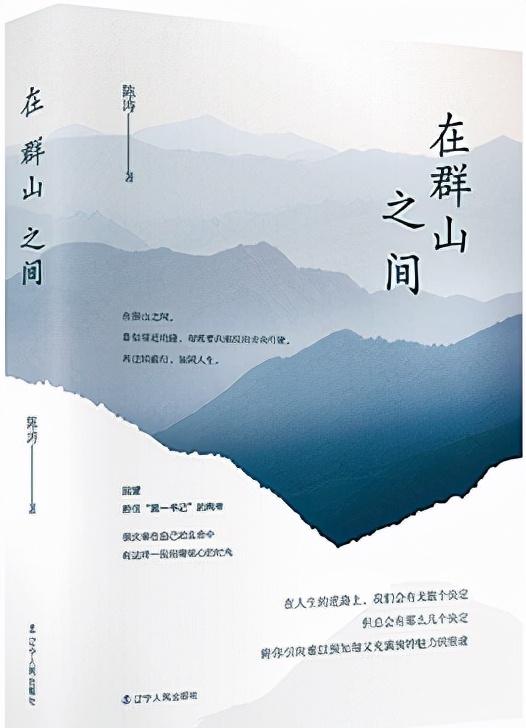
《在群山之間》的作者陳濤曾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挂職兩年,擔任池溝村第一書記。本書就是以他擔任第一書記期間帶領山村農民脫貧為主線,多方面呈現了這個邊遠小鎮的風貌、社會狀況以及作者的思索。這樣的主題其實不是很好寫,容易寫成工作筆記之類的東西,流于平鋪直叙。而本書讀來親切感人,非常難得。
這部作品之是以能夠打動人心,我以為主要與作者真誠的态度有關,他直面自我和農村社會現實,不虛美,不隐惡。給我印象頗深的有兩個方面。
一是作者對自己孤獨和軟弱心理的描摹。錢锺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中說:“風無形,可以從飛沙、麥浪、波紋中看到風的形狀。”内心情感也是如此,往往通過具體的事物才能顯現和得以賦形。隻身一人置身偏遠落後的高原小鎮,難免孤獨。在《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在群山之間》兩篇中,作者都用較大的篇幅通過一系列日常生活行為來描摹自己的孤獨。他因為獨自喝茶而對茶壺産生了情感,寫道:“極無聊時,會把所有的紫砂壺擺放在茶台上,分别放入不同的茶葉,再一一注滿開水,蓋上壺蓋,用熱水輕潤壺身。對于它們,我是喜愛的,它們始終陪伴着我。在無數個深夜裡,我們互相凝視,在孤獨中,我們互相訴說,在陪伴中,壺身日趨透潤,盞内五彩斑斓,它們如同我最親近的朋友,以這種方式陪我見證并記錄了這段時光。”常用紫砂壺的朋友都知道,有“養壺”之說。作者不僅養壺,使壺身日趨透潤,還能與之對話,這也許是長期處于極度孤獨中才會有的冥想狀态吧。他逐漸學會了與孤獨相處,以至于超越自己低落的情緒,更好地進入工作狀态。他還寫了獨處中的脆弱,如年幼的女兒在雪夜打來電話,自己不禁潸然淚下。
二是直面落後農民的心理狀态。作者在《後記》中談到自己的創作追求:“從我寫下第一個字時,我就知道這并不僅僅是關于環境與工作的記錄,我試圖去穿透生活的表面,在展示不同群體的形象以及努力中思考複雜的人性,揭示永恒的困境。”在脫貧攻堅中,他看到了農民的良善、樸實、上進,也嘗試去正視和了解他們身上的缺點;他看到了鄉鎮基層幹部在面對落後農民時的辛苦和無奈。農民教育落後始終是中國啟蒙、革命和農村改革面臨的問題。這在《芒拉鄉死亡事件》中得到深刻的反映。低保戶羊得才夫婦想使全家都享受一類與二類低保,但不符合條件,竟在雪夜将八十一歲的老母拉到鄉政府的院子裡,結果導緻老人身亡。羊得才夫婦在朋友圈和微信群發視訊,給縣鄉幹部造成極大壓力,弄得地方上司隻得妥協讓步。《山中來客》寫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鎮幹部在收費時,誤把六百塊錢給了她。後來她很不情願地還了錢,但又因為自尊心,與兒子多次到鎮政府鬧事。結果也是以鎮裡幹部妥協而告終。文章分析評論道:“窮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對于這個女人而言,面子才是更重要的東西吧,鄰裡的風言風語可沒幾個人能消受得了。”對上述人物的描寫、評論,既展現了群體的性格,也有人性的深度。作者沒有簡單地批評,而是以同情和了解的态度娓娓道來,揭示出脫貧攻堅中面臨的一個普遍性問題。兩個故事都很生動,真實感很強,讓人感覺它們來自熱騰騰的生活本身。
盡管有人主張散文可以虛構,旨在提高文學性,然而散文的魅力主要還是源自真實性。真實性離不開作者真誠的态度。在一部長篇系列性散文作品中,作者都會有意或無意地塑造出一個作為創作主體的自我形象,讀者對這個自我形象的認識和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制約着他們對作品真實性的感覺和态度。本書作者坦誠面對自己内心的負面情緒,不回避現實社會中的陰暗面,塑造了一個可信賴的真誠的自我形象。正如他在《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中所雲:“對這段時光,我有用真心對待。”
作品的真實性與其文體風格也密切相關。《在群山之間》表現出了鮮明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大緻可以說是:樸質、鮮活,感性與智性相結合。作者陳濤對自己的文體風格是有自覺追求的。他在工作中培養了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他的思維方式又進一步影響了其文體風格。他說:“我越來越不喜歡漂亮的但是空洞的文章,我會看文章的核,看作者的思想、思維,看作者如何用最準确的,而非一味堆砌的詞語的表達。”(見《在群山之間》一篇)前不久我讀了增訂版的《大地上的事情》。陳濤的話讓我想到葦岸對散文文體的追求,我覺得他們之間有相通之處。葦岸在自序中說:“就我個人來講,我更傾向散文文字的簡約、準确、生動、智性;我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寫最大的文章。”在《我與梭羅》一文中他又寫道:“梭羅的文字是‘有機’的,這是我喜愛他的著作的原因之一。我說的文字的‘有機’,主要是指在這樣的著述中,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于質感和血溫,思想不是直陳而是借助與之對應的自然事物進行表述(以利于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展現了精神世界人與萬物原初的和諧統一。”我以為葦岸關于“有機”的概念适用于評價陳濤的作品——他的語言是“有機”的,富于質感和溫度,準确、生動,感性與智性相結合,這些與其書寫的對象是契合的。
關于散文,每每有“質勝”與“文勝”之别。陳師道《後山詩話》雲:“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于事情,但不文耳。”陳濤的語言是“切于事情”的,或者說是即物的。《在群山之間》可以說是文質彬彬,不過更偏向于質——它有自己的硬核,屬于質勝之文。
文章作者: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開發
編輯稽核:遼甯出版集團宣傳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