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炜
摘編|張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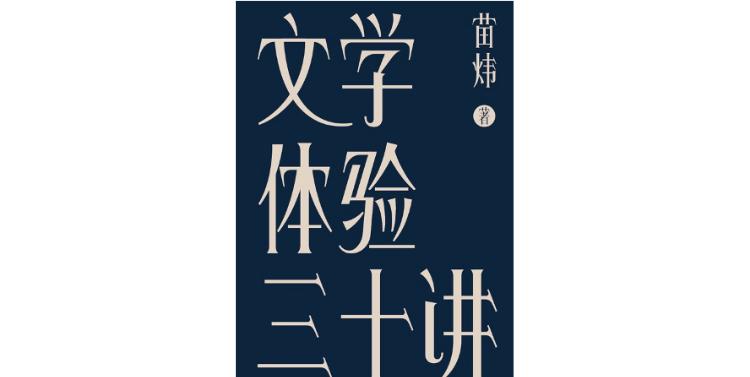
《文學體驗三十講》,作者:苗炜,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1年1月
蔣雯麗演過一部電影,《立春》,她演的那個角色王彩玲,生活在中國北方的一個小城市裡,在師範學院當音樂老師。王彩玲的夢想是調到北京去,到專業樂團裡去唱歌劇。她想獻身于藝術,這本是一件很高尚的事,但她身上又有可笑的地方。她被騙,也自欺欺人,她瞧不上周圍的人,可又需要别人的安慰。小城裡有一個青年叫黃四寶, 考了五年的美院也沒考上,沒事兒躲在自己的屋子裡,脫光了,對着鏡子畫人體。黃四寶跟王彩玲兩人遇上,之後的事,總有點兒可笑。一方面我們看見,小城裡兩個熱愛藝術的人,懷揣着夢想,對抗着命運;一方面我們又知道, 這兩個人折騰不出什麼結果來,早點兒認命比較好。你說《立春》這個電影是喜劇嗎?它的底色非常悲涼,王彩玲有高尚的情操,喜歡高雅的東西,卻不被世俗了解。你說它是個悲劇嗎?王彩玲和黃四寶對自己錯誤的認識,又總讓人覺得可笑。我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可能會哭,也可能會笑。
有時候人們看電影,或者去看戲,都是有心理預期的: 我看這個戲,圖個樂子,或者我看這個戲,帶兩包紙巾,好好哭一場。我想到契诃夫的時候,總覺得,我應該哭一鼻子。俄羅斯大地上那麼多受苦受難的人,怎麼能不哭一鼻子呢?當年,有一位觀衆,看契诃夫的戲就哭了,契诃夫就給他寫信,信裡是這麼說的:“您說,您在看我戲的時候哭了,還不止您一個哭了。但我寫這些劇本不是為了把你們弄哭啊,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我的戲弄成哭哭啼啼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羅斯大導演,導過契诃夫好幾個話劇,但契诃夫說,我要的是另一種效果,我要的隻是誠懇,開誠布公地去告訴人們,看看你們自己吧,你們生活得很糟、很無聊。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人們了解到這一點,然後他們就必然會給自己創造另外一種更好的生活了。要明白,你們現在生活得很糟、很無聊。這有什麼可哭的呢?契诃夫這封信,寫得很殘酷——你們現在生活得很糟、很無聊,這有什麼可哭的呢?他寫這些戲,跟女演員談戀愛,一大堆紅顔知己,他不會哭。但我們能創造出另外一種更好的生活嗎?好像也創造不出來。還是拿《立春》這個電影舉例。王彩玲認識到自己在一個小城裡教唱歌,這裡的生活很糟、很無聊,她想創造另一種生活,去北京唱歌劇,但是她去不了,這可怎麼辦呢?
契诃夫有一出戲,《三姐妹》,寫的是住在俄羅斯某個城市裡的三姐妹,大姐沒結婚,小妹沒結婚,二姐嫁給了一個中學老師。這姐妹三個,都受過不錯的教育。三姐妹還有一位大哥,這位大哥是個讀書人,會拉小提琴,還會雕刻。本來家人都期望他做學問,在莫斯科當個教授,可他就在這個小城裡當了一個小官員,娶了一個很厲害的媳婦,自己很苦悶,賭錢,欠了一屁股的賭債,把房子也抵押了。大哥已經放棄幻想,但姐妹三個總會說,我們要到莫斯科去,到了莫斯科,所有的問題就迎刃而解,所有的苦惱就消失了。
這三姐妹,當年是跟着軍官爸爸到這座城市駐紮的, 他們瞅不上這個地方。忽然,城裡來了一支新的部隊駐紮, 來了一個軍官叫威爾什甯,三姐妹中的瑪莎就跟威爾什甯抱怨,說這個地方不好,在這樣的小地方,懂三種外語, 是不必要的奢侈,是一種累贅,就像長了六指似的。威爾什甯回複瑪莎的一段話,大概是劇中最有名的台詞,經常被引用,威爾什甯是這麼說的——我認為,有知識的、受過教育的人,無論住在哪個城市,也無論那個城市有多麼冷落、多麼陰沉,都不是多餘的!我們就拿這座城市來說吧,住在這裡的十萬人口,當然都是沒有文化的、落後的,我們也承認這裡邊隻有三個像你們這樣的人。周圍廣大老百姓的愚昧,你們克服不了,那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在你們一生的過程中,你們還會接連不斷地讓步,你們也會迷失在這十萬居民的人群當中,生活也會把你們埋沒了。但是,你們依然不會完全消滅,你們不會不産生影響。也許繼你們之後,又會出現六個像你們這樣的人,再以後,又出現十二個,如此以往,總有一天,像你們這樣的人終于形成了大多數。兩三百年以後,世界上的生活一定是非常美麗的,我們應當期望它,夢想它,為它做準備。
這段台詞,不解決實際問題,一下子給捅到兩三百年之後去了,但威爾什甯的确安慰到了瑪莎。瑪莎的丈夫是一個中學教師,比較安于現狀,比較窩囊。威爾什甯有老婆孩子,可他對老婆也不太滿意。是以,這個瑪莎和威爾什甯,就互相愛上了。讓人痛苦的地方是,瑪莎和威爾什甯可能對庸俗的世人抱有一種輕蔑的态度,庸俗的人會偷情,想讓他們單調的生活變出點兒花樣,丈夫和妻子會互相欺瞞,但他們兩個高尚點兒的人,想要互相安慰,也是偷偷摸摸地談情說愛,他們其實沒什麼更好的辦法對抗自己不滿的現實,能互相找到點兒安慰,就不錯了。
苗炜,1968年生,小說家。曾任《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新知》雜志主編。已出版作品《讓我去那花花世界》《星期天早上的遠足》《寡人有疾》《面包會有的》《給大壯的信》等。
生活總是特别麻煩、特别具體的,痛苦呢,總是有點兒抽象。比如你說,我這個月的房租交不了了,兜兒裡沒錢了,這就是生活中的麻煩,很具體,你得想辦法解決。但你說,我的工作沒意義,這不是我夢想中的工作,這就是一種痛苦,但它顯得很抽象。意義?夢想?你是不是要漲工資呢?還是你想換工作呢?我們盡量把抽象的痛苦, 換算成生活中具體的麻煩,但我們也得承認,有些痛苦就是很抽象的,無法換算。我們看《三姐妹》中的那個嫂子, 娜塔莎,她也面對生活中的麻煩:她生了孩子,孩子住的房間陰冷,怎麼辦?把小姑子的房間占過來就是了,讓小姑子姐妹兩個住到一個房間裡去,給自己的孩子騰出一間屋子。慢慢地把她們趕走,讓她們嫁人,占據整個房子。屋子裡太吵鬧,有人想到這裡搞化裝舞會,怎麼辦?告訴他們,舞會取消了,我不歡迎你們。老仆人沒用了,轟走。她對待生活中的麻煩,總是直截了當地給出解決之道。隻有眼前的麻煩,沒有内心的痛苦。這倒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态度。再看看她的丈夫,三姐妹的大哥安德烈,他的痛苦比較抽象,看他這段台詞——
我從前的那種年輕、快活和聰明,我從前的那些形象完美的夢想和思想,和我從前那種照亮了現在和未來的希望,都到哪兒去了呢?為什麼生活才剛剛開始,我們就變得厭倦、疲憊、沒有興趣、懶惰、漠不關心、無用、不幸了呢?我們這個城市,存在了兩百年,裡邊住着十萬居民,可是從來就沒有見過一個人和其餘的人有什麼不同,無論在過去或者在現在,從來沒有出過一個聖徒,一個學者,一個畫家。這些人隻懂得吃、喝、睡, 然後, 就是死。再生出來的人, 照樣也是吃、喝、睡,他們就用最卑鄙的诽謗、伏特加、紙牌、訴訟,來叫他們單調的生活變化一些花樣; 太太們欺騙丈夫,丈夫們自己撒謊,同時也裝作什麼都沒看見,什麼都沒聽見;這種惡劣的樣子,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孩子們,于是,孩子們心裡那一點點神聖的火花也就慢慢熄滅,他們漸漸變成了可憐的彼此相似的死屍,和他們的父母一模一樣。
安德烈所渴望的幸福與自由,是從懶惰、卑賤的生活中解放出來,是要改變人們的精神狀态,至于他能給出的建議,好像就是不要結婚,結了婚肯定要後悔。我們再看看三姐妹中的伊裡娜,她夢想回莫斯科,以為隻要環境變了,痛苦就會消失。到這出戲第四幕的時候,她意識到她回不去莫斯科了,她感歎自己才二十四歲就變老、變醜了, 她打算結婚了,她接受了命運的安排,卻還會追問,她的這些痛苦是為了什麼。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有一種錯覺,總覺得某一種理想的生活是在另一個時空裡,要麼是在莫斯科,要麼是在北京,要麼是在過去,在青春的無憂無慮的時候,後來結婚生子就毀掉了,要麼是在未來, 隻要把眼前的障礙給清除掉,忍幾年,攢點兒錢,然後就可以追逐我們的夢想了。我們否定此時此刻,生活在别處, 在未來,在過去,就不在眼前,然而随着年齡漸長,我們明白了,生活就是不斷地處理眼前的這些麻煩事。生活從來都是一些急就章。
我們還有哪些抽象的痛苦呢?我們是否還認為,一個城市、一個國家整體的生活狀态需要改善呢?契诃夫有一個短篇小說《醋栗》,裡面講故事的人叫伊萬,他的弟弟叫尼古拉,尼古拉每天努力工作、攢錢,就希望在鄉下買一處農莊,養點兒鴨子,種上醋栗樹。四十多歲的時候,他終于實作了自己的夢想,買了個莊園。哥哥伊萬就去鄉下看望弟弟尼古拉,尼古拉拿出醋栗給哥哥吃,眼中飽含熱淚,覺得這醋栗簡直是上帝賜予的禮物,可伊萬卻覺得, 這醋栗太難吃了。尼古拉實作了自己的夢想,過上了他的好生活,可哥哥伊萬卻覺得非常沉重,他是這麼說的——
我看見了一個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夢想顯然已經實作,他的生活目标已經達到,他所渴望的東西已經到手,他對他的命運和他自己都滿意了。不知什麼緣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帶一點哀傷的感覺,這一回親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種跟絕望相近的沉重感覺。
弟弟尼古拉買了莊園,終于種上了醋栗,夜裡睡不着覺,就下床拿一個醋栗吃,吃完再吃一顆,像一個小耗子似的。哥哥伊萬是以感到絕望痛苦,他認為幸福滿足的人, 就是普遍的麻木不仁,他們再也意識不到當下的生活狀态是需要改善的,災難早晚會降臨。簡單來說,尼古拉解決了生活的麻煩,完成了自己的夢想,而伊萬卻被抽象的痛苦糾纏着。說實話,我們大多數人,都像尼古拉那樣,渴望一座自己的園子,渴望自己那一顆小小的醋栗。
你渴望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是此時此地的樣子嗎?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