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籍作家張大春通過對李白多年的研究發現,李白并非人們所印象的那樣俠肝義膽,豪情萬丈,按今天的話說他活得并沒有那麼酷,甚至比較卑微,一直抱有逃避現實的想法。
李白在開元中所做的《贈從弟襄陽少府皓》詩雲:“……結發未識事,所交盡豪雄。卻秦不受賞,擊晉甯為功?”還有一種版本是緊接着 “托身白刃裡,殺人紅塵中”兩句。跟李白有過交往的詩人魏颢在李白去世後所寫的《李翰林集序》中,也有“少任俠,手刃數人”的說法。就是說,無論是李白本人的自述,還是他生前好友的記載,李白都是SHA過人的,而且不止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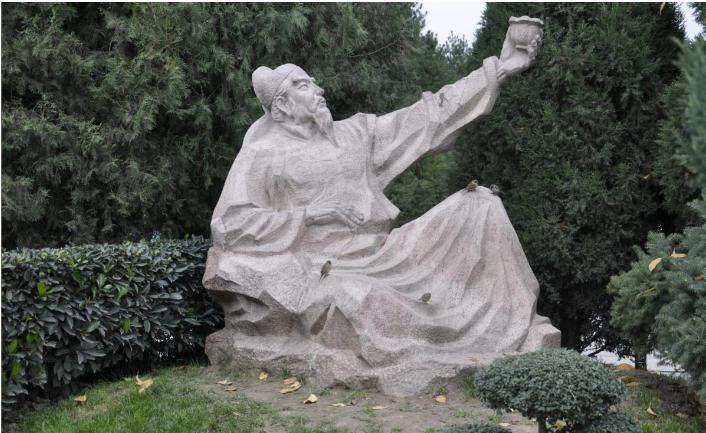
據張大春分析,詩人或許有吹牛的成分,但差點入獄卻是真的。傷人之後,李白QIAN逃,他的父親把他安排到綿州一個叫大明寺的地方藏匿落腳。李白的父親并慷慨地為這家寺院,捐了不少的香火錢,且在此一躲便是兩年,在這兩年時間裡他接觸大量的詩書文章,為成就後來的“詩仙”打下鋪墊。
畢竟是躲避官府的通緝,這個富二代常年的有家不能回,也成就了那首“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靜夜思》。人們都知道詩很美,但很難了解,一個負案在身之人有家不能歸的苦楚與無奈。
離開大明寺不久,李白便投奔趙蕤。趙是以“博宇韬略長于驚世”而著稱于盛唐的道家和縱橫家。也就是那部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雜家和陰陽家、縱橫家思想之大成的《長短經》的作者。李白在此一學又是幾年。這為李白日後的成就提供了方法論。
李白本身是個不差錢的人,他是一個富二代,其父親是一個商人。當時,是位不折不扣的土豪。可惜的是,商人的社會地位遠比農人要低,根本沒有參加科考的資格。這讓有理想而沒有出路的李白,更是平添了幾分惆怅。當時的科舉考試并不完善,并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報考的,不但身份條件限制,還要有人舉薦。如首考落榜,再考高中狀元的王維,還是在唐玄宗的親妹妹玉真公主的引薦之下才得以圓夢的。
有着遠大政治抱負的李白對于權力中心充滿向往。他雖然出身卑微,但畢竟是跟趙蕤學過處事的韬略。是以不缺路子。便通過政治聯姻,情願入墜(做上門女婿),與前宰相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并育有兩個孩子。其間,李白也不失時機地交接了他生命中的貴人,即經常被皇帝召到宮中,宣講道法的一代宗師司馬承祯。
看得出來,李白并非大家想象的視名利如糞土的豪放遊俠,其實李白一直很希望走入仕途,希望能和許多讀書人一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因身份問題,李白并一直沒有得到朝廷的重用,而到晚年,還陰差陽錯地成了叛亂分子。他的一生還是比較悲催滴。
在李白留下的1100多首詩中,的确不乏非常好的詩,“但是也有很多糟糕的詩、肉麻的詩,甚至吹牛拍馬的詩”(作家張大春)。而象《送友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贈汪倫》無疑是精品中的精品。但其中的700多首詩都是為應酬而寫,也就是“幹谒頌人,對象多半是中低階層的官僚,多半是那種八九流的小官”(作家張大春)。把自己的詩作到處送人李白似乎是首創,類似這種現象“之前很少”。這些送人的詩,反而成就了李白的大名,就像是一個活廣告。
從作家張大春的研究,我們看到一個真實而不抽象的李白。不免讓人與宋代方嶽同歎: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語人無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