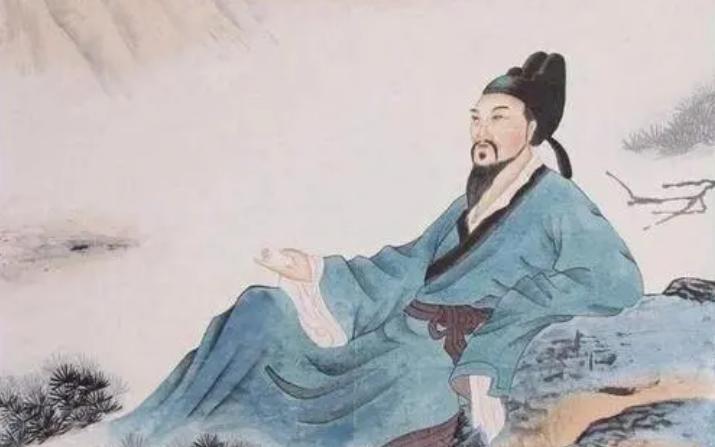
新法受阻,王安石罷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轉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後世所謂“元豐改制”。此舉收效不是很大,無非是例常的裁冗減員而已,但對軍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許多,對不從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變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當先複河(今甘肅臨夏)湟(今青海樂都)”,如此,則可使西夏腹背受敵。同時,河湟地區吐蕃諸部不相統屬,如果宋朝不攻,日後為西夏所得,更會成為大患。當時,王安石贊成此計,于是,熙甯五年(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撫吐蕃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區拓地一千多裡,招撫吐蕃各部30餘萬人,這就是所謂的“熙河開邊”。
當時,吐蕃大頭領唃厮啰已經病死(死于1065年),其子董氈繼位(後世稱這一血系的吐蕃政權皆為唃厮啰政權)。董氈繼位後,仍舊保持與宋朝的友好關系,聯宋抗夏,并曾在熙甯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環慶之圍。王韶到任後,接連把熙(今甘肅臨洮)、河(今甘肅東鄉)、洮(今甘肅臨潭)等地占領,實際上是侵蝕了唃厮啰政權原來控制的地盤和部落。
政治關系一向以利益為先,董氈于是倒向西夏一邊,與西夏聯姻,并在河州殺宋将景思。董氈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進攻河州。不過,王韶出奇兵,大敗吐蕃軍,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畢竟宋與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賜名趙思忠,并委任為官。熙甯十年,董氈派人與宋朝恢複關系,但是,相較于從前,雙方内心都不大舒服。是以,熙河開邊,從長遠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權,自己又不能在當地實行長期穩固的統治,實際上倒是幫了西夏以及後來的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後,其幼子諒祚(夏毅宗)繼位,實際統治權在其舅沒藏訛龐手中。後來,沒藏太後淫蕩無度,為其面首李宗貴所殺。沒藏訛龐為鞏固權力,又把女兒嫁給諒祚為皇後,既是皇帝的舅舅、國丈又是國相,他誅殺由己,臣民都怕他怕得要死。
諒祚成人後,對老丈人很不滿。往來之間,諒祚又和沒藏訛龐的兒媳梁氏暗度陳倉,這位國相很惱怒兒婿(外甥)給自己親兒子戴綠帽,殺心頓起。梁氏慌忙通知諒祚,少年皇帝搶先一步,殺掉沒藏訛龐一家(連同他自己的沒藏皇後),終于親政,立梁氏為皇後。
諒祚執政後,一面大力推行漢化(改用李唐賜姓“李”),一面整頓軍務,對宋朝和吐蕃進行軍事侵擾,但兩方面他都沒得大便宜,還失去綏州(今陝西綏德)之地。
于是,小夥子又與吐蕃盟好,向宋朝“謝罪”。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諒祚病死,年僅21歲,廟号“毅宗”。這小夥1歲即位,親政沒幾年,但在西夏的文治方面建樹甚多。
諒祚死後,其子秉常繼位,年方7歲,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後掌權。梁太後的弟弟梁乙埋為國相,梁氏宗族氣焰熏天。
梁太後雖為漢人,但她廢漢儀,開曆史倒車,改回元昊時的蕃儀。為建樹威權,梁太後親自發動對宋戰争,攻打秦州、環州、慶州等地。熙甯四年(1071年),宋将種谔率宋軍深入橫山要沖啰兀,大敗夏兵,并築起啰兀城(在無定河邊)。見宋人如此深入國境,梁太後與其弟梁乙埋傾盡全國之力,經過血戰,奪下啰兀城。雖然取勝,西夏國内經濟凋敝,梁太後隻得又與宋廷議和。
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16歲,理應親政,但其母梁太後仍不放權。秉常喜歡漢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禮改漢儀,卻因梁氏的反對而作罷。1081年,梁太後幽禁了想向宋朝歸還河南地的兒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時紛擾,不少部落擁兵自固。正是在此情況下,宋神宗五路伐夏,準備收複靈武。
元豐四年(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為借口,興師問罪,發五路大軍伐夏。其中,熙河經制李憲任主帥,他統領熙秦七軍加上吐蕃的雇傭兵共3萬出熙河;王中正領兵6萬出麟州(今陝西神木);種谔率9萬多人的軍隊出綏德;高太後的伯父高遵裕帶近9萬兵出環慶;劉昌祚率5萬兵出泾原。
但是,隻要知道了宋軍的主帥李憲與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監,是人就能夠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開邊”的主要人物王韶聞知朝廷興兵,力勸不要無事生非。神宗惱怒,該幫忙的人不幫,把王韶降職。不久,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還是逃不出曆史的怪圈,即開始時肯定是捷報頻傳,往後就會有一巨坑在那裡等着。
李憲公公也不孬,帶大軍攻克蘭州;王中正公公攻取宥州;種谔克米脂;高遵裕收複清遠軍;劉昌祚在磨齊隘大敗梁乙埋主力西夏軍。至此,宋軍五路捷報飛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諸路兵馬即刻向興州、靈州發起總攻。
劉昌祚一部宋軍很能戰,率先殺入西夏國境,一路斬将奪旗,殺至靈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劉昌祚得靈州首功,嚴命他不要攻城,待雙方合軍再一起進攻。由此,黃金機會喪失,靈州夏軍做足了防禦準備,又掘黃河七級渠水猛灌宋軍,切斷宋軍補給線。水淹、缺糧、凍餓交加,攻城又死傷慘重,十萬宋軍,狼狽撤退時隻剩一萬出頭。宋将種谔的九萬多人馬,也因西夏人的堅壁清野戰術損失嚴重,最後隻剩三萬多人。王中正部宋軍死亡二萬多人。隻有李憲公公所部軍很小心,全軍而還。至此,宋軍五路攻西夏以大敗告終。
此次大敗,如果宋朝君臣靜心思過,休養生息,還可以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發動了大規模攻西夏戰争。結果,永樂大敗,宋軍再次損兵折将,铩羽而歸。
這次對西夏戰争的敗事之人總共有三人:徐禧、種谔以及沈括(《夢溪筆談》作者)。
本來,種谔和沈括(時任延州知州)都主張在橫山地區經營,種谔建議在銀州築城,然後依次規劃夏州、鹽州、會州、蘭州。沈括建議在夏州以西八十裡築城,此議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給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揮。
徐禧到西北,與沈括相談甚歡,二人最終決定先築永樂城。這兩個文人無軍謀,永樂距銀州故城不遠,三面絕崖而無水泉,地雖險卻欠缺最緻命的水源。種谔表示反對。徐禧官大,不聽,并把種谔調往延州。
元豐五年(1082年)九月,徐禧發兵民二十多萬人,用十四天就築好了永樂城,宋神宗賜名“銀川寨”。然後,徐禧、沈括等人傳回米脂,隻留八百多人守衛。
西夏聞報,深知永樂城處咽喉要地,即刻集結二十多萬步騎前來争奪。
徐禧聞訊,留沈括守米脂,自領萬餘大軍前往永樂城,并于城前列陣。徐禧此人,在熙甯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實,徐禧是個志大才疏之人。聞西夏人傾國而來,他還不信,大言道:“如敵寇多來,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貴的大好機會。”
飛蛾撲火一般,徐禧直奔永樂城。
西夏軍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議乘其半渡發起進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麼,王師不鼓不成列。”說着話,徐學士竟然“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親臨最前線。
想當年元昊病死,宋朝邊将就曾建議要趁其國内動蕩興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書生,表示“幸人之喪,非是以懷柔遠人”,喪失了攻取西夏的絕好機會。
不久,後繼的西夏兵越來越多,無邊無沿,宋軍将士皆有懼色。宋将曲珍建議收兵入城以避兵鋒,徐禧不聽。很快,雙方接戰。宋軍的先頭部隊本來最為骁勇,他們錦槍錦襖,看上去光彩耀目。但是,遇見這麼多狼一樣的西夏軍,這些人心中生怯,接戰不久就失敗。西夏軍乘勝,殺得宋軍大敗。
徐禧這才慌忙入城,被西夏兵團團包圍。
衆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耗盡。此城險是很險,平地凸起,但要鑽出水來比登天還難,沒多久,士卒渴死大半。宋軍确實英勇,大多數人仍舊持兵器拒鬥。
曲珍勸徐禧趁還有些實力突圍,徐禧不聽;高永能勸他盡出金帛招募敢死隊血拼,又不聽。
結果,一夜大雨,多處城潰,永樂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亂兵,宋軍隻有四将逃免。
此次大敗,宋軍損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萬餘,最可憐的是十多萬名築城後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西夏兵刀下之鬼。
永樂之圍,種谔觀望,沒有及時救援。不久,種谔疽發後背而卒,時年57歲。他是名将種世衡之子,勇敢善謀,永樂城之敗,他早已有所預見。
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輩,為人“詐誕”,年前宋軍五路攻西夏,正是他撺掇神宗皇帝,說:“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神宗是以“壯之,決意西讨”。是以,兩年兩大敗,種谔難辭其咎。
坐鎮守衛米脂的沈括,本應率軍救永樂,但聽聞西夏軍數萬奔襲綏德,危及關中,他便去奔救綏德。由于他先前附和徐禧築永樂城,戰後,他被貶為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年間起複,沈括隻做過光祿少卿分司這樣的虛官,政治生命徹底完結。
當然,他閑居潤州8年,才有時間寫出《夢溪筆談》這部巨著。雖然在中國小課本中常常能看到他的畫像,在史傳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僅列于《宋史》列傳第九十一文臣沈遘的附傳中。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時,沈括為訪察使,回京後必盛贊良法大為便民。王安石罷歸,沈括為三司使,馬上向宰相吳充呈上新法的種種弊端,宋神宗很厭惡他的為人。
沈括與蘇轼一直是老同僚,蘇轼外放杭州,沈括作為兩浙訪察使,臨行,宋神宗囑咐他“善遇蘇轼”。蘇轼見到老朋友,非常高興,兩人親切話舊。沈括請蘇轼把到杭州後所作的詩文給自己一份以“拜讀”,蘇轼馬上答應。結果,沈括在蘇轼詩文中用朱筆一一評點,密呈禦史台與蘇轼有過節的李定,表示蘇轼在詩文中有很多譏諷朝廷的話。差點要了蘇轼的命的“烏台詩案”,實由沈括而起。
永樂之役後,沈括閑廢潤州,又同沒事人一樣,對蘇轼迎谒“甚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這位今古無二的大科學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張氏打得滿臉血肉模糊。張氏病死後,大家都為沈括慶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慣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還要跳水自殺,不久,郁郁而亡。可以想見,撰寫《夢溪筆談》的沈括幾乎是天天捂着血臉在艱難“創作”。
宋神宗聞敗訊,涕泣悲憤,好幾天吃不下飯。早朝時,他又對輔臣痛哭。确實,自熙甯開邊以來,隻得西夏國葭蘆、米脂等6個堡寨,但靈州、永樂兩次大敗,宋軍兵民役夫以及邊境歸附的熟羌竟有60萬人死于争戰。至于宋朝的花費支出,更是個天文數字,算也算不過來,絕對是吐血賠本的大買賣。
宋神宗過于有“大略”,假使打敗西夏,他肯定還會用兵河北同遼朝開戰。是以,王安石變法,一定程度上是神宗皇帝想積累财帛與西夏打仗而導緻。
變法以後,國家實力稍有積累,但天下元氣已傷,接着連續兩次大敗,實際上宋朝陷入更加困頓的局面。
不久,西夏來“講和”,宋朝隻得按數“賜”歲币,仍舊每年交給西夏大把大把的銀帛以“買”和平。
憂憤之下,不到3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僅38歲。
最後,再總結一下王安石的為人。在個人操守方面,老王勤儉無奢欲,天天日理萬機,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好幹部典型。但是,這個人,“起大獄以報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獎遊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邏卒以察诽謗也,毀先聖之遺書而崇佛老也,怨及同産兄弟(王安國,與王安石政見完全相反)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喪(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宅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這些,均成為當時後世士大夫所不齒的大把柄。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所作詩詞雅麗,清新脫俗。仔細讀之,則有森然幽冷之氣,現摘其小詩一首,以展示其當時心境:
荒涼煙雨助人悲,染濕衣襟不自知。
除卻春風沙際綠,一如送女過江時。
王安石變法的悲劇,其實也是時代的悲劇。宋仁宗在位達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與民休息是好事,壞就壞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懈怠,對西夏、遼國以“歲币”買和平,大輸錢帛以買苟安,全國上下沉浸于一種虛假的甯靜氛圍中,沒有奮發有為的精神氛圍,這才是最為可怕的事情。
此後,宋朝上下就怕言兵,兵事成為忌諱。
宋神宗繼位,天天為國貧而憂心忡忡,是以輕信王安石聚斂變法之謀,弄得天下擾動,富國的目的也沒有真正達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國強兵之計,從本質上說是“聚财”二字,以為有錢有糧就可以無敵于天下,完全忽視了精神的作用。
關于這一點,中國曆史上的“經驗”不勝枚舉:漢高祖劉邦小亭長出身,身無餘糧,最終統一中國;秦朝有六國積儲,斂九州賦财于關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開國者劉裕,内憂外患,隻以三吳一地财力,破後秦,殺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祿山得勢,擁長安,據險關,金銀山積,唐肅宗地處僻遠靈武,最終仍舊複國。
由此可見,宋朝之患,“實不在貧也”。宋神宗之時,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強國民的憂患意識,不急于求成,不貪圖小利,不打腫臉充胖子,積累20年,西進北讨,或可一舉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雖象征性地得以複位,梁乙埋又把自己的女兒給這位倒黴皇帝當皇後。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逋襲封國相。同年,梁太後也病死,但朝權仍在梁氏宗族手裡。
轉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順被扶上帝座,又是一個3歲的娃娃,是為夏崇宗。同時又是一個新出爐的梁太後主政(梁乙埋之女)。
(來源|《宋遼金夏:刀鋒上的文明》 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