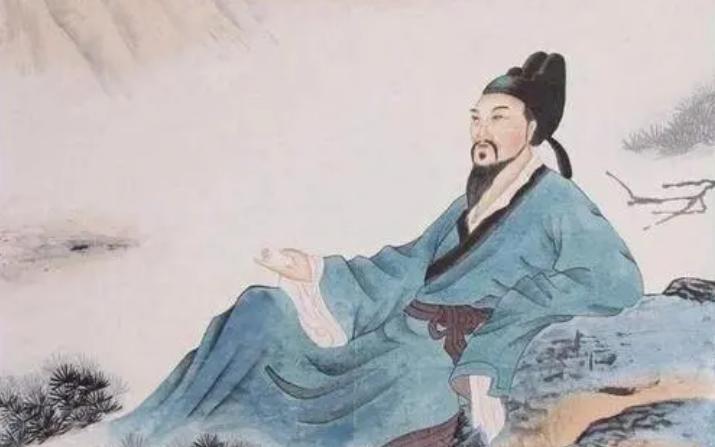
新法受阻,王安石罢相,神宗失去精神寄托,转而去搞官制方面的改革,即后世所谓“元丰改制”。此举收效不是很大,无非是例常的裁冗减员而已,但对军兵保甲制度的改革深化了许多,对不从者施以重法。
王安石变法之初,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表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今甘肃临夏)湟(今青海乐都)”,如此,则可使西夏腹背受敌。同时,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不相统属,如果宋朝不攻,日后为西夏所得,更会成为大患。当时,王安石赞成此计,于是,熙宁五年(1072年),宋廷派王韶招抚吐蕃诸部,又打又拉,竟也能在熙河地区拓地一千多里,招抚吐蕃各部30余万人,这就是所谓的“熙河开边”。
当时,吐蕃大头领唃厮啰已经病死(死于1065年),其子董毡继位(后世称这一血系的吐蕃政权皆为唃厮啰政权)。董毡继位后,仍旧保持与宋朝的友好关系,联宋抗夏,并曾在熙宁三年助宋攻夏,解了宋朝的环庆之围。王韶到任后,接连把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东乡)、洮(今甘肃临潭)等地占领,实际上是侵蚀了唃厮啰政权原来控制的地盘和部落。
政治关系一向以利益为先,董毡于是倒向西夏一边,与西夏联姻,并在河州杀宋将景思。董毡的侄子木征也率其部落进攻河州。不过,王韶出奇兵,大败吐蕃军,并生俘木征送入汴京。毕竟宋与吐蕃昔日是老朋友,宋神宗招降木征,赐名赵思忠,并委任为官。熙宁十年,董毡派人与宋朝恢复关系,但是,相较于从前,双方内心都不大舒服。所以,熙河开边,从长远角度看,失大于得。北宋削弱了吐蕃的唃厮啰政权,自己又不能在当地实行长期稳固的统治,实际上倒是帮了西夏以及后来的金朝的大忙。
西夏方面,元昊死后,其幼子谅祚(夏毅宗)继位,实际统治权在其舅没藏讹庞手中。后来,没藏太后淫荡无度,为其面首李宗贵所杀。没藏讹庞为巩固权力,又把女儿嫁给谅祚为皇后,既是皇帝的舅舅、国丈又是国相,他诛杀由己,臣民都怕他怕得要死。
谅祚成人后,对老丈人很不满。往来之间,谅祚又和没藏讹庞的儿媳梁氏暗度陈仓,这位国相很恼怒儿婿(外甥)给自己亲儿子戴绿帽,杀心顿起。梁氏慌忙通知谅祚,少年皇帝抢先一步,杀掉没藏讹庞一家(连同他自己的没藏皇后),终于亲政,立梁氏为皇后。
谅祚执政后,一面大力推行汉化(改用李唐赐姓“李”),一面整顿军务,对宋朝和吐蕃进行军事侵扰,但两方面他都没得大便宜,还失去绥州(今陕西绥德)之地。
于是,小伙子又与吐蕃盟好,向宋朝“谢罪”。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谅祚病死,年仅21岁,庙号“毅宗”。这小伙1岁即位,亲政没几年,但在西夏的文治方面建树甚多。
谅祚死后,其子秉常继位,年方7岁,自然又是其生母梁太后掌权。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为国相,梁氏宗族气焰熏天。
梁太后虽为汉人,但她废汉仪,开历史倒车,改回元昊时的蕃仪。为建树威权,梁太后亲自发动对宋战争,攻打秦州、环州、庆州等地。熙宁四年(1071年),宋将种谔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大败夏兵,并筑起啰兀城(在无定河边)。见宋人如此深入国境,梁太后与其弟梁乙埋倾尽全国之力,经过血战,夺下啰兀城。虽然取胜,西夏国内经济凋敝,梁太后只得又与宋廷议和。
1076年,小皇帝秉常已16岁,理应亲政,但其母梁太后仍不放权。秉常喜欢汉文化,一度下令取消蕃礼改汉仪,却因梁氏的反对而作罢。1081年,梁太后幽禁了想向宋朝归还河南地的儿子秉常。皇帝被困,西夏内部一时纷扰,不少部落拥兵自固。正是在此情况下,宋神宗五路伐夏,准备收复灵武。
元丰四年(1081年)七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为借口,兴师问罪,发五路大军伐夏。其中,熙河经制李宪任主帅,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的雇佣兵共3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6万出麟州(今陕西神木);种谔率9万多人的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伯父高遵裕带近9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5万兵出泾原。
但是,只要知道了宋军的主帅李宪与另一方面大将王中正二人皆是太监,是人就能够知道此仗不可能打赢。而且,“熙河开边”的主要人物王韶闻知朝廷兴兵,力劝不要无事生非。神宗恼怒,该帮忙的人不帮,把王韶降职。不久,这位功臣即病死。
宋朝打西夏,还是逃不出历史的怪圈,即开始时肯定是捷报频传,往后就会有一巨坑在那里等着。
李宪公公也不孬,带大军攻克兰州;王中正公公攻取宥州;种谔克米脂;高遵裕收复清远军;刘昌祚在磨齐隘大败梁乙埋主力西夏军。至此,宋军五路捷报飞奏入京,宋神宗大喜,要诸路兵马即刻向兴州、灵州发起总攻。
刘昌祚一部宋军很能战,率先杀入西夏国境,一路斩将夺旗,杀至灵州城下。但是,高遵裕暗急刘昌祚得灵州首功,严命他不要攻城,待双方合军再一起进攻。由此,黄金机会丧失,灵州夏军做足了防御准备,又掘黄河七级渠水猛灌宋军,切断宋军补给线。水淹、缺粮、冻饿交加,攻城又死伤惨重,十万宋军,狼狈撤退时只剩一万出头。宋将种谔的九万多人马,也因西夏人的坚壁清野战术损失严重,最后只剩三万多人。王中正部宋军死亡二万多人。只有李宪公公所部军很小心,全军而还。至此,宋军五路攻西夏以大败告终。
此次大败,如果宋朝君臣静心思过,休养生息,还可以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但是,宋神宗急火攻心,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攻西夏战争。结果,永乐大败,宋军再次损兵折将,铩羽而归。
这次对西夏战争的败事之人总共有三人:徐禧、种谔以及沈括(《梦溪笔谈》作者)。
本来,种谔和沈括(时任延州知州)都主张在横山地区经营,种谔建议在银州筑城,然后依次规划夏州、盐州、会州、兰州。沈括建议在夏州以西八十里筑城,此议得到宋神宗同意,派给事中徐禧等人前往指挥。
徐禧到西北,与沈括相谈甚欢,二人最终决定先筑永乐城。这两个文人无军谋,永乐距银州故城不远,三面绝崖而无水泉,地虽险却欠缺最致命的水源。种谔表示反对。徐禧官大,不听,并把种谔调往延州。
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徐禧发兵民二十多万人,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宋神宗赐名“银川寨”。然后,徐禧、沈括等人返回米脂,只留八百多人守卫。
西夏闻报,深知永乐城处咽喉要地,即刻集结二十多万步骑前来争夺。
徐禧闻讯,留沈括守米脂,自领万余大军前往永乐城,并于城前列阵。徐禧此人,在熙宁初年作《治策》二十四篇呈王安石,得以跻身朝廷。其实,徐禧是个志大才疏之人。闻西夏人倾国而来,他还不信,大言道:“如敌寇多来,正是我立功名取富贵的大好机会。”
飞蛾扑火一般,徐禧直奔永乐城。
西夏军渡永定河,大将高永能建议乘其半渡发起进攻,徐禧竟有宋襄公之仁,回答道:“你知道什么,王师不鼓不成列。”说着话,徐学士竟然“执刀自率士卒拒战”,亲临最前线。
想当年元昊病死,宋朝边将就曾建议要趁其国内动荡兴兵征讨,宋臣程琳也是食古不化的书生,表示“幸人之丧,非所以怀柔远人”,丧失了攻取西夏的绝好机会。
不久,后继的西夏兵越来越多,无边无沿,宋军将士皆有惧色。宋将曲珍建议收兵入城以避兵锋,徐禧不听。很快,双方接战。宋军的先头部队本来最为骁勇,他们锦枪锦袄,看上去光彩耀目。但是,遇见这么多狼一样的西夏军,这些人心中生怯,接战不久就失败。西夏军乘胜,杀得宋军大败。
徐禧这才慌忙入城,被西夏兵团团包围。
众多宋兵,困守愁城,食水很快耗尽。此城险是很险,平地凸起,但要钻出水来比登天还难,没多久,士卒渴死大半。宋军确实英勇,大多数人仍旧持兵器拒斗。
曲珍劝徐禧趁还有些实力突围,徐禧不听;高永能劝他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血拼,又不听。
结果,一夜大雨,多处城溃,永乐城失陷,徐禧、高永能皆死于乱兵,宋军只有四将逃免。
此次大败,宋军损失将校二百三十人,精兵万余,最可怜的是十多万名筑城后未及回去的役夫,也皆成西夏兵刀下之鬼。
永乐之围,种谔观望,没有及时救援。不久,种谔疽发后背而卒,时年57岁。他是名将种世衡之子,勇敢善谋,永乐城之败,他早已有所预见。
但是,此人也是急功近利之辈,为人“诈诞”,年前宋军五路攻西夏,正是他撺掇神宗皇帝,说:“夏国无人,秉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来!”神宗因此“壮之,决意西讨”。所以,两年两大败,种谔难辞其咎。
坐镇守卫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军救永乐,但听闻西夏军数万奔袭绥德,危及关中,他便去奔救绥德。由于他先前附和徐禧筑永乐城,战后,他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年间起复,沈括只做过光禄少卿分司这样的虚官,政治生命彻底完结。
当然,他闲居润州8年,才有时间写出《梦溪笔谈》这部巨著。虽然在中小学课本中常常能看到他的画像,在史传上他并不是知名之人,仅列于《宋史》列传第九十一文臣沈遘的附传中。
此外,沈括人品很差。王安石在位时,沈括为访察使,回京后必盛赞良法大为便民。王安石罢归,沈括为三司使,马上向宰相吴充呈上新法的种种弊端,宋神宗很厌恶他的为人。
沈括与苏轼一直是老同事,苏轼外放杭州,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临行,宋神宗嘱咐他“善遇苏轼”。苏轼见到老朋友,非常高兴,两人亲切话旧。沈括请苏轼把到杭州后所作的诗文给自己一份以“拜读”,苏轼马上答应。结果,沈括在苏轼诗文中用朱笔一一评点,密呈御史台与苏轼有过节的李定,表示苏轼在诗文中有很多讥讽朝廷的话。差点要了苏轼的命的“乌台诗案”,实由沈括而起。
永乐之役后,沈括闲废润州,又同没事人一样,对苏轼迎谒“甚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今古无二的大科学家沈括,畏妻如虎,常常被其妻张氏打得满脸血肉模糊。张氏病死后,大家都为沈括庆幸,殊不料,沈括受虐惯了,母老虎一死,他天天精神恍惚,还要跳水自杀,不久,郁郁而亡。可以想见,撰写《梦溪笔谈》的沈括几乎是天天捂着血脸在艰难“创作”。
宋神宗闻败讯,涕泣悲愤,好几天吃不下饭。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确实,自熙宁开边以来,只得西夏国葭芦、米脂等6个堡寨,但灵州、永乐两次大败,宋军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的熟羌竟有60万人死于争战。至于宋朝的花费支出,更是个天文数字,算也算不过来,绝对是吐血赔本的大买卖。
宋神宗过于有“大略”,假使打败西夏,他肯定还会用兵河北同辽朝开战。所以,王安石变法,一定程度上是神宗皇帝想积累财帛与西夏打仗而导致。
变法以后,国家实力稍有积累,但天下元气已伤,接着连续两次大败,实际上宋朝陷入更加困顿的局面。
不久,西夏来“讲和”,宋朝只得按数“赐”岁币,仍旧每年交给西夏大把大把的银帛以“买”和平。
忧愤之下,不到3年,宋神宗即撒手人寰,年仅38岁。
最后,再总结一下王安石的为人。在个人操守方面,老王勤俭无奢欲,天天日理万机,百分百是宋朝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干部典型。但是,这个人,“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遗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王安国,与王安石政见完全相反)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其子王雱先死)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所有这些,均成为当时后世士大夫所不齿的大把柄。
王安石晚年落寞,但所作诗词雅丽,清新脱俗。仔细读之,则有森然幽冷之气,现摘其小诗一首,以展示其当时心境:
荒凉烟雨助人悲,染湿衣襟不自知。
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送女过江时。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的悲剧。宋仁宗在位达42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与民休息是好事,坏就坏在“解散以休息之”。天下人心懈怠,对西夏、辽国以“岁币”买和平,大输钱帛以买苟安,全国上下沉浸于一种虚假的宁静氛围中,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氛围,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情。
此后,宋朝上下就怕言兵,兵事成为忌讳。
宋神宗继位,天天为国贫而忧心忡忡,所以轻信王安石聚敛变法之谋,弄得天下扰动,富国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达到。
宋神宗、王安石君臣的富国强兵之计,从本质上说是“聚财”二字,以为有钱有粮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完全忽视了精神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不胜枚举:汉高祖刘邦小亭长出身,身无余粮,最终统一中国;秦朝有六国积储,敛九州赋财于关中,一宵瓦解;南朝宋的开国者刘裕,内忧外患,只以三吴一地财力,破后秦,杀慕容超,吓得北魏也屏息蹑足;安禄山得势,拥长安,据险关,金银山积,唐肃宗地处僻远灵武,最终仍旧复国。
由此可见,宋朝之患,“实不在贫也”。宋神宗之时,如果守先朝之小康,增强国民的忧患意识,不急于求成,不贪图小利,不打肿脸充胖子,积累20年,西进北讨,或可一举成功。
西夏方面,夏惠宗秉常虽象征性地得以复位,梁乙埋又把自己的女儿给这位倒霉皇帝当皇后。梁乙埋不久病死,其子梁乙逋袭封国相。同年,梁太后也病死,但朝权仍在梁氏宗族手里。
转年,夏惠宗秉常郁郁而亡,其子乾顺被扶上帝座,又是一个3岁的娃娃,是为夏崇宗。同时又是一个新出炉的梁太后主政(梁乙埋之女)。
(来源|《宋辽金夏:刀锋上的文明》 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