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雨程
“不客氣的說,這就是人類飼料!”
得知我最近為了節約吃飯時間,嘗試了一款名為若飯的代餐粉——将人體日常所需的營養素按比例混合起來的粉末狀食物——一位朋友疾言厲色的如此批評我。
朋友認為,代餐粉剝奪了人類通過進食獲得的肉體愉悅感,以及聚衆共食帶來的社交樂趣,這是“反人性”的。另外,中國是個注重吃飯品質的國家,代餐粉這種東西的存在從根上否決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傳統飲食文化,顯得“離經叛道”。
在外界被看作“知識分子與精英聚集地”的知乎上,有一些人跟我的朋友觀念相左。他們驕傲的在簡介欄上寫上這個标簽——若飯/Soylent使用者,以此彰顯自己是個工作忙碌而先鋒前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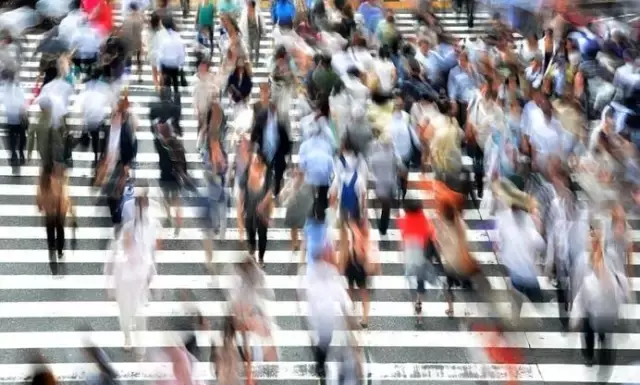
這并不意味所有知乎使用者都認可若飯這種食物。也有與我的朋友持類似想法的人,他們激烈的批判若飯這種食物(或許他們并不認為這是食物)的存在,更有甚者惡毒的詛咒若飯這家“反人性的”公司趕緊倒閉,他表示願意以個人身份出資1000元用作抵制活動的資金。
體驗報告
但丁在《神曲》中将“暴食”放在了七宗罪的第二位,第一位則是“色欲”。
按照中國的老話,食色性也。那如果能夠克制他們,人是否有機會更接近于神呢?當我開始嘗試将若飯完全替代正餐,遠離食欲的時候,我确實感覺到自己離神更近了,但老實說我并不懷念那種體驗,一些曾經激進體驗過若飯的使用者也有類似的感受。
沖泡開的若飯是一種口感像半甜半鹹豆漿的液态食物,質地略有些粘稠,但比粥要稀一點。粘稠的原因是本身添加了提供飽腹感的膳食纖維,另一方面則是若飯需要溶解的固體物質實在是有點多。
一支獨立包裝的若飯有50克重,按照邵炜的建議,一頓午飯需要三支,那也就是總計150克的固體物質——堆在杯子裡大概有半杯那麼高,而他們給到的沖泡水量建議是750ml,這意味着沖泡的時候需要大力搖晃才能保證所有内容物全部溶解。
首先是飽腹感的問題,若飯剛喝下去的時候其實非常飽肚子。使用者M告訴我,他最開始覺得一支若飯分量很少,就沒有按照推薦的3支量,額外增加了1支。顯然,他高估了自己的“飯量”:“第一次吃若飯,我幾乎是含着淚喝下去的,真的非常撐。”
然後,好喝嗎?除了有些不溶解物略微有些咯牙以外,老實說味道還不錯,超過預期一大截。但問題在于,如果讓你一日三餐都隻喝濃稠豆漿,你會不會精神崩潰到懷疑人生的意義?
據若飯的忠實使用者M介紹,經過了近三年時間的口感改良,若飯目前确實好喝多了。但若飯倡導的代餐概念卻并不那麼新鮮,國外有一款名為Soylent的産品,早就做了類似的事情。
起 因
“你需要氨基酸和脂質,而不是牛奶本身,”他說。“你需要碳水化合物,而不是面包。”水果和蔬菜提供必需的維生素和礦物質,但它們“主要是水”。Soylent的創始人Rob Rhinehart這樣看待進食的本質。
Rob Rhinehart原本是美國的一位工程師。創業時,為了節省開支和時間,他決定把吃飯這件“比天大的事”從日程表裡面砍掉。
在Rob Rhinehart看來,如果把人體看作是一台精密機器,那食物就是燃料,是以進食的本質是個工程問題。
他把吃飯這件事“去意義化”,然後像工程師看待底層代碼那樣分解了進食的概念——為什麼人類不直接攝取這些更為單純的營養成分呢?
于是他真這麼幹了。
通過研究營養生物學教科書、FDA、美國農業部和醫學研究所的網站,他制作出了一份覆寫(美國)人日常需要的營養素比例配方。然後他購置了這些營養素的原料,按比例混合在一起,這是第一代Soylent。
Soylent原本并不面向大衆,而是Rob Rhinehart自用。後來這個東西意外的在矽谷獲得了碼農們的認可,随後居然一炮而紅。再加上紐約客一篇煽動力十足的長報道——《食物終結者》,Soylent竟然一舉獲得了2000萬美元的A輪融資。
Rob Rhinehart将Soylent定義為開源食物。開源的概念來自于IT界,用在這裡的意思是Soylent将配方公開給公衆,任由公衆使用和按照自己需求修改這份配方(這意味着閱聽人如果不想購買Soylent的産品,他們也可以根據配方自己在家購買原材料DIY)。Soylent也會根據最新研究或消費者意見修改自身的配方,以期使其更符合人體的真實需求,他們管這個政策叫疊代——也來自于IT界。
而若飯,幾乎照搬了Soylent的前期概念,但CEO邵炜卻說若飯目前做的事更加嚴苛而艱難。在他的回答中,我們得到了關于這門生意的更多細節。
邵炜是個理想主義者,雖然目前他的理想并沒有得到多少認同:“食品行業已經很多年沒有過大的革新了,我希望若飯能帶來變革,在未來成為一個全新的食物品類。”
他認為,目前傳統的食品制造商一直在研發着不利于人類健康的食品,那是一種以滿足人類的食欲追求為根本出發點,陳舊而且不斷惡性循環的研發思路:追求極緻口感,崇尚口味至上,但為人類帶來了各種不健康的飲食習慣——高糖、高脂、高鈉、缺乏膳食纖維等。
而革新,指的是目前沒有一款食物能真正做到摒棄“追求極緻口感”,回歸“健康”。
“那沙拉呢?”“沙拉也不完全健康。”
除了關于健康的訴求,曾身為碼農的邵炜也有着和RobRhinehart類似的苦惱——吃飯這件事太費時間了。直到有一天,他給狗倒狗糧的時候忽然被一個念頭擊中:“狗糧這麼友善,我們為什麼不能像吃狗糧那樣吃飯?”
如果能接受這種設定,其實狗糧和若飯在邏輯上确有一絲相通之處。他們都是将成型的營養素(自然提取或人工合成)直接混合加工制成食品,相比傳統食物來說,他們的吸收更高效,營養配伍更科學。
反對者們勃然大怒的點也在于此,他們直接稱若飯為“人類飼料”。不過邵炜卻并不在意他們的批評:“老實說,我并不排斥‘飼料’的叫法,不過我更願意将若飯叫做‘基于精準營養配比的一種全新食品’。”
所謂精準營養,就是若飯最讓邵炜驕傲的特性。他參考了官方提供的符合中國人體質情況的營養素攝入推薦表,并在營養學專家的優化建議下混合了這些營養素的原材料。然後若飯也像Soylent那樣實行了開源的做法,配方表也在不斷優化,趨于一個完美的終極目标:“我希望若飯能實作全營養覆寫。”
關于這個說法,營養師顧中一也持有保留的支援态度,他認為若飯目前确實能夠一次性提供人體必需的各大營養素,也比日常膳食合理且健康。但保守之處在于,若飯做不到絕對意義的“全營養覆寫”,因為目前仍然有一些對人體有積極意義的微量元素隻存在于自然食物中,還處于待發現的階段。是以邵炜建議,進食若飯的使用者都應搭配着蔬菜和堅果一起食用,借此來消滅上面提到的那種可能性。
而“實作全營養覆寫”的另一個阻礙在于目前我國實行的食品安全法規。按照規定,目前一些已經被明确效用的微量元素不允許被添加到若飯中去,因為若飯定位預包裝食物,目前走的是食品生産許可,添加微量元素是違法的。如果希望把微量元素補全,則需要将若飯變更為保健品品類,走保健品生産許可。“若飯是面向最廣大閱聽人的,我們不希望它成為一款針對特定閱聽人的保健品。”邵炜是個異常較真的人。
除了這點,人們還擔心的長期進食流食會導緻的消化系統的萎縮及退化。顧中一表示不用過度擔憂,因為目前沒更多論證表明這一現象的存在:“對于健康人來說胃腸其實可能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嬌貴。”與之相反的是,現在很多人的牙齒以及颞下颌關節反而可能存在過度使用的問題。
不過顧中一對于長期進食若飯還是持保留意見。由于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其實不盡相同,是以如果作為個體的人類長期吃單一食物,某些營養素的缺乏和過量的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另外,目前的營養學研究仍存在很多盲點,目前針對若飯這類食物并沒有更多研究,拿不出更多的健康證據。從營養師的立場出發,他隻能很保守的推薦若飯——完全代餐建議不超過三個月,并且最好檢測一下腎髒功能、甲狀腺功能。
顧中一最後毫不留情的告訴我,若飯及Soylent這類産品,在臨床營養界屬于全腸内營養制劑,本身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技術,從任何工藝或者配方上看也沒有任何創新。如果一定要說是某種革命,可能更多的屬于生活方式和營銷理念的創新而已。
隻吃代餐粉的第三天
我覺得見到了神
一日三餐隻吃若飯這種行為,我隻堅持了兩天。第二天晚上,我夢到有個面目慈悲的人端着炸雞和芝士蛋糕送到我面前,然後告訴我“回頭是岸”。
使用者K比我的意志力堅定,他堅持了一個月隻吃若飯。後來,他所有的感官都被強化了,走在街上的時候,他說自己能夠聞到這條街上每家餐館和燒烤攤的味道。在一個月結束之後,K狠狠的吃掉了一碗酸辣粉,然後他就拉肚子了,癱軟在馬桶上久久不能自拔。
邵炜比我們更接近一個禁(食)欲主義者,若飯公衆号的每篇文章底部總會有這樣一句話:“吃一餐飯的滿足不一定源自味蕾,也可以是修道士般的自律。”抛開這些形而上的宣傳語,從健康層面出發,他認為現在食品行業的研發幾乎全是陷阱:
“人類很難擺脫食欲的控制,當你吃過好吃的,尤其是那些高脂肪高糖的一些東西以後會更難忘記,這是寫在我們基因裡的東西。一些人推崇的重口味的東西,明明知道這些東西是不健康的,但是還是會忍不住去嘗試它。為了賺取利潤,商家抓住了這一點,不斷生産滿足我們欲望的東西,然後再生産新的欲望誘導我們消費。“
在邵炜看來,“人性”幾乎是欲望的代名詞。健身、早睡早起這些都是反人性的生活習慣,但他們又确實是對身體好的一種生活方式。是以“反人性”對他來說不僅不是貶義詞,反而另一種形式的認可。
若飯的忠實使用者們也認同這種觀念。使用者K認為,吃若飯的人應該都有極強的自控和學習能力。不過按照邵炜和另外一些使用者的說法,他們應該還有另一個标簽——工作強迫症。
M是一名網際網路公司的營運。他的工作并沒有繁忙到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但是工作的連續性卻很強,如果在飯點停下工作去吃飯,他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回工作的中斷點,然後恢複到工作狀态。若飯為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花五分鐘的時間沖泡、吃(喝?)掉、然後繼續工作,什麼都沒有耽誤。
邵炜則給了兩個更加明确的使用者畫像:工作時因種種因素(拜訪客戶、出差、執勤等)不友善按時進餐的人和死宅。
恐懼代餐的理由
在我宣布用代餐粉完全替代正餐的實驗結束的時候,朋友不失時機的又冷嘲熱諷了一番,不過他的态度可不止戲谑那麼簡單。
預言這個古老的詞語從未失去過市場,人類為了消除因未來的不确定性而産生的焦慮,總會通過預言給予自身以可能的安全感。
若飯/Soylent的誕生及流行指向了一種目前隻存在于科幻狂想中的未來——“賽博朋克”世界。生活被科技全面入侵,人的意義在科技文明裡持續坍塌,人性被工具理性的狂潮湮沒。人們都曾為《攻殼機動隊》裡草薙素子的命運哀歎,她成為了尋找自我的人形兵器,而我們卻一點也不想變成失去自我的人形機器。
《超世紀諜殺案 / Soylent Green》劇照
Soylent的産品名來自于這部電影
反對者認為若飯們是站在人類對立面的邪惡公司,瘋狂抵制的動機是為了滿足一種英雄主義的信念:“隻要你拒絕服從,你就仍然算是人類。”
若飯的CEO邵炜在看待這個問題時中庸了不少:“我們目前從來不提倡使用者将若飯完全取代正餐,我們隻是希望提供一種新的選擇而已。”
不過,他對未來的猜想卻一定會讓保守者們憂心不已——以後的自然食物價格将越來越高,而若飯這類的未來主糧價格則會越來越低,全面占據人類的餐桌。對普通人來說,吃一頓自然食物将成為奢侈而且富有儀式感的行為。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