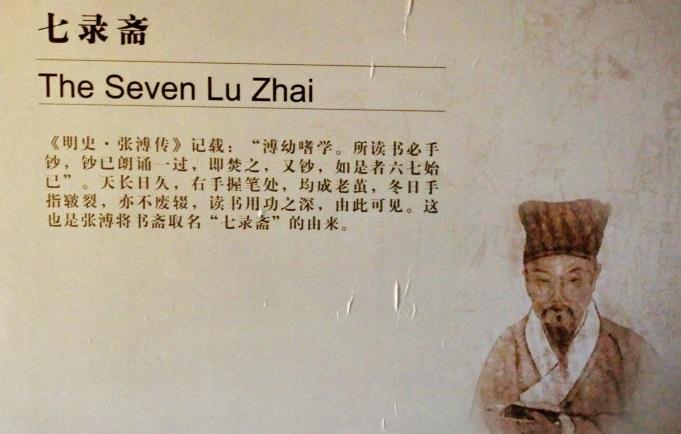
崇祯三年(1630)金桂飄香時,江南一幫士人集會于秦淮河的畫舫中,會議的召集者乃太倉人張溥。張溥,字天如,時人尊稱他為西銘先生,和同為太倉人的張采共同建立了複社。
明朝初年,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了自己的江山鞏固,特别害怕讀書人在一起議論朝政,使王朝的思想控制失效,禦制《卧碑文》,頒示天下學校,規定士人若議論國事朝政,當斬。
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權威,其效能總是遞減的,到了明朝中葉以後,殺氣騰騰的《卧碑文》已幾乎成了虛文,江南一帶文人聚會結社成風。最開始,士子們聚在一起完全是為了互相砥砺,切磋學問,許多會社完全是研讨如何寫好八股文、應付科舉考試的。但漸漸的聚會和結社就不限于此了。像王陽明學說的繼承人,常常舉行規模浩大的“講會”,讨論宏大的哲學問題;東林書院建立後,被士大夫的主流——即官場抛棄的士人們聚在一起論學議政,影響了整個民間輿論。木匠皇帝熹宗登基後,魏忠賢上司的閹黨和東林人士産生慘烈的沖突,一批優秀的士人慘死在诏獄,東林精英喪失殆盡。書院也被拆掉,結社講學之風被打壓。
但已到暮年的明王朝,隻剩下一個龐大的外殼,它的社會控制力已相當有限。崇祯登基後,閹黨被清除,東林人士被平反,結社之風又起來了。
張溥還是生員的時候,就很有名望,本邑和外邑許多青年弟子拜他為師,包括後來名滿天下的吳偉業。當時的張溥,和清末廣東南海康有為築室授徒的架勢差不多。在前一年即崇祯二年(1629),他們在蘇州府吳縣的尹山舉行成立大會。所謂複社的“複”,有恢複東林的意思,是以人們叫複社為“小東林”,但複社并非當時江南唯一的文人社團,像陳子龍、夏彜仲等人在松江建立了幾社。
由于張溥的名望,最後其他社都以複社為中心,陳子龍、夏彜仲等創辦其他社的人,也加入了複社。——因為這類文人社團畢竟比較松散,不像後來的政黨那樣紀律嚴明,入了此黨基本上就不能入别人的黨了。
尹山大會的動靜還比較小,因為當時複社中的士子,隻有張采中了進士,其他的人還隻是普通的生員。
在中國,一個人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他所具有的聲望及其他資源,往往和他在權力場中所居的位置密切相關。崇祯三年的金陵大會就不一樣了,此時許多社員已經中了舉人。
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為東林重要人物,熹宗朝被魏忠賢害死。崇祯登基後,他聯絡其他遇害者的子弟,上北京鳴冤,成為“東林孤兒”的領袖人物,東林人士被平反後,他來到了南京,參加崇祯三年的江南鄉試,經人介紹進了複社,于是也躬逢這條畫舫上的盛會。晚年他在《思舊錄》中記載了這次歌舞聲中的文人會:
庚午(崇祯三年)(與張溥)同試于南都,為會于秦淮舟中,皆一時同年,楊維鬥(廷樞)、陳卧子(子龍)、彭燕又、吳駿公、萬年少、蔣楚珍、吳來之。其下第者,沈眉公、沈 及餘三人而已。
也就是說,參加大會的江南名士,除黃宗羲和沈壽國兄弟外,其他都中舉了,真是功名在前,美人在旁,有酒有歌,張溥為首的這些名士該是何等的意氣風發,而黃宗羲卻是衆多得意中一個孤單的失意者。
對這次大會有人記載為約有兩千人參加,那幾乎是當時參加鄉試的士子們都來湊熱鬧了,那個秋天青樓的生意真好。與張溥、黃宗羲在一條船上的應當是複社的骨幹。當然,少不了陪酒、唱歌的秦淮名妓。她們自然逢迎科舉場上的得意者,黃宗羲當然隻能一人向隅。
這張溥可算是“文壇領袖,花界伯樂”,那時候的社會風氣是美人名士,相得益彰,青樓中的美女經名士一頌揚,立刻身價百倍;而某位并不很有名的士子,如果得到某青樓有名的花魁垂青,同樣會傳為美談。當然也有附庸風雅的假名士去青樓泡妞,被奚落的故事。有一位叫劉元的名妓,晚上和某位“名士”晚上睡在一起,面朝裡面把脊梁對着那位“名士”,那位“名士”覺得受到了冷落,拍着劉美眉的肩說,“汝不知我為名士耶?”劉美眉轉過臉說了一句:“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
這劉美眉若是碰到張溥,斷不會這樣,因為天如先生成名很早,是真名士,這樣的文壇領袖青樓女子巴結都來不及,哪敢得罪他。他捧紅了許多名妓,包括《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又名李香),而且是他介紹給侯方域的。那時候文人之間互相介紹自己受用過的青樓女子,乃是雅事。侯方域回憶道:“仆之來金陵也,太倉張希銘偶語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詞》,尤落落有風調。’”
不過當時李香君不可能出現在畫舫中,她在崇祯十一年左右碰到侯方域時,才十八歲左右,此時還是位不到十歲的女童,董小宛年齡也和她差不多,柳如是,此時還在吳江相國周登第家裡做婢女,而且她來金陵時,已是錢謙益的側室,老一代的馬湘蘭已死去。這次金陵大會在船中侑酒唱曲的會有誰?史無明載,但李香君的假母李貞麗此時正當年華,她和複社人士交往甚密,此時應在畫舫中。這人有豪俠氣,曾夜間賭博,千金立盡。
黃宗羲的考運不好,連續三次鄉試都落第,後來滿清定鼎中原,他立志做遺民,便不再參加清廷的科舉考試了,到死的功名還是個諸生——即俗稱的秀才。張溥和他的得意弟子吳偉業第二年會試及第,殿試後選為庶吉士,名氣更大了。成名太早不是件好事,從此他的學問沒有更多的長進。多年後黃宗羲後來評價道:
其在翰苑,聲價日高,奉之者等于遊、夏(跟随孔子的兩名學生子遊、子夏)。門無益友,天如亦恃其才,下筆豐豔,遂無苦功入細。嘗以泥金扇面,信筆書稿,故所成就,不能遠到,為可惜也!
文化人一旦過早地被炒作成公衆人物,就等于進了娛樂界,其學術成就必定“不能遠到”。是以金陵大會時張溥的得志和黃宗羲的失意,日後再審視,真是禍福相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