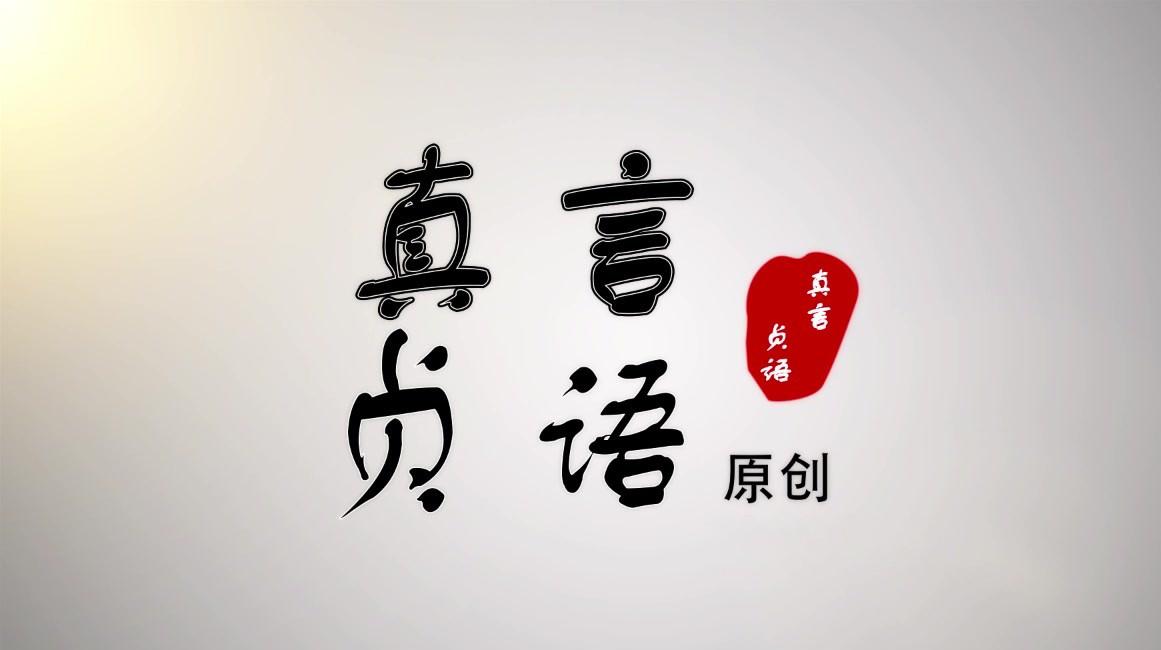
我的月餅故事
文/周長行
筆者今年七十一歲,已經度過七十個中秋節了,其間我到底吃過多少種月餅呢?看來這問題有點唐突,其背後卻躲藏着一個“月餅”故事哩。
二十歲時,是我人生命運的轉折年。之前,我在一個貧困農村出生、讀書、勞動;之後,告别家鄉參軍入伍長達二十多年;再之後是轉業回地方一家電視台做記者又是二十多年。屈指算來,我在外面已混了半個多世紀,其間亦曾經曆過各種各樣的中秋節,品嘗過各種風味的月餅。
然而,往事林林總總,沉沉浮浮,比比較較,終了,真正凸顯于心中的恰是在故鄉中秋節必吃的“糖火燒”,若按當今,也可稱之為“笨月餅”。如時下大受歡迎的笨雞笨鴨笨魚笨豬笨牛笨玉米笨大豆等等,也許就是因為它們“笨”得沒有轉基因和瘦肉精,而被人們倍加喜愛吧。然而,如今的“笨”與幾十年前的“笨”真能畫等号嗎?對此,我持懷疑态度。
恰恰倒是歲月深處的“糖火燒”,總是牢牢地紮根于我的記憶中。
那時生産隊的小麥一般畝産都是百把斤左右,一個麥季下來每戶分到的麥子少得可憐,沒有人家敢敞開了糟蹋白面。這段往事非親曆者而不能置信。中秋節如不拜望至愛親朋,是沒人肯去供銷社買月餅窮嘚嗦的。可窮人也得過節呀!月餅有啥了不起,不就是白面與紅砂糖做的嗎?
于是,父母在中秋節的前幾天就開始忙碌。既忙地裡的莊稼,又趁晌午頂去趕集買一兩斤紅砂糖,半斤肉,再買幾個梨或柿子,加上自家樹上的大棗。拮據,窮困,卻又很用心地講究。
想吃“笨月餅”也并非易事,于我而言,大概從六七歲時就跟着大人忙活,推磨推碾,将麥子磨成面粉,累得汗流浃背,力不能支。現在琢磨起來,“粒粒皆辛苦”不僅僅是指播種、耕耘、鋤禾和收割,一粒糧食到了人肚子裡是一個漫長辛苦的過程呐。
比我們更辛苦的是母親。她不但和我們一起推磨推碾,還要熬大半個晚上甚至整整一個晚上,和面,發面,再将一大盆發好了的面攤開分成一個個面團壓平,與紅砂糖合攏起來,拍打拿捏成一個個“圓月亮”。然後,有時用鐵鍋,有時用鏊子,慢慢地文火烙焙,後來我寫文章用到“漫長熬煎”這個詞時,常常會聯想起母親在廚房裡煙熏火燎艱辛張羅的一些細節。吃起來感到無比香甜入心的“笨月餅”就是這麼來的。地道地道,徹頭徹尾,步步都是笨功夫啊!
“笨月餅”在中秋節晚上擺上飯桌,先放在香台上和水果一起“貢”一會兒祖宗和神仙,笃信神仙的奶奶還要閉目合十念叨半個時辰,而後才由爺爺分給全家人慢慢地品嘗。可以沒有限制地吃,但不能沾染半句不吉利的話。特别是母親,每當過節,不論春節還是中秋節,她都要我們嚴格按照她的“講究”去做,比如不能将筷子豎插在飯碗裡,吃飽了,要麼悄悄地離開,要麼說聲“吃好了”再離開,但絕不能說“吃完了!”老人家特别忌諱“完了”這類的話兒。那時我們對老人、對節日、對“笨月餅”充滿一種敬畏感、神聖感,更有一種難以描繪的溫馨感。
可做夢也沒想到,世上還有比“笨月餅”不知“精巧”多少倍的美食呢!在我離開家鄉後的歲月裡,吃過著名的桂林月餅,長沙月餅,上海月餅,北京月餅,香港月餅等等。記者職業生涯中,我見識、品嘗、采訪過不少食品行業,“月餅天地”越來越大,或許還吃過摻假的月餅,添加劑超标的月餅,其包裝豪華到美輪美奂的月餅,外包裝比月餅不知要貴多少倍的“月餅”。月餅對我而言,不僅再是美食,而是一種曆史文化的載體,或世态炎涼的“擺設”,或投機取巧的噱頭,或比着花樣翻新上演的“現代戲”的縮影版罷了。
然而,在我内心,終其一生,還沒有哪種月餅能夠取代“笨月餅”的地位,它“笨”得令人難忘,“笨”得幹幹淨淨,“笨”得富有親情鄉魂,“笨”得沒有豪華的包裝、沒有添加劑。“笨月餅”粗糙卻結實,它還可能是唯一不掉渣渣的“月餅”。到了如今的中秋節,面對花兒呼哨琳琅滿目的月餅,我反而格外懷念起五十多年前的笨月餅來!沒有親身經曆作為背景,沒有縱橫對比作為參照,人家得說我這是吃飽了撐的啊。
現在回味,貧窮時,“笨月餅”比洋月餅顯得富貴。然而,實話實說,我既懼怕那時的貧窮,卻又始終懷念着“笨月餅”。如今算來,我吃過的月餅可以排列長長一大溜了,但領頭的,還是那個從來都沒上過大台面的“笨月餅”。
天上,還是那輪明月;情懷裡,還是那枚“笨月餅”,中秋之月依然“故鄉明”。1949年農曆2月16日筆者出生于山東省汶上縣南站鎮黃南村。回眸來路,恰是故鄉賦予我的兩樣“童子功”:“笨”與“拙”,令我受用不盡,回味無窮……
(寫于2020年中秋時節)
【作者簡介】周長行(男),共和國同齡人。老兵;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資深記者;詩人。主要著作:自選集《偉大的我們》,長篇人物傳記《不醉不說 喬羽的大河之戀》,長篇小說《渾人八斤》,詩集《句子的隊伍》等。